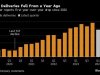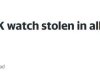在批評復旦大學侵犯學生隱私,高調處理嫖娼男生的事情之前,請容我先打一點字,大致敘述一下,我對「賣淫嫖娼」這個人類最古老的社會問題的個人觀念史。
我聲明:本人48歲,獨身主義,老處男一枚。一向反對嫖娼,至今從未嫖過娼,但是,曾經差一點就失過足。
1994年-2000年是我的青蔥歲月,我卻困守在山區小鎮的一家小國企。
那幾年,除了看電視,剩下的娛樂就是打麻將。我經常和同事一起,麻將打到晚上十一二點才結束,然後,到小吃店吃宵夜、喝白酒。
在那個絕大多數人從未摸過電腦,根本沒有網絡的時代,人的時間和精力無法像現在一樣,可以隨時拿起手機,通過刷短視頻發泄。
偶爾,男同事喝完酒,還嫌無聊,便會提議,連夜包一輛麵包車,去縣城洗三溫暖,找小姐按摩。
那時候的小縣城,只要是靠近城鄉結合部的地方,幾乎所有巷子,都遍布洗頭房。
洗頭房非常容易識別。幾乎無一例外,門都是窄窄的,裡面透出的燈光都是粉紅色的。門口總是坐著幾個十八九歲或二十出頭的小妹。
遠遠看到男人,她們便會熱情地招呼「先生,進來洗頭」。
你如果路過,看都不看她們,她們大都比較識趣,不會過於熱情。
你若賊眉鼠眼地瞄她們幾眼,一旦目光有接觸,嗅覺靈敏的她們,立刻便能從墮胎中挖掘出你這個潛在的客人。於是,馬上會站起來,熱情地拉住你的手臂……
第一次去洗頭房,是1996年夏季。
那天晚上,十二點打完麻將,被幾個同齡和中年男同事慫恿著,一起去縣城洗洗頭、泡三溫暖。當時,22歲的我,我對「洗頭」毫無概念,就稀里糊塗地跟著去了。
同事帶我進洗頭房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色情場所。只是非常好奇,洗頭房燈光這麼昏暗,理髮怎麼看得見啊?
那一刻,我本能般地產生一股舉起雙手、護住雙耳的衝動,心裡總擔心,理髮的時候,一不小心,耳朵被她們剪到。
剛剛坐下來,我就更好奇了。除了幾張椅子和沙發,怎麼壓根看不到一個理髮工具?
小小「會客廳」後面是工作區,被一張布簾隔開。布簾後面並排放著幾張窄窄的躺床。床與床之間,也用布簾隔開,彼此看不見,但是,聲音能聽的一清二楚。
布簾後面傳出調情的聲音,總算讓我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儘管小姐非常熱情地拉我享受她們的服務,我仍然是坐懷不亂。
不是說我這個人有多麼高尚,而是我天生患有嚴重潔癖。不要說找小姐,就是正常性愛,我都覺得髒。(本文對自己的詳細介紹「另一種政治啟蒙:我的無性人生與公號寫作」)所以,我至今還是守身如玉。
當男同事們在布簾後面尋歡作樂的時候,我便坐在會客廳,耐心等他們出來,帶我去泡三溫暖。
利用這個間歇,我會找小姐聊聊天。
若問她們叫什麼名字?名字幾乎都不出小紅、小白、小青、小藍……這些色譜的範圍。問她們來自哪裡,更是瞎編,反正都不是本地人。
我心裡總會想,那些同事當中,除了中年男人,有幾個跟我同齡,才22歲、23歲,都有女朋友,竟然全都會背著女友,出來開開葷。
天下的男人,有幾個對老婆從無二心、絕對忠誠的?男人真的沒幾個好東西。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時常掛念當年那些小紅們、小白們、小青們……她們應該早就結婚生子了,正和中年的我一樣,哀嘆時光易逝,年華易老。
那個時候,我一直以為,只有學歷低的青年男人,才會出去嫖娼,以至於第一次看到研究生模樣的男生嫖娼的時候,我非常震驚。
2000年,我到廈門打工。那幾年,我在廈大後門的胡里山炮台租了個農民房小單間。
房東的衛生間窗戶一推開,就能看到沿街那一排店面的地下室。
隔三差五,在衛生間,我總能看到上面那一家髮廊的小姐帶著男的,進入地下室房間。然後,關上門。
有時候,我會好奇地躲在衛生間,看看他們能在裡面「戰鬥」多久。
被領進地下室的,絕大多數都是中老年人。一般不到二十分鐘,就會出來。快的不到十分鐘,就出來了。
「戰鬥」結束,門一開,男的邁出門檻那一刻,一般會先伸出腦袋,警覺地朝四周張望幾眼。發現沒有埋伏了,便大膽地走出來。
進去的時候,一般是女前男後,有說有笑。出來的時候,一般是男前女後,彼此冷麵冷心,好像不認識。皮肉交易,不過如此啊。
偶爾,我會看到和我算得上有一點面熟的廈大研究生,都是27、28、29歲模樣的男生,背著書包,大多像是剛剛從學校圖書館的故紙堆里,或實驗室的儀器堆里,爬出來,帶著一身的疲倦,被小姐領進地下室房間,躺倒在席夢思上。
那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嫖娼原來不分學歷。
2004年,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陸院長屢次嫖娼敗露被抓。在中國的網絡世界,新聞轟動一時。畢竟,只要是社會文化知識精英出醜,總會成為民間的一道輿論盛宴,引來陣陣歡呼。
很多嫖客們開心:「高級知識分子尚且管不住自己的那個傢伙,何況我們這些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男人呢?」
某些女人們開心:「大學教授都會出去尋花問柳,也難怪我老公了。看來,這並非我人老珠黃、魅力不再,而是男人都管住不自己的下半身。嗨!」
某些貪官們開心:「這幫知識分子,平時總喜歡批評這個,批評那個,搞得自己多乾淨似的。以後終於可以閉嘴了。」
最讓我震驚的是,在我父親退休之後,患癌去世前幾年,我發現,70歲的他染上了嫖娼的惡習。
他經常跟著同伴(一位退休教師),騎著自行車,到郊區一個旅館去…..他甚至為此專門到藥店去買壯陽藥吃,小鎮一半的人都知道。我是在父親去世之後,整理遺物的時候,才發現那些藥丸。
父親一輩子從來沒有做過壞事,是一個公認的地地道道的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父親的嫖娼告訴了我,也告訴了很多熟人朋友,嫖娼不應該提倡,但是,一個人嫖娼行為與道德水準之間,真的沒有必然聯繫。法律可以禁止,但是輿論不必過度指責。
2014年,博士畢業,我成了高校教師。和全國各地的大學同行交流多了,我驚訝地發現,很多高校的中年男教師,有些甚至是我的同學,已成嫖娼主力。
別看他們平時站在講台上,滿嘴「論語」、滿嘴「三字經」,每到夜幕低垂時分,或每次出差在外,他們便活躍在全國各地火車站附近的小巷子裡…..
我目前工作的學校是從未聽說過,但是,我知道的其他多數高校,都有聽說男教師嫖娼被抓的事情。
被抓之後,無一例外,不能再上講台,發配圖書館。各大高校圖書館,幾乎已經淪為嫖客看守所。
……
囉囉嗦嗦,胡扯了這麼多,終於可以轉向復旦開除幾個嫖娼學生事件了。
大學生嫖娼,肯定不對。這一點,毫無疑問。
但是,復旦這一次做得太過分了。本次開除行動,顯得非常高調。高調到,堂堂一所百年名校,不惜觸犯學生的隱私權,把人家名字全部公開。
我個人分析是,復旦如此高調,不過是為了偽裝有道德潔癖,假裝容不得任何瑕疵,以此挽救自己近年來被一起起醜聞弄髒的名聲。
兩年前,一位復旦女博士腳踩四條船,同時劈腿四個男人,不但騙取大量財物,還騙取了幾篇博士畢業所需的關鍵核心論文,用於公開發表。
這位女博士的道德水平,比起那些自己掏腰包的嫖客,比起那些用自己的體力賺錢的小姐,不知道惡劣多少倍。
請問,復旦處理了嗎?
不久前,轟動全國的青年教師姜某某手刃學院領導事件,更讓復旦蒙羞。
聲名日漸不彰的復旦大學,這一次重拳出擊,以公布實名的方式,高調開除幾個嫖娼學生,在我看來,不過是為了「裝純」,結果,卻進一步弄髒了自己。
真正可憐的是那幾個年輕的學生。他們嫖娼固然不對,但是,成為復旦偽裝聖潔的祭品,名字被公之於天下,更是他們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