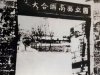沈從文和范曾,都是當代中國文化界的大佬。前者,以文學創作、文物研究名世;後一位,則昂然以書畫巨匠、學問宗師、當世大儒自居不疑。表面上所事行業、所攻領域都不同,實際上曾是師徒關係。
他們兩人之間,整整相差36歲,屬兩代人,乃前後輩。年輕時的范曾,初出茅廬,不名一文,內無奧援,外無幫助,為此曾異常恭謹地拜沈為師,而沈從文亦極看重這位青年才俊,引舉譽薦不遺餘力。也正是在沈公的著意栽培下,范先生如願以償,得以供職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並逐步踏入京城上流文化圈。
後來,「丙午丁未年之劫」降臨,范先生「真是快人」,不僅陡然變臉,立即與沈從文割恩斷義,甚至投井下石,主動密告誣害,師徒二人遂徹底決裂。沈從文晚年,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談到,這是他後半生最感憤然的一件事了。此後,任何公開場合,他再也不願提及范曾的名字了。
沈、范師徒的反目,是當代文化界很著名的一起公案。嘮叨舊事,既是出於公心表達愛憎,更意在重溫,在那個驚魂動魄的時代,所有人其實都在失去尊嚴的悲音。
從現有材料看,沈、范二人能相識,並且結下師生情緣,主要是青年范曾主動、刻意及努力的結果。
1949年後,僥倖躲過生死線的沈從文,被安排進入彼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一代文壇大家,就此改弦易轍,轉換主業從事文物探究,尤其是注目於周公共交通付給他的職司使命,即「中國古代服飾史」研究。
到了1960年代前後,逃離烽火口,識趣默存的沈從文,境遇實已逐漸改觀。據「沈學專家」凌宇《沈從文傳》一書記錄,早在1958年,彼時掌舵文化界的周揚,甚至擬請沈出任北京市文聯主席,只是為沈所婉拒;他還有單獨受到某巨公接見與鼓勵的無上殊遇。
這些年,社會上一直流傳一個說法,說他自解放後就不再從事文學寫作云云,幾成定論。這其實多半也是以訛傳訛的誤解。最好的反證,自然是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的40卷本《沈從文全集》——在這套書中,明顯可以看到,他1949年之後的文學作品,依然占據很大篇幅,不過再無名作罷了。
總之,這一切都可證實,當時的沈從文,已有再度受到重視的態勢,起碼是有點話語權的。

沈從文的這番變化,天生百樣玲瓏的范先生,也許早就看在眼裡了。據陳徒手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文披露:1962年,25歲的范曾,行將從中央美院畢業。為能謀得個好去處,范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表達橫無際涯的崇仰之意。
在這批意在投贄的書信中,范先生甚至曾動情傾述說,有一回「夢見沈先生生病,連夜從天津趕來」,感人肺肝之態,著實令人毛髮皆聳。這份謙恭至極的表白,的確讓沈從文甚為感動,熱心為之聯絡疏通,幫助他如願調入歷史博物館美術組,成為自己的助手,給中國古代服飾做插圖。
以上所述,范先生在日後的《范曾自述》一書中,大體也是這麼講述的。這就是二人早期關係的定位:沈從文對范曾有照拂提攜之恩,倆人一度是親密的師生關係。
沈從文誠篤君子,陋於知人心,他不知道的是,這種手法,范先生早先就屢試不爽。同樣著名的一段學界掌故:幾乎是同時,即將畢業的范曾,以《文姬歸漢圖》為結業作品。
畫成,他四處打聽到了郭沫若的住址,腋下夾畫每日守在其門外。有一日,終於逮到郭下班回家,他立即趨前請求題詞。郭一看是年輕人,畫也確實不錯,揮筆就是一首四十八句五言古風詩。
拿到郭沫若題畫詩的范曾,一夜成名。這事也在中央美院轟動一時,傳得沸沸揚揚。但這種求名心切,不惜走終南捷徑的格調,卻也讓范曾當時的指導老師蔣兆和、系主任葉淺予極為不滿,認為他心術不正,意在借郭的名頭逼壓校方,是「靠名人光芒愚弄觀眾,虛抬自己的投機行為」。開始,葉淺予堅決不讓此畫參展,經人說情,才以「郭先生題字必須蓋掉」為條件,得列1962年央美的畢業展覽,並最終被該校美術館收藏。
可惜,好景不長。這一對才華蓋世的師徒,「蜜月期」不過只維持了4年左右。時間來到了1966年,中國大地翻雲覆雨,什麼都將是未知數。沈從文與范曾,往日弦歌堂內的師弟子,關係也陡然生變,直到勢同水火的破裂。決裂的原因,一般公論,是因為范先生向壁虛造的中傷,與必至死地的構陷。
歸納起來,則無非有二:1、范先生陸續貼出10多張大字報主動揭發、陷害沈從文。這起是非的關鍵證據,除了「知情者說」之外,主要還來自於當事人沈從文彼時及此後所留下的文字:1966年7月的《一張大字報稿》、1969年11月的《致張兆和信》、1975年2月的《致一畫家信》、1977年4月的《致汪曾祺信》,都在《沈從文全集》第18~26卷中能找到。
在這批書信中,沈從文感傷說道,「揭發我最多的竟是范曾」,「說是丁玲、黃苗子、蕭乾等,是我家中經常座上客,來即奏爵士音樂,儼然是一小型裴多菲俱樂部」,總的罪狀就有「幾百條」,分布在「12大張紙上」,其中只要「十大罪狀已足夠致人於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寫了幾百條」,可是「無中生有」、「無一條成立」。
2、范曾幸災樂禍投阱下石,處處不忘公開羞辱前恩師沈從文。沈從文曾在《致張兆和信》《致汪曾祺信》等私人書信中有過言評,認為范曾這人,「為人陰險」,喜歡「損人利己」,學識欠缺嚴重,「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善忘」,而且特別自負,「太只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地步」。最後,是一句斷言,說范到歷史博物館10年,「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
他對范先生的好攀附名人亦表鄙夷,說他「大畫家」的名頭,跟「名人」身份,都是到處設法而來,說他只是「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他這種觀點,實際上李苦禪大師辭世前評價如出一轍的:「我沒有范曾這個學生,子系中山狼,得志變猖狂」。
對范先生,儘管在親友書信中,沈從文偶有義憤流露,可在公開場合,他實際一貫保持沉默。唯一的一次例外,大概是劫難過後,有回接受學生黃能馥採訪時曾感慨萬千。
那日,沈從文與這位愛徒閒聊往事,不知怎地,談到了范曾。他說,有回范曾畫了一幅屈原像,沈見後,善意提出一點服飾上的謬誤,不料范突然勃然大怒,「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的那套,我這是上頭批准的,你靠邊吧」,沈黯然而退。
這種來自昔日高足的羞辱,顯然讓以寬厚著稱的沈從文,終身不忘。他舊事重提,是為了藉機叮囑眼前這位同樣敦厚的白髮老學生,日後招手弟子時,也需要慧眼識人,避免自己的慘痛教訓再度上演。據黃能馥回憶,閒談最後,沈從文還意味深長地感嘆了一句,「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這些,都是流傳了幾十年的陳年舊事了,是非曲直也早有公斷。再後來,名滿天下的范曾大師,終於寫出《我與沈從文的恩恩怨怨》面對非議。對於外界那些指控,他倒大體都大方承認了,只是辯白說,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錯,是「大家同樣概莫能外地在層出不窮的運動中顛簸所導致的」。
范曾先生到底是絕頂聰明之人呀!所有的成就,他都巧妙地歸功給了自己;而所有的荒謬,他都樂善好施地推給了一個叫「時代」的玩意。

沈從文對范曾的回覆
前天,因事到館中,偶然相遇,又偶然見到你去年為安徽某報繪的商鞅畫像,佩了一把不帶鞘的刀,覺得不大妥當。因為共同搞了服裝十多年,怎麼您還不知道戰國末年還不佩刀,只用劍。劍用玉作裝飾,劍柄劍珥用玉,劍鞘中部也用玉,即過去人說的「昭文帶」,而應當叫做「璏」。劍名「轆轤」即可以上下,如取水井上轆轤作用。平時前端必低下,坐下才方便,使用時再提起,過長,拔不出時,必向後由肩上拔,秦始皇在緊急中聽彈箏宮女的歌聲,才應急救了自己。
您還畫過沂南漢墓列士傳,很不錯,我說明也寫得很清楚,大致不看說明,才弄錯。不想想秦國法律嚴極,哪容商鞅露刃上殿議事!作歷史畫,一個參加過服裝史的骨幹畫家,常識性的錯誤,提一提,下次注注意,免得鬧笑話,有什麼使你生氣理由?
……你說你負責,正因為你不懂得什麼叫「集體」,也對於業務上常識不夠認真學,才告你錯誤處,仔細想想看,是幫助你還是束縛你?若這是使你天才受約束不易發揮,回想回想你當時來館工作時,經過些什麼周折,一再找我幫忙,說的是些什麼話,難道全忘了嗎?你可以那麼自解說,這是一種手段,重在能留下,利用我一下,免得照學校打算,下放鍛鍊幾年,去掉不必要的驕傲狂妄。其實對你長遠說,大有好處。
經過十多年同事看來,學校當時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錯的倒是你的老師劉先生,一再向我推薦,保證你到我身邊不僅業務上能得到應有的提高,以至於在工作態度、學習態度、做人態度上也有幫助。我由相信劉先生所說,他和我相熟四十年,總比你懂得我多許多。不然就不會把郭慕熙和大章同志向我推薦了。他相信我到這個程度,而事實上他兩人和我共事前後廿多年,彼此印象都很好。私人可以說毫無關係,一切都從工作出發,保持了很好的友誼和理解,從來不感到我比他們高一著,一切工作都合作得很好。
此外,之檀、李硯雲、張毓峰、老史……大都前後共事快廿年了,總能保持到很好的工作關係,為什麼你倒恰恰相反?這倒很值得你回想回想,毛病是在您的方面,還是我的責任?對別人那麼好,對你卻會到前天情形,很值得您認真想想,來博物館時候經過種種,由於你只圖自保,不負責任的胡說,損害我一家人到什麼程度。現在照你昨天意思,以為我「垮了」,在館中已無任何說話權,甚至於是主要被你的小手法弄垮,而你卻已得到成功,滿可以用個極輕蔑態度對待我。即或是事實,也太滑稽了。你那麼善忘,容易自滿,蠻得意開心,可忘了不到半月前,在永玉處說些什麼?我既然早就垮了,無可利用處了,你要我寫字幹嘛?是對我還懷了好意,還是想再利用作為工具?還是對永玉明天也會照對待我那麼來一手?
范曾老兄,你實在太只知有己,驕傲到了驚人的地步,對你很不好。從私說,我對你無所謂失望或生氣,因為我活了七十多歲,到社會過獨立生活已快六十年,見事見人太多了,什麼下流、愚蠢、壞人都接觸過,同時好的也同樣接觸過,受的人事教育太多了,不然,怎麼能設想,由標點符號學起,用不到十年,就寫了六七十本小說?而由小學生身份,轉到國立大學去教寫作,混了廿五年,不被哄走?而且把多少「襲先人之餘蔭」的在大學裡習文學、教文學的「大作家」,几几乎全拋到後面去了。若果你處到我這個地位,怎麼辦?或且得意到真正瘋狂,更目空一切自我膨脹到不易設想!
沈從文在1977年4月4日寫給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對這件事難以忘懷:
我們館中有位「大畫家」,本來是一再托人說要長遠做我學生,才經我負責介紹推薦來館中的。事實十年中,還學不到百分之一,離及格還早!卻在一種「巧著」中成了「名人」,也可說「中外知名」。有一回,畫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帶一把亮亮的刀,別在腰帶間上殿議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會有這種刀,更不會用這種裝扮上朝議政事。」這位大畫家真是「惱羞成怒」,竟指著我額部說:「你過了時,早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
大致因為是「文化革命」時,曾胡說我「家中是什麼裴多斐俱樂部」,有客人來,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黃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書和工作資料全部毀去。心中過意不去,索性來個「一不做,二不休」,扮一回現代有典型性的「中山狼」傳奇,還以為早已踏著我的肩背上了天,料不到我一生看過了多少蠢人做的自以為聰敏的蠢事,哪會把這種小人的小玩意兒留在記憶中難受,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識。我搞的工作、方法和態度,和社會要求將長遠有一段距離。——摘自《沈從文全集》第2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