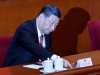前排左一:李大同,左二:徐祝慶。(圖片由作者提供)
【編者按】原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徐祝慶,因病醫治無效,於2022年元月6日凌晨4時25分在北京去世。一枚園地今日特刊發三篇悼文,以為悼念。徐先生千古!
懷念老徐
不久前得知老徐肺癌已經轉移。所以今晨聽到老徐去世消息並不意外。心裡祝願他走好。
老徐是個好人。
老徐和我前後腳進入報社。他是復旦大學67屆的老大學生,1978年10月報社復刊前,從人民日報調過來的;我則是1979年7月進入,是報社復刊後招聘的第一批駐站記者。老徐在本報退休,我也一樣,等於整個職業生涯都是同事。
記得老徐先是在經濟部當編輯,然後很快成為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我則是在地方記者、機動記者和編輯的軌跡上,兩人幾乎沒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後來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個非常內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輕同仁很有些畏懼他。
李方曾經說過一個貌似笑話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飯,湊巧電梯裡只有老徐和他,氣氛瞬間有些尷尬,因為不知道應該如何與老徐搭訕,電梯運行時間顯得格外長。李方終於忍耐不住了,沒頭沒腦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干!"老徐反倒被嚇一跳。
這個場景讓我們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來大約是1984年,這時老徐已經是副總編輯,分管科學部。我則客串科學記者,為科學部打工。這一年電腦的漢語拼音輸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電腦天才林才松與漢語拼音的發明者周有光先生聯袂完成的。我進入採訪,費了牛勁兒,才算基本搞懂關於電腦的基本知識,周有光先生的講解真是深入淺出。
盛夏,那時連電扇還買不起,我大汗淋漓窩在家裡寫這篇報導,及至最終完成時已經超過萬字。這是我的第二篇萬字長稿。第一篇萬字報導是鍾沛璋任總編輯,老鍾在簽發稿件時有一句留言,"請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見那時文字還不夠成熟。這篇稿件寫作時我感到比較自如了,最後一節甚至產生了節奏感。不過這麼長的稿件通過率甚低,因為題材和文字都得壓得住一個整版。
稿件送老徐過審,沒過一個小時辦公室就把稿件送回來了,老徐已經簽發,發稿單上啥批示都沒有,翻開看,竟然一個字的改動、刪節都沒有。這麼輕易一稿過關是我沒想到的,很不好意思,於是在送工廠發排前自己又仔細修改了一遍,刪去一千多字。
稿件迅速在一版頭條發表。這麼多年過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稱,這是記錄周有光先生在拼音輸入法上的重要貢獻的唯一一篇詳細報導。
1985年,我開始擔任科學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頂頭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們開始熟悉起來。1986年9月末,我們開始了一場冒險,將"11位大企業負責人對當代青年知識分子作出基本否定評價"作為一版頭條消息發表了。這條報導引起青年知識分子極大的不滿和反彈,反彈意見我們同樣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識分子與青年知識分子兩軍對壘的輿論局面。
下一步怎麼辦?只有摸著石頭過河,開始討論。第一組討論按慣例放在一版,後續討論轉二版。討論需要有個欄題,老徐建議叫"關於知識分子之我見"。晚上我將改定小樣送總編室夜班時,覺得老徐的欄題不夠打眼,於是給夜班留條,說老徐的欄題是什麼,我建議用"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擬的欄題。自然,這是請示老徐後的結果。
我和老徐都沒有想到,這場大討論竟然持續了100天,並且始終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國巨大的反響和高度關注,甚至人民日報在討論進行到一半時也發出專論予以肯定。這期間的每一篇討論稿都是我編好後送老徐審後發排,兩人在他辦公室對每一句話討價還價,他想更穩妥一些,我則想更有鋒芒和衝擊力,最後我們總是互相妥協。
這場大討論涉及到了關於知識分子幾乎所有方面的問題。到86年年底,我們馬不停蹄地加快刊發節奏,由原來兩天一期改為一天一期,終於,在12月30日,對話錄刊出了最後一期——這是這一天一版上,本報唯一的新聞產品,其他均為新華社通稿。
20年後,在一次社慶茶話會上,老徐感慨地說:"兩代知識分子對話錄,就是放到今天也不過時。"
今年已經是對話錄已經過去35年了,微信群里一些群友聽說我關於對話錄有一個詳細記錄,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後,一位快八十歲的四川老編輯說,我沒看幾頁就回到了八十年代,眼睛幾次發熱流淚……
1987年年初,老徐開始任總編輯。我轉任學校教育部主任。上任頭一年,就碰上一件怪事:部門同事去參加國家教委的新聞發布會,回來後我問有什麼新聞,答曰教委說不要發任何報導。到場記者生氣,問那叫我們過來幹啥?回答說你們可以報導我們取得的成就。
我一聽就火了,立刻抓起電話向老徐匯報此事,說要寫一篇言論批教委。如果換一個總編輯,多半會讓我不要沒事惹事,可老徐只是遲疑了一下,"說些什麼呢?"我說寫好你看。言論中,我援引了剛剛結束的十三大閉幕式上,總*書記面對一群國外記者,把酒縱論天下事,毫無躲閃與做作,展示了中國政壇新風的例子,痛批"某部門"的僵化與保守,標題就叫《不許發布新聞的新聞發布會》。老徐認真看過稿子,改了一兩處,簽發,第二天竟在一版顯著位置刊登。
原以為教委會打上門來問罪,沒想到過了幾天沒動靜,反倒有不少國務院部委打電話來問是不是在批評他們。又有一天,總編室的同事告訴我,一個"革命家"級的老同志受某部長之請,來問究竟批的哪個部門。原來總*書記看了這篇評論,說"是哪個部門,查一下。"我說怎麼教委沒打上門來。
與國家教委的正面衝突,發生在1988年4月。這一年年初,學校部獲得一個線索,中國人民大學布告欄上,出現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對人大的教育管理體制和學校決策的程序提出尖銳批評。
我立即請記者部支援一個文教記者,再加上兩個部門編輯共同採訪。採訪前主題我已經很明確,結果第一稿出來後,被這個文教記者寫成什麼學校的競爭機制問題。我當即槍斃。這位記者不服,要求分管副總編輯裁決,結果這位副總不發表意見,直接把稿件上交給老徐。那天我上班剛進辦公室不久,老徐就拿著這摞稿件進來了。我問他,"看了?"老徐就四個字:"不知所云!"
我請記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門兩位同事二次採訪寫作。前後折騰了四個月,我終於拿著萬字小樣在編前會上得意洋洋地說,"這篇東西已經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過去仔細看過,認可。第二天就頭版頭條大字標題刊出《傾斜的金字塔》。
據傳人大每個班因為只有一份本報,由一個同學朗讀,大家靜聽。一位微信群友,當年正在人大讀研,說這篇報導"把我們轟得靈魂出竅"。
這是八十年代第一篇全面調查披露教育如何被擠壓的重頭報導。
不知道教委是怎樣與本報上級團中央交涉的。見報當天晚上,報社值班副總編輯接到團中央分管書記的電話,嚴令報社今後所有涉及國家教委的報導,必須事先經過教委審稿。
第二天,老徐看了電話記錄,據說"臉色鐵青"地立刻給團中央書記處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說了什麼,總之我在任學校部主任期間,沒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審稿。大概在老徐的強硬態度下,不了了之。老徐把壓力扛住了,沒有向下傳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