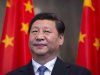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左傳》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齊國有個大大的花花公子叫齊莊公。齊國有個大大的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齊莊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終和她暗通款曲。可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覺。那天他趁齊莊公與棠姜幽會時,安排武士們將其亂刀砍死。
崔杼是個猛人,也是齊國重臣。他對前來記載的史官說:你就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史官並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很生氣,拔劍殺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當時慣例由其弟繼承職位。崔杼對新史官說:"你寫齊莊公得瘧疾死了。"新史官也不聽從,在竹簡上寫"崔杼弒其君光。"崔杼又拔劍殺了新史官。然後更小的弟弟寫下同樣的話,同樣被殺。最後是最小的弟弟。崔杼直視著他,問:"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年輕的史官繼續寫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弒其君光。"崔杼憤怒地把竹簡扔到地上,過了很久,嘆了口氣,放掉史官。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告訴了他這個故事。而我恰恰要強調的是這故事讓我一開始很拒絕寫作。它表明,寫作純屬一件找死的事。像我這麼庸俗的人當然不會幹一件吃力還找死的事,加之家族裡從文者悲涼的命運,文學出身的我就曾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玩一種毫無風險的遊戲,並暗自慶幸。可漸漸地,我發現另一種風險。規則明明規定一場比賽由兩支球隊進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一名球星告訴我:"那天我上場一看,快哭了,因為有隊友把球往自己家門踢,場上就是三支隊了。可是踢著踢著我又笑了,因為對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門踢,就是四支了。直到散場時我終於確定,其實總共有五支隊,因為,還有裁判……"
我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漸漸意識到一個叫"尊嚴"的東西是存在的。哪怕遊戲也要有尊嚴,我不能無視兩支變成了五支,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長期把五支證明成兩支,並證明得文采飛揚的樣子。這個不斷修改大腦資料庫的過程讓我痛苦不堪,越發失去智力的尊嚴。我從文學躲到遊戲,在一間沒有尊嚴的大屋子裡,任何角落都蝟瑣。又去看開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還有個結尾:那個史官保住性命,撿起竹簡走了出來,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記載歷史的人。史官驚訝地問:"你怎麼來啦。"南史氏說:"我聽說你兄弟幾個都被殺死,擔心被篡史,所以拿著竹簡趕來記錄了。"我覺得這個結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堅持自己的工作而死,南史氏則是主動找死。這叫前赴後繼。有種命運永遠屬於你,躲無可躲,不如捧著竹簡迎上去。
直到2008年,壓在殘垣斷壁下的體溫尚存還動著的小手,花花綠綠的衣袖……我終於明白,我確實該回去了。這,就是我的來歷。
當然,我仍是一個庸俗不堪的人,骨子裡畏懼著節烈的東西,我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簡沿著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猶如彩虹掛天穹的壯麗景象,只是低頭琢磨尋常巷陌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識。這些故事和常識,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只不過我們曾經丟失,或假裝丟失了……我一直償試給這些事和常識找出統一的特徵,後來才明白,這其實是尊嚴。
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智力上的尊嚴。很長一段時間了,這個民族失去智力上的尊嚴。趙高說:這是一匹馬。人們點頭說:是啊,好快的一匹馬。趕緊去修改腦子裡的資料庫,哦,馬是長角的。後來又有人說:要大煉鋼鐵。於是家家砸爛家裡的鍋碗瓢盆,村村建起煉鋼的高爐。大家假裝看不見煉出來一砣砣的東西,一捏就是一個坑。其實那一砣砣的東西和那一匹馬一樣是不存在於物質世界的,只是大腦被強行修改後產生的木馬。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鋼鐵量超過了整個歐洲,農作物產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著我們去營救。那件事情有個結尾:人們並沒有煉出鋼,倒是飢腸轆轆回家後發現不僅沒食物,連做飯的鍋都砸爛了。這個景觀壯烈與幽默並存,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並互相說服這是事實。
讓飢餓的農民相信畝產兩萬斤,讓產業工人相信柴杆煉出的鋼能造坦克,讓醫生相信是紅寶書治癒了聾啞兒的疾病……這樣讓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紅歌能治癒不孕不育,有個叫阿貴的丈夫為了感恩,甚至讓妻子李彩霞拖延兩天再生,以讓自己的孩子跟恩主的生日同一天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