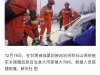公共經濟學告訴我們,政府是因提供公共物品而立。而如果按「公共」性質排序,預防和救助自然災害是排在第一的。而自然災害中最常見的是洪水。換句通俗的話說,抗洪救災是政府最該做的事情。這種觀念並不是現代經濟學出現以後才有的,而是在中華早期歷史中就形成的文化基因。《史記》記載,五千年前的大洪水時期,大禹受命治水,「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是說他身先士卒,不畏艱險,公而忘私,糲食粗衣陋室,終成治水正果。在此之後,大禹創立了夏這個中華第一國家。不僅是因為治水這個第一公共服務提出了國家的必需,而且是大禹在治水中的優異表現得到了民眾的認可。
正是因為治水是公共權力的第一職責,失職的官員就要受到懲罰。大禹的父親鯀因治水不利而受極刑是眾所周知的故事。最近更發現一個例子,說明懲罰治水不利者的傳統一直保持到了清代。《讀書》上的一篇文章提到,「嘉慶十五年(1810)7月永定河大水,王念孫作為時任永定河道員,被撤職查辦,……但河道漫溢的損失,仍需由直隸各級衙門賠償,王念孫需要承擔其中三成,總計一萬七千餘兩,限五年繳清。」(華喆,2023)不僅官員個人要受懲罰,還要承擔經濟責任。查了一下《大清律》,其中『律』「盜決河防」條例二,果然有黃河及運河的河堤被衝決,承修官及「防守該管各官」要賠償修堤費用的四成。大概其它河流的決堤也套用這個條例。看來要靠正反兩方面的獎懲,才能保證公共權力機構堅持不懈地執行其第一職責。
這種「治水是第一公共職責」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很晚近。然而,這一傳統到現在卻不見了。從各方面的信息來看,這次涿州水患慘不忍睹,而權力機構卻做了與其公共性質相反的事情。偷挖堤壩,不報預警(李木子,2023),阻礙救援,拒絕捐助,壓制表達自由(推石頭的富蘭克林,2023),限制災情透明,製造虛假新聞(滄浪大俠,2023),隱瞞遇難人數,各級官員消失不見(最底層,2023)……更重要的是,這次涿州泄洪並非必需,恰是權力機構的錯誤決策所釀成。與1998年洪水不同的地方,是這次洪水沒有出現在長江流域,其規模要小得多,最大流量7500立方米/秒,明顯低於當地歷史最大流量14600立方米/秒(1917),更大大低於1998年長江洪峰流量53500立方米/秒。在歷史上,涿州沒有出現過這次這麼嚴重洪災。為什麼這次出現了?在這次抗洪中,中央當局發出的指示是「保北京,保雄安、天津」。北京和天津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現在存而不論;而雄安是在若干年前還不存在的城市。
雄安被當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城市設立和建設。據說由清華大學規劃院等六家規劃院聯合規劃,由30多位頂級專家評審通過規劃。但其中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據陸大道院士,雄安「選擇在河北省北部平原上的一個大窪地(窪地中心部分是白洋淀)的『邊坡』上,平均海拔10米左右。歷史上洪澇災害頻發。未來的雄安新區可能需要按照極高的洪水標準設防。在嚴重洪水發生時,白洋淀有可能必須泄洪,可能會使城市被淹。」(2019)但這一問題被輕輕放過。徐匡迪說,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是傳統泄洪區,才使之像一張白紙,好大展宏圖。他說,「這個泄洪區將來是不是會再有洪水呢?但現在這個地方不是怕洪水的問題而是乾旱的問題。……從1968年大洪水以後這個地方沒有發過洪水。」(2017)排除了發洪水的可能性,就是雄安規劃的致命傷。這導致了一旦有洪水,為了保雄安就要犧牲其它地區。可以說,這次涿州、霸州和淶水等地的水患就是這個重大決策失誤在多年前就預訂的了。
據報導,這次暴雨期間在河北啟用了七個蓄滯洪區,有兩個在涿州附近,而沒有白洋淀(金台資訊,2023)。官媒也承認,這是為了「減輕雄安新區防洪壓力」(鄭丹,2023)。如果雄安規劃事先就考慮到了有洪水的可能,並且預先把涿州等地作為替代泄洪區,就違反了一個權力機構所應存在的基本原則,即保護民眾的財產與生命。而在中華大地上,一地民眾的財產與生命並不比另一地的更貴或更賤。因而作為中央當局沒有權力以另一地民眾的損失為代價建立和發展一地的城市。更何況這是很晚近才做的決定,這個決定所產生的對另一地民眾的負面後果可以在事先就知道,並且通過修改或取消該決定加以避免。因而,如果在雄安規劃中沒有考慮到洪水的後果,是重大失誤;如果考慮到,而事先就想到要以鄰為壑,就顛覆了公共權力的基本性質。因為一個政府被建立是為了保護所有公民平等地受到保護,它不應該讓一個城市以另一個城市為代價,正如一個社會不應讓一個公民以另一個公民為其發展的代價一樣。
這樣的原則是發自遠古的一般常識,也寫進《憲法》,其第33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所有公民權利平等的顯現表述。權力機構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應該是平等的,全國當局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做出明顯帶有地方歧視的決策來。那麼為什麼事情竟然如此了呢?顯然,這一憲法原則並沒有得到遵守。建雄安新城,涉及重大的經濟決策,其全部投資或數萬億,到現在為止已投入上萬億。這必然帶來對國家預算的重大負擔。更何況,這還涉及到跨地區的利害再配置。因而應該在全國人大加以討論。如果全國人大有足夠的代表性,受損地區的代表就會反對,遵循憲法原則的代表也不會贊成。然而,我們沒有看到這一決策在人大討論的報導或記錄。這就失去了糾正錯誤的一次機會。這種非程序的決策一旦作出,公民更少約束行政當局遵守憲法的手段。這一個例子很有普遍性。它說明,當局是不受憲法約束的。
這次保定及涿州權力機構的表現,就是一個不受憲法約束的典型案例。它的表現就像是它是一個經濟實體,固定領取公民的納稅,但並不按憲法要求去努力工作,甚至做相反的事情。一旦因為做得不好,公共服務的消費者有抱怨,就用公共暴力去壓制批評,並且利用官媒造假表揚自己(滄浪大俠,2023)。正是因為它以為掌控了信息,所以它才敢誇大自然災害的作用,縮小自己無能或失職造成的公眾損失,少報遇難民眾的數字,就如鄭州水患時的作法一樣。甚至為了「嫁禍」於自然,它可以偷挖堤壩決口,在官媒中將泄洪說成是「降雨」。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受憲法約束是一個系統性錯誤。它的官員是上級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它的上級不會用憲法要求和評價它,而只看它是否聽從自己的命令。這些命令更多滿足上級的個人偏好,而不是依據憲法。所以地方權力當局也沒有動力為民眾服務,而只考慮上級的喜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