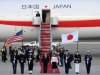大隈重信(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佐賀縣人。德川幕府末期佐賀藩士出身。早年赴荷蘭求學。後積極參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維新」運動。歷任日本明治政府民部大輔、大藏大輔、參與外國事務局判事等職。創辦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1910年任早稻田大學校長。

「在資訊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形泛濫,更有可能,更加危險,更為絕望。」
——加藤嘉一
1886年10月24日發生的一起海難事件,將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當天,英國籍貨船「諾曼頓號」在和歌山縣海上觸礁沉沒。英國船長和外國船員為了保命搶上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斃。然而,根據日本與英國的條約,日本法院無權審理此案。英國駐神戶領事依據領事裁判權,對諾曼頓號船長進行了審判,船長最終只是服刑三個月,死難者也沒有獲得任何賠償。消息迅速在日本國內傳播開來,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民眾,所有國民都憤慨至極,報紙上義憤填膺的評論文章連篇累牘。
「諾曼頓號事件」徹底激怒了日本人,他們強烈要求廢除治外法權,憤怒的公眾輿論也轉向了日本正在進行的「鹿鳴館外交」。
鹿鳴館是日本3年之前建造完成的一個政府級外交俱樂部,耗資甚巨,前後歷時數載。時任外務卿的井上馨在開業典禮上說:「友誼無國境,為加深感情而設本場……吾輩借《詩經》之句名(「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為鹿鳴館,意即彰顯各國人之調和交際,本館若亦同樣能成調和交際之事,乃吾輩所期所望。」為了招待歐美高級官員,外務省經常在這裡舉行有首相、大臣和他們的夫人小姐們參加的晚會舞會。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證明,日本已經是一個「文明國家」,與世界先進國家立於同等地位,希望藉此達到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目的。

鹿鳴館
可是,外國人諷刺「鹿鳴館外交」是「公開的大鬧劇」,國人也批評其為驕奢淫逸的國家頹廢行為。媒體人陸羯南尖銳地指出,這種歐化做法不過是「盡力討外國人之歡心,博取其同情,以此來使其應諾條約之改正」,實際上與國力不相匹配,更毫無效用。
「諾曼頓號事件」後,鹿鳴館外交在徹底破產,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繼任外務卿,承擔起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重任。大隈年青時學習西方文化,維新初期參與外交談判,曾經成功處理過棘手的外交問題,但是此時的外交形勢遠為複雜。
「諾曼頓號事件」和條約改正不利,導致群議洶洶,此時不管誰接任外務大臣,都很難有所作為。因為日本不具備和列強平等對話的實力,不可能一舉推翻舊約,而民眾要求一步到位地廢除治外法權,因此改約談判幾無勝算。外務大臣稍有不慎,就會被國人罵為「賣國賊」。在這種情況下,大隈仍然毫不畏懼地開始了新的談判。
大隈採取了與井上馨完全不同的談判策略:日本只和列強進行一對一的談判,絕不與「列國會議」對話。這樣一來,就改變了日本的談判地位,而且通過分化瓦解的辦法削弱了對手的談判價碼,談判取得了相當的進展。

大隈重信
1889年,日本分別與美國、德國、俄國簽定新條約。在與英國簽訂新條約的前夕,突然橫生波瀾。英國《泰晤士報》率先曝光了大隈改約方案,日媒隨之廣泛轉載。根據這份方案,治外法權將於5年後完全終止,日本本土向外國人開放,給其旅行、居住、營業和取得財產的權利;日本獲得了部分關稅自主權,並定下12年後完全自主關稅的約定,從而打開了日後日本關稅自主化的大門。在司法權方面,僅在大審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並僅在被告為外國人時才令其擔當審判,且其任用期限為12年;新條約實施後兩年內,日本完備民法、商法和訴訟法等法典,法典民的頒行也只用知會列強,不必取得其同意。
新條約對日本相當有利,儘管其中仍然包含相當多的「不平等」成分。當時日本實力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大隈能夠爭取到如此地步,已是當時所能達成的最好結果了。可是,當消息傳到日本國內以後,舉國譁然。
國民認為,日本明明已經是一個先進的「文明國家」,為什麼治外法權仍將存續5年,關稅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還要入主大審院?這豈不仍是損害國家利益的不平等條約嗎?!轉眼之間,大隈重信成為一個「賣國賊」。各地展開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要求停止改約談判的建議書達185件。愛國憤青們更是磨刀霍霍,決心跟賣國賊決鬥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參加完內閣會議後,坐馬車經過外務省大門口。一位名叫來島恆喜的愛國憤青突然投擲炸彈,大隈倒在血泊中。56歲的大隈右下腿卻被炸壞,一度生命垂危。雖然最後倖免一死,卻不得不截去右腳,晚年只能扶仗而行。來島恆喜則跑到皇宮前剖腹自裁。弔詭的是,行兇者非但未被譴責,反爾被社會輿論譽為「英雄」。

大隈重信雕像
在這種情況下,大隈不得不辭職,條約改正再次擱淺。在死亡的威脅下,沒有人再敢輕易啟動改約談判。最終,廢除外國人治外法權比大隈方案晚了5年,實現關稅自主晚了近10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復關稅自主權。
一百多年後,日本青年評論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寫道,「愛國賊」雖然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是「愛國者」,實際上卻做著和「賣國賊」相同的事情——損害國家利益,「在一個國家裡面,絕大多數人不是『賣國賊』……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不少,規模不小。」他指出,「在資訊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形泛濫,更有可能,更加危險,更為絕望。」
這是歷史教訓的總結,也是對那些被民族主義情緒籠罩的國家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