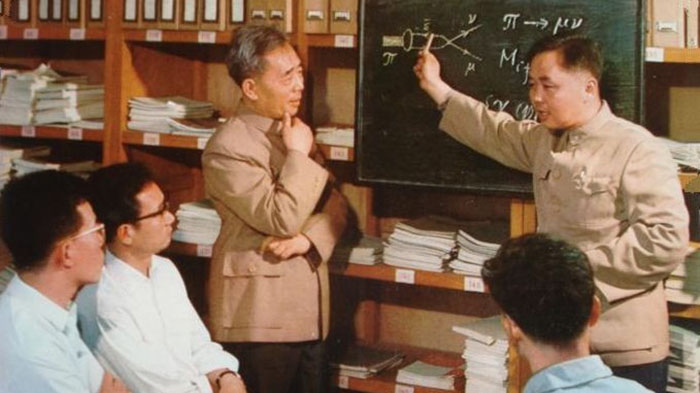
1968年2月間,清華兩派的爭鬥開始白熱化。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已厭倦了文革生活,尤其是那沒完沒了的大喇叭、大字報,口號、標語、鑼鼓、遊行……,每天只是無所事事地觀望,著實無聊。一天,聽說科學院物理所有批判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會,便和幾個同學騎車去了中關村。
在物理所的一間會議大廳里,已聚有幾百人的樣子。和別處一樣,與會者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常規之後,來自湖南醴陵第二中學的物理教師周友華開始了他的報告。我只記得他講,他是在一座古廟的門框上懸掛一個重錘,然後發現「每日早晚錘尖的位置有規律地變化」,但已記不得他是怎樣由此聯繫到要批判相對論的問題上去的。據物理所研究員郝柏林後來回憶(1),「周從而得出結論說萬有引力常數隨溫度變化,提出了一套『熱輕冷重』學說。」那天會上反對他的人發言時,就有說他的觀察不過是「熱脹冷縮」的現象而已。還有一位發言者「聲色俱厲」地質問他,「你說『總有一天太陽不再升起』是什麼意思?」那時的人在政治上都高度警覺,因為「紅太陽」就是專指毛主席的用語,而周在談到日出日落時可能是用詞不當或不小心說漏了嘴,因此,會場氣氛一度火爆。這種問話出自物理所書生之口,又在這種場合下,總讓人感覺很不協調,甚至有點滑稽。但我明白,這大概叫做「以毒攻毒」,文革中人們常常這樣互抓話柄,攻來攻去。回來後,我與幾位同去的同學談起周的觀察,我認為導致那些變化的因素太多,不過,由天體運行引起「固體潮汐」的影響,可能比「熱脹冷縮」更容易解釋他的觀察。他們贊同我的看法。事情就這麼過去了,我們也不再把「相對論」一事放在心裡。
但不到兩個月,清華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武鬥,兩派搶占樓宇,把學生趕走,使得在校住宿和吃飯都成了問題。此時聽說科學院剛成立了「批判相對論學習班」,因為那裡有熟人吳介之已在其中,我們幾個同學便決定到那裡去看看。
學習班的行政頭頭是天文台中年老成的黃硼,還有個副手物理所的陳慶振,但核心人物是北航的研究生吳介之。吳的腦筋和筆頭「像鬼一般地快」,在討論時可以迅速把眾人所說的集成文字,並朗朗上口。他引用奧地利物理學家玻爾茲曼(1844—1906)的一句名言:「雅致的事當留給靴匠[1]和裁縫去做。」(Elegance should be left to shoemakers and tailors.)[2],自謙自己不過是把大家的意見拼湊在一起的「總裁縫」罷了。但不久便被大家簡稱為「總裁」,有人還提醒道,「世界上除了蔣介石和日本自民黨的首腦,如岸信介,被稱為總裁之外,閣下是第三位。」
吳的近代物理基礎一般,但英文筆譯飛快,數學甚好,尤精流體力學中的湍流問題。來自物理所的人有北大畢業的吳詠時和清華畢業的郭漢英,從清華去的五個人,徐湛、張達華、季梁、李雲及我,都是工程物理系五、六年級的高班生,已上過電動力學等近代物理課程。吳詠時、徐湛、張達華和郭漢英物理概念紮實,邏輯思維清晰,後來都成了搞理論一等一的好手。沈乃澂是從計量科學院來的,從科大先後來過兩三位,只有一位朱清時留了下來。還有一位羅嘉昌是黨校搞哲學的,能言善辯,但盤算太多。
顯然,這些年青人湊在一起,已不再是周友華的「熱輕冷重」說的水平了。我們決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以往有關相對論的哲學討論及物理實驗的文獻細細查考一番。畢竟愛因斯坦並未因發現「相對論」得過諾貝爾獎,可見當時物理界對他在這個領域的學術成就爭議很大。於是黃和陳負責到圖書館去借來大量的外文期刊和書籍,分給大家去看。其中吳介之譯得最多最快,然後輪流傳閱討論。
在思想閉塞專一的文革年代,這些西方學界的爭論無疑給大家啟發很大。記得吳介之譯過一篇論文,忘了作者是誰,裡面有一句話,大意是「當科學家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登上了知識的頂峰,在那裡卻遇見了『恭候以久』的一批神學家。」這句話令大家印象深刻,感嘆不已,也開啟了我個人對上帝的認知。多年之後,業已成名的科大朱清時同學皈依了佛門,他在對公眾講學時說了同樣的話,但只把「神學家」改為「佛學家」。他沒有提到此乃前人所言,只是改動了一個字,便成為他的「偈語」,為人廣為傳頌,這令我驚異。
然而,後來有人據此便把現代物理與佛學硬扯在一起,大談「科學的終結竟是信仰的起點」。我卻以為,科學與信仰不是終點和起點的關係。科學並非是要用來迎合或詮釋宗教,而宗教也不應替代或約束科學。愛因斯坦講過,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足的科學,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宗教。」上帝無需科學的證明,科學也無法證偽上帝。科學與宗教信仰,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東西,它們可以並存,即使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一個嚴肅的科學家與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有著某種相通的地方,那就是一顆謙卑受教的心,以及一種追求真理的熱忱和勇氣。在我看來,基督宗教精神實際上是人類的一種高尚信念和情感的升華,一種對於大愛、公義、聖潔、永恆和超越的追求與信心。
科學院的條件很好,以批判的名義,可以看到許多西方的資料。因為量大,我們幾個學生乾脆就住在那間會議室,晚上加班,白天在科學院的食堂買飯吃。一天晚上,吳詠時的弟弟,吳建時,來到我們住處。吳和我同系同級,人極為聰明,是學校的尖子生。他來是因為一人在家悶得抓狂,聽說這裡有一幫同學,便跑來要和我們打橋牌。那時我們中間,也許只有清華的張達華會,於是一拍即合,吳和張便開始教我們玩。他們倆教得很正規,從誰洗牌、誰切牌、誰發牌及順序,到如何叫牌、怎樣問尖問K、以及記分都有嚴格規定。張警告說,牌場上要是有一點差池,亂了規矩,人家就不會跟你玩了。於是我們不敢造次,一板一眼地學,很快也就上了癮。只是記分太複雜,通常由吳和張細細地算,一筆不苟。
到了七月,學習班寫出一篇《相對論批判》的文章,準備作為「成果」上報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各位。大信封都裝好了,就要送走之前,學習班的負責人黃硼說,再檢查一遍吧!結果在給林彪的信封中,竟發現一張橋牌記分紙被夾在其中,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我們」、「你們」,每局的分數,還有些「哈哈哈」之類的胡話和塗鴉,黃見了差點沒背過去。這除了「大不敬」之外,還因為「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以好打橋牌聞名,於是橋牌在「革命者」看來,也一定是「資產階級」的玩藝。好在事後黃沒有不准我們再打牌,但我們從此也的確很少再玩了。
下面談談我們在物理方面做了些什麼事。
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提出了兩個基本原理,第一個是「光速不變原理」,即在所有慣性系中光速各向同性,等於常數值c,與座標變換無關。第二個是「狹義相對性原理」,即各慣性系物理定律相同有效,平權等價;真實的物理定律必須具有洛侖茲變換的不變性。由此他建立了一套嶄新的四維時空觀念,包括由洛侖茲變換引出的同時性的相對性。這是物理學、以至人類理性與思維的一個偉大的躍進,並非是單純的經驗歸納所致。
但經過討論,我們覺得,這兩個原理有些重複,顯得過強。從經濟的原則來看,只要肯定在一個慣性系(標準系)中,真空中單程光速各向同性,等於常數值c,且與光源運動無關,再加上「相對性原理」,便可得出「光速不變原理」。
在查找文獻之後,我們認為在地球這個慣性系(待定系)中,實驗直接驗證的只是雙程光速各向同性,等於常數值c,且與光源運動無關。這比所有慣性系中「單程光速不變」的假定,要弱一些。因此想到,如果我們退一步,暫時放棄「相對性原理」,僅從滿足這個實驗結果出發,看能得出什麼樣的線性時空變換?
部分推導的結果,可見附錄,這裡簡要說明幾句。
我們導出的待定系與標準系之間的時空變換關係,很接近相對論的洛侖茲變換,但它有一個待定因子f需由實驗進一步決定。如果f=β=v/c,就是洛侖茲變換。在地球系中,可以認為,f~β=v/c<<1,即與β同數量級。
標準系的時空度規張量與相對論一致,表明它是正交的膺歐氏空間,光速各向同性。但在待定慣性系中,如果待定因子f≠β,度規將不是正交的,對光的傳播而言,群速度各向異性。換言之,光速可能在一個方向上大於c,在反方向上則小於c,但可以證明雙程光速的確是不變的。
在狹義相對論的情形,協變張量gμν與逆變張量gμν沒有區別,但是對於非正交變換,四度矢量及張量有協變與逆變之分;此外,要看出由於引入待定因子f所帶來的差異,計算往往要展開到高階項,因而數學推證繁複。無論如何,我們終於把電動力學及場論里所有的重要關係,用這個新的觀點又重新推導了一番。
最後的結論是,由於f與β同數量級,在目前的實驗精度範圍內,用這個帶f的洛侖茲變換,同樣可以解釋所有已知驗證狹義相對論的實驗,包括運動的時鐘變慢,尺度變短等狹義相對論效應。然而,不同之處在於,由它推導出來的動靜質量關係式,由於這個f因子的存在,在某些座標系中,當粒子速度達到或超過光速時,粒子質量不會變成無限大,因而不存在對於光速不可超越的限制。
以上這些是我根據當年存留的一份資料回憶而寫。
關於哲學部分的「批判」,因無資料,已記不準確我們都說了些什麼。不過,那時所謂的哲學批判,多為概念生搬硬套、戴帽上綱,這都是文革時的風氣,實不足為訓,當引以為戒。但是,總的印象是我們強調物質的相互作用及時空的物質性。的確,沒有相互作用,物質的存在便沒有意義,而沒有物質的存在,時空也就沒有意義。因此,宇宙或時空就是相互作用著的物質存在之總和。這聽起來很乏味,是不是?剛好,最近有一位對佛學感興趣的朋友問起:「萬物皆空,那物質究竟是否存在?」我答道:「『萬物皆空』只不過是佛教宣揚的一種處世心態,千萬不要把它與真實世界混為一談。『古代一個哲學家反駁唯心論,他說,你要是懷疑這碗麥飯的物質是否存在,那最好請你吃下去,看飽不飽。』(魯迅,《智識過剩》);或者,你要是懷疑一堵牆壁的空間占有性及其相互作用,那就請『去牆數尺,奔而入』,看你是否能『緣起性空』、俯首捏訣而過,還是會『頭觸硬壁,驀然而踣』,以至『額上墳起,如巨卵焉』?(蒲松齡,《嶗山道士》)」
然而,這裡最奇妙的卻是,物質結構及其相互作用的規律又是可以被認識的,其中的一些甚至可以用數學形式準確地表達、計算和預測,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神跡」。那時我們在文獻中讀到過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宇宙最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它竟然是可以思議的。」這話給了我極大的啟示,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從上述物理工作來看,我們那時並非是要推翻狹義相對論,而只是想要看看現有的實驗能夠容忍理論後退或擴大到什麼地步。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顯然是近代物理學的基礎之一,它的對稱與簡潔堪稱之為美麗或優雅,這對物理學家而言有著永恆的魅力。我們所做的推演,似乎把絕對時空或以太(Ether)又帶了回來,破壞了那完美的四維時空對稱性,儘管很微小。但從另一方面來考慮,這會不會只是一種四維時空對稱性的破缺(Symmetry Breaking)?會不會因此而為實體粒子超光速運動保留可能的一席之地?會不會與「暗物質」、「暗能量」及「宇宙膨脹」等新發現有什麼關係?這隻有存疑,讓以後更多的實驗或觀察來回答了。
五十年後的今天,平心而論,我仍認為在哲學上強調時空的物質性及物質的相互作用,並沒有什麼大錯,我們在物理方面所作的那些嘗試,即使思路與演算都有錯誤,也無可厚非,因而並不覺得羞恥與追悔。相反,我倒很懷念文革時那一段罕有的「桃花源」式的時光。那時,我們看到了國外二、三十年代物理學界思想的活躍,他們對起源不久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爭論很多。這也開啟了我們的思想,在討論會上,大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互通信息,互教互學,個人並不藏著掖著些什麼。例如,吳詠時曾專門為大家講解了場論中有關的張量計算,令我獲益匪淺。記得吳介之也講過一課,是關於空氣動力學中超音速聲障的數學,即當物體速度接近音速時,它所受到的阻力趨於無窮大。在數學上這與近光速時質量增加的行為非常相似,但聲障是可以突破的。……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愛因斯坦晚年自述中的一句話:「自由行動和自我負責的教育,比起那種依賴訓練、外界權威和追求名譽的教育來,是多麼的優越呀。」
然而好景不常,近在咫尺的清華園內兩派武鬥越演越烈,毛澤東終於出手了。他派工宣隊來收拾那些不聽話的「革命小將」,因為「工人階級必需領導一切」,結果發生了著名的「七·二七」事件。之後不久,我就回校接受工宣隊的領導和教育,並參加已推遲一年多的畢業分配。
十月份,我告別了那個多事的清華園,奔赴青海指定的工作崗位,在那裡從事接受「再教育」的體力勞動。但我與後來分在張家口的吳介之、遼寧的徐湛及四川的張達華保持通信聯繫,繼續討論物理問題。在我離開之前,小組已注意到單、雙程光速的問題,並提出了待定同時性的變換關係。我到青海後,還用它算過「菲索實驗」,並給尚在京的吳介之去信,認為我們可以解釋它。69年10月回京探親,又見到還在那個「學習班」里堅持的一些哥們,他們已把帶q變換整理得十分專業化,作了系統的推導,並鉛印了一份內部討論稿。當時正值文革高潮,科研單位已無人搞業務,故為排印此稿,還專門找回科學院印刷廠的一些老師傅,因為只有他們知道怎麼對付有希臘字母和上下角標,及有微積分和矩陣的數學公式,但恐怕那時他們也是心神不定,匆匆忙忙,最後還是有不少排印錯處。
再後來事情怎樣結束的,我已不記得了。但在青海的十年裡,我始終對物理、數學及英文保持興趣。記得有一次在物理刊物上看到郭漢英的典型時空理論,我對其度規二次型的正定性有些異議,但投稿後被退回[3]。1976年初我給在天體物理方面已經知名的科大方勵之教授寫信,談了我對「典型時空」的一些批評和疑問。兩周後即收到方先生的回信,全文如下:
×××同志:
3月1日來信收到了。
你提的問題的確是存在的,對於典型時空所採用的度規,dτ並不總具有類時性,這從該文(2·2a)容易看到。所以,將ds=√g00dx0規定為原子鐘的讀數,不能在整個σ>0範圍中適用。
在宇宙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的曲率,是一種容許的設想,把不同的度規接連起來,廣義相對論中也是有先例的。當然,具體處理中,是可能有困難。
據我了解《物理學報》準備摘要發表對典型時空質疑的文章,也要刊登作者的答覆。但從目前作者準備的答覆看,典型時空中的一系列問題似未解決,所以很可能還要進一步地討論。希望你進一步地鑽研這些問題,以提出自己的意見。
這些看法,不一定對,供你參考。如有不妥,請不客氣地批評。
祝工作順利
方勵之,76·3·15
信寫得開門見山,坦言己見,並無保留,字跡工整,誠摯謙和,毫無客套與廢話。我與方先生素未謀面,想必是「文如其人」罷!現在寫出來,也算是對先生的一種紀念。
光陰似箭,斗轉星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門戶開放了。由於學業沒有荒廢,我順利通過了教育部關於派遣訪問學者的考試,於79年8月赴美開始從事快中子實驗物理的研究。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中關村那幾個月的時光以及後來的努力,也許生活對我會是另外一個樣子。無論如何,在那個「學習班」里,至少我學會了橋牌,它給我的生活帶來不少樂趣;但不幸的是,我也學會了吸菸,雖然量不多,而赴美之後,就完全戒掉了。
寫於6/2018,8/2020修改
注釋:
[1]郝柏林,《一段荒誕往事:「批判愛因斯坦」》,收入《負戟吟嘯錄——一個前沿戰士對中國科學的感懷》一書中,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八方文化工作室,2009。
[2]這裡,玻爾茲曼原來用的是「手套工匠」(handschuhmacher)一字,在德譯英時被誤為「靴匠」(shoemaker),此後英譯中亦照翻不誤,流傳至今。這是譯界,或更一般地,是信息傳遞中,「以訛傳訛」、「人云亦云」之一例。
[3]直到四十三年之後,2019年3月收到友人來信,我才知道我的那份稿件已被收入《關於「典型時空」問題的討論》,發表在《物理學報》1976年第25卷第4期。
附錄(數學推導,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