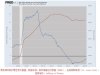重慶的冬天,比較陰冷,或者說,是把陰冷演繹到極致的冷。比如說我太太頭一回來重慶,記得戶外有12度,然後沒過兩天,她竟然生了凍瘡。北京則比較乾冷,小風兒殺氣騰騰,但是,重要的事情只說一遍,「羽絨服里莫要穿毛衣」,否則,一進屋你就像搬過磚一樣汗流夾背。波士頓還要不一樣一些,如果大冬天顯示有12度,還沒小風兒,然後又出大太陽的話,陽光直射半小時,能把你丫烤死。
家裡93歲老爺子的身體,新冠陽過之後感覺是一年不如一年了。2022年之前,一天能走一萬步,每天上街逛兩回,各種湊熱鬧,打望美女,樂在其中。陽了之後,每天走得了兩百米,趕緊停下來大喘氣,八抬大轎——我推的輪椅,馬上接駕。
這個冬天,左腳莫名腫痛,一個星期去了三回醫院,仍然查不出個所以然,似乎什麼都是好的,似乎好了一些,比如,不怎麼痛了,但是,仍然腫著。臘月二十九,我們老家的領導關心民眾疾苦,已經把老中醫帶來了家裡,看了一個多小時,開了藥,羅列了一些注意事項。
本來希望他的左腳可以和重慶的天氣一樣,在正月里好起來,現在看來,樂觀了一點,老祖宗講的「病去如抽絲」,不算瞎說。
大年初一的下午,太陽出來了,推著他去江邊逛了一大圈。一個固定打卡的地點,又讓他失望了,鎮上唯一的報刊亭,年初一不開門。老頭每天都要買報紙看,閱讀量巨大。亭子裡的老闆大老遠一看到老老邱同志,像打了雞血一樣衝出來:
「客戶你好,《環球時報》、《報刊文摘》、《新周報》,一共7塊錢。」
這個《新周報》,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個什麼報紙。
總之,大年初一這一天,精神食糧沒有買到,左腳仍然腫著。逛街逛到一半,革命的老同志已經在輪椅上睡著了。
我們小鎮上,有一條黃溪河,涓涓細流,在此地匯入長江。童年的時候,黃溪河不是細流,是一條小河,夏天河水會漲起來,淹沒了摸著石頭過河的石頭,父親和母親會輪流攙扶我們過河去小學上課。
那個時候,母親是我的右腳,父親是我的左腳。現在,右腳已經永遠離開我了,左腳腫痛著。
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老頭在輪椅上醒過來,說:
「他媽滴,還是美國人在搞鬼,又是貿易戰,又是病毒,又搞垮我們的股市,還把我的左腿搞成恁個樣子。」
如此這般,「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個講述了一千遍的故事又講了一千零一遍:抗美援越的時候,美國人就用了氣象武器,搞得天天下雨,泥濘不堪,我們支援的物資,根本送不上去。我和我的老兄弟小徐第一次聽這個故事的時候,都表示沒有聽過,老頭並不在乎我們有沒有聽過,說,你們懂個屁。
如果按照時下有理不「槓」非君子,三觀不對盤立即拉黑的思路,我和我家90後這父子關係遲早得陷入僵局。
不過,大年初一這一天,天兒暖洋洋的,而且為了他的左腳,已經搞到我的左膝蓋又脹又疼,但是一切以歡樂祥和為主基調,我提出我倆一起演唱一首他最熱愛的《紅梅贊》。
「來,我先起個頭:
紅梅花兒開,
朵朵放光彩……唱!」
「紅梅花兒開,
朵朵放光彩,
昂首怒放花萬朵,
香飄雲天外。
喚醒百花齊開放,
高歌歡慶新春來,新春來!」
老頭說:「不唱了,腳脹!」
我沒忍住頂了一句嘴,「要我說,你的這個左腳,肯定跟美國人沒得關係,只能叫『人窮怪屋基,瓦漏怪桷子稀』。」這是重慶言子兒,土話,我也不知道怎麼翻譯,大約是說,自己不找自己的原因老是把自己不幸的原因歸結到其他因素上。
這下捅了馬蜂窩,90後在輪椅上大聲批評:「你們這些小崽兒,不讀書不看報,天天刷手機,遲早吃大虧。」
我再也不敢吭一聲,想想,我們不僅讀書看報,而且還辦過報,只是比較難搞,越搞越難,快要辦出神經病來了,只能作罷。
故鄉的長江邊放了很多免費的桌球桌,讓老百姓鍛練身體,老頭這兩年看到那些活蹦亂跳的中老年老頭老太,滿腔悲憤,羨慕不已。
他觀看了一刻鐘總結說:「中美關係,小球推動大球,桌球也是有過大貢獻的呦!」
如此這般,我又必須得承認,我家90後的三觀,似乎又並不偏頗。
我說:「我的老同事採訪過中美桌球外交的見證者,其中有一個細節,說是那個最重要的美國球員叫科恩的,是個嬉皮士,他在北京訪問的時候,突然向周恩來總理提了一個預案外的問題,他問周總理,如何看待美國的嬉皮士運動?周總理回答說,年輕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可能會作出各種各樣的選擇,但最終他們都會選擇真理。」
大年初一的這一天,我講的這個小故事,說明我讀書看報,讓老頭琢磨了好久,表示很有意思。
回家的時候,我們住的這幢樓,進大門前有個小坡,外加一扇隨時自動關上的大門,推輪椅的人會非常不便,大門裡面,有兩桌打麻將的退休老太太,每天輸贏10塊錢左右,樂此不疲。
我推著老父親一到門口,總會有一個80歲左右的老太站起來,幫我們拉著門,幾個月如一日,我們說了一百多遍謝謝。
有一回我實在沒忍住:
「這個雷鋒老太是咋回事?又不是咱家傭人?」
老頭說:「哦,那是以前我們副縣長的太太呢。她年輕的時候,就是還沒嫁給副縣長的時候,有點經濟上的事,我就是負責偵辦的人,事情不大,都沒什麼錢,東西也退回了,我就找她談了一次,給上頭也匯報、擔保了,我讓她不要有負擔,好好工作。」
我說:「你擔保有個屁用。」
老頭說:「啷個沒得用,人家後來好多年都是先進,嫁的先生也很有出息,還當了副縣長,兩個娃兒都是大學生。有些事情,重一點,毀別人一輩子,輕一點,救別人一生。」
我說:「現在流行的話,槍口抬高一厘米,你聽得懂不?」
老頭說:「聽不懂,抬高一厘米鳥不是飛俅了。」
老太太有一天在樓下碰到我,說老頭的左腳腫痛哦,我說去看了一回,好像問題不大。老太很震驚,「還問題不大,你要高度重視,你們老頭是從來不說痛的人,他都說痛,肯定嘿痛!」
「以前反右的時候,你老爸的同事差點被打成右派,上面喊你老爸檢舉他,你們老頭說,這個人沒得問題,上面說,你不檢舉他,你就有問題。你們老頭說,『他沒有問題,我也沒有問題,其他無可奉告。』你老爸後來吃了不少苦頭哦,不過還好,最後兩個人都沒打成右派。」
如此這般,我們老頭的三觀是個什麼底色,「無可奉告」。
我在新年的時候幫他整理他讀的報紙,實在太多了,也找不到收舊報紙的人,只能堆在客廳的角落裡。有一天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連續有幾天的報紙,都折在同一個內容上:自由前進黨候選人哈維爾·米萊當選阿根廷總統、阿根廷股市狂飈、全國大罷工考驗米萊新政……
某一天輪椅出行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了一個問題:
「你看得懂一個叫米萊的人?」
他雲裡霧裡:「啥子?」
我說:「哈維爾·米萊,阿根廷的新總統,他在達沃斯喊了一句口號:『自由萬歲,媽的。』」
老頭又想了很久,突然有點小興奮:「這個人值得研究哦。」
我說:「研究個屁,他是美國人的走狗哦。」
這回輪到老頭沒勁了:「那倒是,貨幣都用美元了。」
正是這個莫名奇妙的話題,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成為了我倆在逛街的時候偶爾可以聊聊天,互動一下的動力,事實上我發現,他根本就是前讀後忘記,但是似乎有什麼神秘力量讓他非常關心這個「瘋子」的一舉一動,事實上,還推動了我大量閱讀有關米萊的幾乎所有內容。
有一天經過銀行門口,我說:「米萊有一句競選口號,『我要炸掉中央銀行,這不是一個隱喻,這是字面意思。『要得不,瘋狂不?」
老頭說:「字面意思是個啷個意思?」
我說:「就是真的炸掉,或者,高度準確地說,叫摧毀。」
老頭說:「因為阿根廷通貨膨脹噻,民不聊生,錢不值錢,國民黨反動派倒台的時候,我們買他媽一斤米要幾捆錢。」
有一天刷短視頻,看到一個金教授,在台上講,南美洲總是提供教訓,非常高興米萊再次提供一個教訓。我把短視頻給老頭看,他看了一萬年,耳朵也聽不見,饒有興趣地貼在右耳邊聽了半天。
我說:「一分鐘的短視頻,你硬是看到我把三國演義都讀完了。」
老頭把手機還給我說:
「投機分子。」
我說:「你這個老公安思想不對頭哦。」
老頭說:「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啷個剛開始就下結論是教訓。」
老頭說:「投機分子的特點就是你把他帶到派出所,褲襠裡面來一腳,他該說的不該說的、真的假的全部說了。」
我忍不住笑起來,破例給他買了麥當勞冰淇淋。
老頭吃著冰淇淋跟我說:「你說的這個人叫啥子,我又搞忘了。」
「米萊!唉,跟你講話太累了,麻俅煩。」
「還有你說的那個經濟學家,叫啥子克?」
「哈耶克,算了,你吃冰淇淋,要化了。」
「哈耶克,米萊,人就是要學習,不學習要落後。」
老頭的甜食整完了想起來一個話題,說:「你曉得不,米萊這個瘋娃兒,以前是踢足球的,後來發現足球救不了國,去學經濟學,當總統,救國,我覺得了不起,年輕人要有報國救國的志向。」
我說:「那萬一他反而害了國呢?可能性不會低於百分之五十。」
老頭說:「對頭!同意你說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毛主席講的這個滄桑,就是不斷改革、不斷發展、不斷前進,這是必然規律。」
我說:「厲害了我的老頭!雖然不知道你說的是啥子。」
有一天晚上,有一個企業老總的電話,講了很大膽的思路,和現在熱衷的企業出海有關,我琢磨了半天說:「不急不急,三思而後行。」
老頭推開門進來,說:
「我覺得這個叫米萊的人還有一個特點,有點像重慶崽兒,做事情果斷,不拖泥帶水,你覺得呢?阿根廷這個地方,報紙上說的,叫做國難當頭。國難當頭的時候,容不得三思而後行。」
我說:「重要的事情說兩點,第一,不要半夜三更偷聽我打電話;第二,朋友要做大事,我先冷靜分析,不拱火,沒得錯。」
老頭說:「那是那是,我的聽力不好,沒有偷聽,是你講話聲音大。」
我在新年的晚上亂翻書,錢穆注《論語》,在「三思而行」下面,注曰:「事有貴於剛決,多思轉多私。」
黃溪河流入長江的地方,總是有很多人釣魚,我還經過一家魚具店,生意不錯,叫「忘不釣」,無語。
讀大學的時候,有一年暑假我和朋友湯總去姐姐工作的絹紡廠玩,她的一個老頭同事嫌我們太吵,把我們帶到旁邊的魚塘釣魚,釣了一個下午,一條魚都沒釣上來,湯總沒耐心了,撲通跳進水裡,東遊西竄,冒出頭來說:
「日你媽裡面根本就沒有魚。」
要釣魚首先要確認水裡有魚,據說是芒格說的,反正魯迅肯定沒說過。我想哈維爾·米萊叫囂「國家是魔鬼發明的,上帝的制度是自由市場」,是不是他發現水下已經沒有魚了。
關於哈維爾·米萊的話題,在黃溪河邊,漸漸告一段落,天氣越來越暖和,老頭的左腳,慢慢有了轉機。甚至,在我離開重慶的時候,我還預約了阿根廷的作者,為我們帶來「自由萬歲」的米萊後續的內容。
在我家90後那顆「什麼都是美國人幹的」的心裡,似乎,還埋著「真理萬歲」、「報國萬歲」的三觀。
我們還未到互相拉黑的程度。
臘月二十九的下午,去重慶巴南區的中醫院幫父親拿好中藥,想起明天就過年了,應該去南山看看母親。
天下著小雨,叫了輛滴滴專車,山路彎彎,開了一半,師傅說:「你定位在西南門,你要去的這個南山龍園小區,還有別的門不?」
我突然有點小尷尬:「師傅,我要去的這個地方,不是小區,是一片墓園,你要是不想去的話,我可以換一輛車。」
師傅說:「哦,這樣啊,下雨,天冷,沒事的,你去好也叫不到車,我在那邊等你。」
我在南山龍園的半山腰上呆了半個小時,把這一年所有的事都和母親講了一遍。雨越下越大,墓碑前放的白色小花,心事重重地散開來,像這一年無數個哀傷的碎片。
重新把花紮好,壓在一塊石頭下面,我說:「媽,我回去了。」
回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說:「爸,我去看過我媽了。」
老頭說:「哦。山上還好不?」
我說:「山上有啥好不好。山上的人只希望山下的人好。」
他說:「那倒是,你看我這個左腳,南山也爬不上去,心有不甘啊!」
記得前年底母親在ICU里去世的時候,我還在國外,我的老同事去家裡告訴了他,幾個同事作好了所有準備,甚至連救護車都安排了,老頭聽了看著窗外,沉默了好久,回頭說:
「我曉得了,辛苦你們了。」
這是疫情三年他遭到的第二次沉重打擊。
2020年初,我的60歲的哥哥心梗去世。老頭有一周都沒怎麼說話,有一天突然問我一個問題,他說:
「文化人,問你一個問題,老公死了的女人和老婆死了的男人,都有一個特定的稱呼,但是娃兒死了的人卻沒有,是不是?」
我說:「沒有。」

邱兵,重慶巴南人,李植芳老師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