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在學校官網發文披露,該校學生詹姆斯·李在學院路交叉口被火車撞倒後身亡,年僅19歲。
這位普林斯頓大學大一的新生才華過人,精通日語、西班牙語、義大利語等多國語言。
他的母親李翊雲是繼哈金之後,在西方文壇上第二位以英文寫作而名聲大噪的華人作家。

●李翊雲
李翊雲曾在2021年的一場對談中談到自己的小兒子,說「他特別喜歡看《三體》,特別喜歡看劉慈欣,也看劉宇昆的作品,還有特德·姜。他不會看我的作品,會看經典的偵探小說,比如《福爾摩斯探案集》。」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7年前,李翊雲的長子文森特就因自殺身亡。如今,年過半百的她再度遭遇喪子之痛。
熟悉普大環境的學生強調,列車經過學院路口時,通常都會有響亮的警示聲,一般行人很難撞上火車。
因此,有人推斷,李翊雲的次子也是自殺的。

●李翊雲和兩個兒子在一起
再向上追溯,李翊雲本人也曾因為嚴重的抑鬱症而兩次輕生。
當死亡的魔咒施於這個本應幸福的家庭時,我們似乎更想探尋悲劇背後的故事與肇因。
01移情「繆斯」
「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悲劇感往往是在強大落差下產生的。如果翻開李翊雲的人生履歷,我們會驚嘆於她的光環如此耀眼。
1996年北大生物系畢業後,她遠涉重洋到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免疫學,並在2000年獲得碩士學位。隨後,她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免疫學博士學位,轉而從事寫作。
2010年,李翊雲獲得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麥克阿瑟」基金會的評審認為,李翊雲的英文寫作反映出其母語的語調及文化,這給英文讀者帶來一種別開生面的體驗。那一年,她還上榜《紐約客》「最值得期待的年輕作家。」
短短兩年後,她成為了第一位榮膺歐·亨利獎的華人作家。
2013年,李翊雲受邀擔任第五屆「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2020年,李翊雲因作品的「形式美和大膽的想像力」而獲溫德姆·坎貝爾獎和古根海姆獎。2022年,李翊雲入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一年之後,她又憑藉新作《鵝之書》獲得福克納文學獎。
因創作成就斐然,李翊雲被認為會是第一位獲得諾獎的華人女作家。
但她小時候從來沒有夢想過會成為一個作家,儘管對文學的熱愛就像天然的基因一樣深植於心。
和同代人一樣,李翊雲成長於閱讀資源頗為匱乏的環境中,她如饑似渴地閱讀任何可以得到的文字,包括「魚販不要了的舊報紙,連環畫上的高爾基自傳三部曲,托爾斯泰《復活》的報刊連載,圖書館借來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詩》」,此外她還大量閱讀英美文學巨擘狄更斯、托馬斯·哈代、D·H·勞倫斯、海明威等人的著作。對於中國的古典詩詞她更是如數家珍。

讀書為她暫時屏蔽了周遭的種種難堪與煩惱,甚至讓她挺過了那些充斥著家庭暴力的歲月。
雖然醉心文學,李翊雲上大學時卻選擇了一個與她的興趣大相逕庭的專業。
到美國深造後,她將成為一名業界專家的方向清晰可判,連人生的道路似乎也一眼能望到邊,這種沒有任何挑戰的確定性讓她對未來產生了懷疑。
讀碩士時,因為實驗任務很重,大家紛紛尋找減壓的方式,不少同學選擇了園藝來解壓,李翊雲卻報了一個社區寫作培訓班。
在那裡,她發現了自己對寫作的濃烈興趣,於是決定離開科研,嘗試英文寫作。
她的高中同學對其予以勸阻,「我不相信你能寫成,你在中國長大,你怎麼去寫美國的上層和主流社會?」她的丈夫也提醒她,比起科研,寫作對她的索取會更多。但她「去意」已決,告訴丈夫,給自己三年時間——如果三年結束,寫作還沒進展,她就去讀MBA,或法學院。
2002年,李翊雲在The Journal雜誌上發表散文《充滿蟬聲的夏天》。2003年,老牌文學期刊《葛底斯堡評論》發表了她的散文《那與我何干?》。那年的秋天,她的小說《不朽》被《巴黎評論》在自由來稿里選中,被讚譽為「一篇堪稱完美的小說」。
《巴黎評論》的編輯布麗吉特·休斯在採訪她時說,發現李翊雲的寫作才華,是比自己當上《巴黎評論》的主編更令人興奮的事。
02「我有信心扮演我的存在」
在英語文壇一鳴驚人的李翊雲很快就成為了媒體廣泛關注的對象。2004年,她獲得了《巴黎評論》年度新人獎。權威文學雜誌《格蘭塔》和《紐約客》也分別命名她為美國最傑出的青年小說家之一。
不久,李翊雲考取了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
這個知名的創意寫作項目全美排名第一,聲名遠揚,培養出了17位普立茲獎得主、4位美國桂冠詩人,以及眾多國家圖書獎、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
它附屬的「國際寫作計劃」由著名華人作家聶華苓及其丈夫、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共同創辦。很多中國作家:王蒙、北島、王安憶、阿城、莫言、蘇童、余華等,都參加過該計劃。
在「作家工作坊」的嚴苛寫作訓練,讓李翊雲於2005年獲得了愛荷華大學藝術創作碩士學位,蘭登書屋很快買下了她短篇小說集的版權,並於同年推出了她的第一本書《千年敬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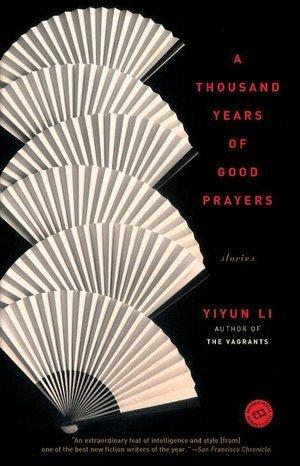
●《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
這部短篇集以90年代的中國為背景,從人潮洶湧的北京、廣袤蒼涼的內蒙古,一直寫到了大洋彼岸的芝加哥,最終摘取了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美國筆會海明威獎和英國衛報新人獎等多項大獎。
出任評委會主席的克萊爾·阿米茨泰德稱讚《千年敬祈》一書:「她所講的故事衝擊著人們的心靈,即使合上書很久很久,它們仍然在不斷地膨脹發酵。」
2008年,著名華語影視導演王穎把《千年敬祈》搬上銀幕,俞飛鴻出演了重要角色。

●俞飛鴻主演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千年敬祈》
繼《千年敬祈》後,李翊雲又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金童玉女》、長篇小說《漂泊者》。從《千年敬祈》到2014年發行的長篇《比孤獨更仁慈》,李翊雲這一階段的作品大多發生在中國,或以中國人為主要人物。她坦言,一個人和母語之間的聯繫,其緊密程度是超乎想像的。在祖國的成長經歷和所見所聞,是她用英語寫作的最大源泉。
在布麗吉特·休斯看來,李翊雲或許的確為英文世界注入了寶貴的中國經驗,但更重要的是她不同於其他作家的特質:「對時間的持久興趣,對將自己視為獨立個體的追求,一種拒絕服從任何期待的執拗,無論這期待來自他人還是她自己。」
因此在旅美華人作家中,李翊雲是個無法被歸類的「異端」。
此外,她厭惡陳詞濫調,反對有章可循的「技法」,抗拒美國寫作坊教授的金科玉律。
她了解自己作品的價值,並會堅定地捍衛它們的稀缺性,哪怕被人視作「敝帚自珍」。在修改首部長篇《漂泊者》時,李翊雲的編輯凱特·梅迪納勸她去掉一個年輕女性角色臉上的胎記,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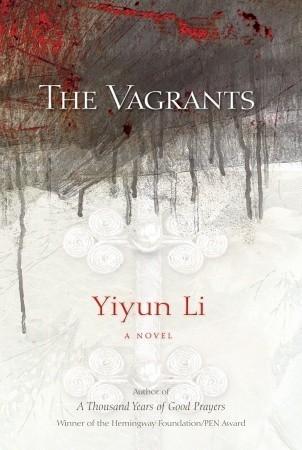
●《漂泊者》(The Vagrants)
此後,她不再採納梅迪納的建議。梅迪納是一位資深編輯,與眾多作者都有過密切合作,包括南希·里根。面對這位「無法被馴從」的作者,她無奈地對別人說:「翊雲不好管。」
李翊雲曾在文章強調:「我有信心『扮演』我的『存在』。」
有人說,「如何不被低估、如何證明自己大於肉眼所見,是許多移民畢生的需求,也是動力。對用第二語言從事寫作的創作者來說,或許更是如此。」
但李翊雲擁有自己的底氣與自信。迄今為止,李翊雲已出版六部長篇小說、三部短篇小說集、一部回憶錄,很多作品被翻譯成西班牙語、義大利語、法語、日語等十幾種語言,她也因此成為用英語創作成就最高的華人作家之一。
03原生家庭之殤
李翊雲的成功被視為海外華人勵志故事的樣板,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刻苦攻讀、她的出國留學,其實都是為了逃離自己的父母與家庭。
小說家英格博格·巴赫曼曾寫過,「我正在用被灼傷的手書寫火的本質。」其實這也是李翊雲的感受,她的寫作講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關於生存與掙扎,關於衝突與人性的戰爭,但光怪陸離背後,是她承受的巨大創傷。
李翊雲出生於北京的一個四口之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的母親是一名優秀的教師,受到一代代學生與家長的尊敬,但在家中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父親作為核物理學家,是母親經常責罵的對象。「面對驕縱跋扈的妻子,他的應對方式永遠是無節制的退讓和自我麻痹。」

●1977年,李翊雲一家四口合影
在兩個女兒中,母親偏愛出色的小女兒,但母親的忽冷忽熱和畸形的愛令李翊雲難以喘息。
李翊雲說,「很早之前,雖然還無法將其訴諸言語,我就知道:母親才是這個家中唯一的孩子。比起母親的憤怒,我更害怕母親的眼淚。巨嬰式的母親,需索無度。她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失控得幾近病態,家中每個人因此都不得安寧。
她說,我,這個她唯一深愛的人,活該得到最殘忍的死法,因為我不懂感恩。」

●李翊雲(右)與父親、姐姐
在一種扭曲窒息的氛圍中生活,「出逃」成了一種必然之選,後來當李翊雲放棄可以給她帶來光明前景的專業,而從事作為「情緒出口」的創作,也源於對長久積壓的痛苦的一份宣洩,對人生真相的一種追索。
後來,她在美國堅持用英文寫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的母親不會英文,這門外語於是成為了一道厚厚的「屏障」,將母親的審視與操控阻隔於外,李翊雲也藉助這種方式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自由:
「當一個人用新的語言記憶時,他的記憶就有了一條分界線。在那之前發生的,可能是別人的人生,也可能成為某種虛構。」
她試圖通過構建新的語言體系,來摒棄過往,完成自我救贖。
但這個過程非常艱難。
創作期間,李翊雲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根據《衛報》報導,整整10年,李翊雲都在午夜到凌晨四點之間寫作,還要平衡家庭和白天的工作。她曾認為自殺是「一個合適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2012年,李翊雲兩次自殺未果。
李翊雲因為抑鬱症第二次入院治療結束後,加入了一個康復項目,然而那些康復項目對於一個心靈受到長期戕害的人而言,顯得漫長而微弱。她常常生出強烈的願望:我要是從未出生過就好了。
李翊雲在住院治療期間,喜歡一個人去花園,沉浸於書籍的世界,一讀就是好幾個小時。別人覺得她看上去安靜平和,不能理解她為何會有自殺這種念頭。她說她表面最平靜的時候,是內心最激烈的時候。

「天人交戰」於她而言,是常態化的內心戲碼。面對命運的弔詭與冷酷,她拒絕無謂的妥協與和解。
她想起父親曾經灌輸給她們的宿命論——「只要相信宿命論就會讓一個人看起來平靜、無所不能,甚至是開心。」這是她當年與姐姐唯一的「護體」。但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無法掩蓋那些被深深壓制的悲傷、無助與絕望,它們的汁液滲透到了每一寸肌膚里,甚至長成歲月的紋理,以至於她後來無論用什麼方式,都難以將其徹底清除。
無法選擇的出身與家庭,成為她一生都擺脫不了的「宿命」,而這種「宿命」,成為流動的沙漏,最終影響到她與下一代的相處模式。
在李翊雲的記憶中,一天下午,她與小兒子坐在長凳上等待大兒子下課,小兒子把手放在母親的手上,但是她卻無法理解:
「我知道那一定很舒服,並且是天下最自然不過的事了。一定是這樣的。不過我突然覺得我無法理解它。我能接近理解它,但是那只能是作為人類學家的理解的一部分。」
儘管她篤信,日常的親密關係比外部的驚濤駭浪更值得書寫,但在原生家庭中無法獲得健康之愛的「殘缺」,讓她在自己成為母親後,也難以做到與孩子真正的水乳交融,因為那種自然而然的親昵無間、溫暖明亮的情感慰藉,是她不曾擁有過的生命體驗。
起源於上世紀50年代的「家庭系統心理學」認為,「家庭是一個系統,家庭中的任何事件都會在每一個人身上留下痕跡……愛與恨都能夠通過家庭一代代傳遞。過多的創傷徹底改變了生命感覺,並且在家庭的集體無意識中留下了足以導致更多苦難的陰影。」
2017年,李翊雲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教授,她準備舉家搬遷到新澤西州去。但秋季還沒開學,命運卻與她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她16歲的長子文森特自殺而亡。

●李翊雲主持普林斯頓大學的小說研討會
此前,文森特還隨母親去看房子,「甚至對廚房、花園和他的臥室都有了計劃」,但新家還沒有搬進去,他就走了。
沒有來由的結束,對於活著的親人來說,像極了突然被推至無底的淵藪。
後來李翊雲在書中寫道:「我們買了你看中的那幢大房子……你要在就好了……沒有你,房子空蕩蕩的。」
04生命是一場漫長的療愈
更讓李翊雲悲慟的是,不久後她的父親也患病去世了。在醫院裡照顧病重的父親時,李翊雲猶豫了很久要不要告訴他外孫自殺的消息。
最終,她還是選擇了沉默,因為她覺得父親已經承受了太多的打擊。
她和父親都不擅長表達感情,直到父親去世,她都不知道父親為何總喜歡唱《北國之春》。《北國之春》裡有句歌詞:「雖然我們已內心相愛/至今尚未吐真情/分別已經五年整/我的姑娘可安寧」,是因為歌里有父親生前曾渴望的繾綣之愛和家庭的幸福嗎?
不得而知。包括對於文森特的死,她同樣百思不得其解。
曾經,「她致力於將自己和生活藏在小說里」,兒子去世後,她意識到逃避沒有意義,決定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對兒子之死,於是就有了2019年出版的《理性終結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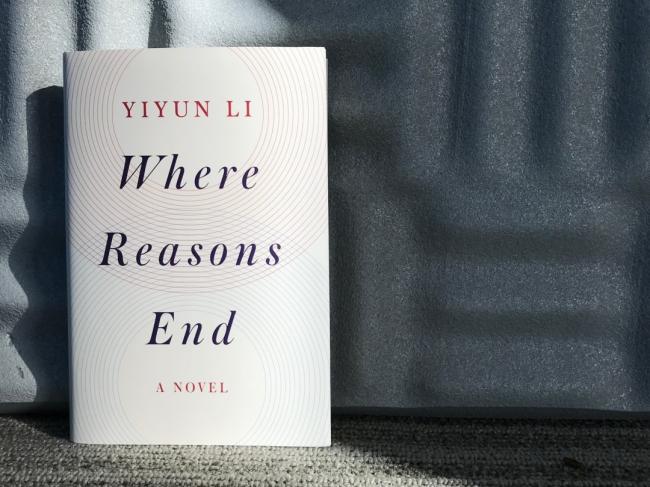
●《理性終結之處》(Where Reasons End)
暢銷書作家伊莉莎白·麥克拉肯稱,這本書是「關於世界上最悲傷的事情」。
小說中的母親特別想知道,一個身姿輕盈如鹿,喜歡閱讀、音樂、烘焙,能輕易地用他的蛋糕、鮮花、歌聲占滿整個空間富有活力的少年,為什麼會選擇結束生命?死亡究竟意味著什麼?母親是否能夠拯救自己的孩子?
在書中,她調動小說家的想像,在時光隧道里,與逝去的兒子進行了一場不可能的對話。
兒子:我非常愛你,希望我沒有傷你的心。
母親:哦,別那麼說,令人傷心的是生活。
兒子:你是個好母親。
母親:沒有好到能使你留下來......
與其說這是一份困惑,一種自責,不如說是一場與自我的對話,一次省察,她希望自己能懂得兒子的選擇,就像理解當年她自己的那些行為一樣。
即使是在最難熬的時刻,她也習慣性地微笑,「我時不時會停下來聽正在吠叫的鸚鵡,它不知道從哪裡學來一句,『那隻狗的事我很抱歉!』……所以在寫的時候,就經常被它逗笑。」
「笑」是對正常生活的感知,也成為陷於泥淖之中的人們的一根稻草,哪怕它如此輕盈,不堪一握。

●李翊雲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家中
她曾在與抑鬱症交鋒期間,讀過多位作家的信件、日記、傳記和作品,他們有的受困於不幸的家庭關係,有的被惡疾纏身多年,有的背井離鄉一生坎坷......「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像時間流過每一個人,在他們的身上留下溝壑縱橫的烙印,這讓她愈發清晰地感受到了命運的不可理喻之處,當追問沒有必要,當同情變成對普羅大眾的悲憫時,她更願意以實際行動去填充生命的虛無,去超越那些似乎永無止境的痛苦。
兒子離開的那年冬天,她訂購了25棵風信子。此前的秋天,她種下了800棵。
「風信子」寓意生命與愛戀,她希望天堂的兒子能收到來自母親的思念。
2020年,《我該走了嗎》出版,這是李翊雲首部被譯成中文出版的長篇小說,也代表著她願意進一步拆除心靈的藩籬,去直面那些被割裂與深埋的經歷,整飭曾傷痕累累的精神原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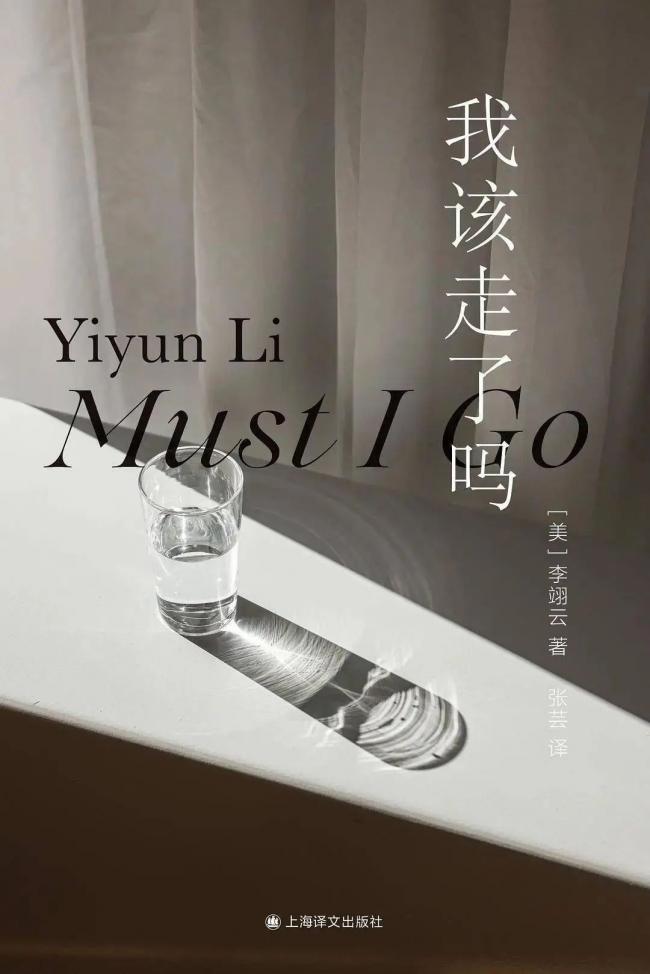
●李翊雲首部被譯成中文的長篇小說《我該走了嗎》,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始終、永遠的文森特(李翊雲長子)」
同時,更為了「從我的生命寫進你的生命」。眾生皆苦,天意無常,所以,她在深味諸般痛楚與心碎後,渴望能從文字的世界裡,從無邊的幽暗中「升起火光,讓從寒冷中趕來的人,可以坐下來烤烤火」。
美國作家西格麗德·努涅斯對這本書的評價展示了她的深刻理解:「《我該走了嗎》帶我們進入李翊雲熟悉而有力的情感領域。它精妙地探索了我們所愛的、失去的和哀悼的將如何塑造、恢復和重塑,讓我們成為現在的自己。」
05無解之謎
在李翊雲早期的短篇小說《善良》中,講述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女孩無法接受自己養的小雞就這麼死了。她於是去了廚房,敲開一個雞蛋,把蛋殼洗淨、瀝乾,然後嘗試把死去的小雞塞進空殼裡,想讓它重新孵出。
李翊雲說,這就是一種絕望的復活,想要試圖回到開始,卻再也回不去了。
因為她曾經也對兒子如此呼喚:「多希望你還在這裡,多希望你還在身邊。」
但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如今,李翊雲的幼子也過早離世,如果代際遺傳的不幸成為悲劇的肇始,那麼,自我的覺醒與關係的重建是否可以為身處困境的人們指出一條路徑?
戛然而止的生命,與未盡的長途,有太多遺憾與難解之謎,它們無法彌補,也難以求證。在《理性終結之處》裡,兒子生前留下了一個電子文檔,母親在和丈夫商量後,選擇不打開它。「無法知道答案想必最接近人們所說的傷口」。
創傷也許只會被撫慰,從不會消失,但它的存在卻是生命無法迴避的構成,亦如廢墟之於大地,彤雲之於天空,亦如愛,之於所有的破碎。
在書的結尾,李翊雲以反問的方式表達了對命運的參悟:「深淵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人自然棲居的地方?我們是不是可以像接受頭髮或眼睛的顏色一樣,接受痛苦?」
就像當年她種下的那些風信子,長在黑暗的泥土裡,卻開在每一個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