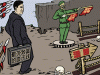讀過初中,就都背過《正氣歌》,知道有一種正氣,乃「在齊太史簡」。
如果有幸連高中都上過,就會學過「在齊太史簡」的相關典故,即「崔杼弒其君」:齊國大夫崔杼殺了齊莊公,齊太史秉筆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把他殺了。太史的弟弟承兄職(那時史官都是家族世襲制),還是這麼寫,崔杼也把他殺了。又一弟弟頂上,依然是這五個字,崔杼再殺。沒想到,太史的第三位弟弟,沒有被三位哥哥之死嚇倒,五字照寫不誤,而連殺三人的崔杼,終於被這種正氣嚇退,不再殺人了。更感人的是,這時候齊國南方另一負責記史的「南史氏」,聽說太史全家被殺光,帶著竹簡就往齊都趕,走到半路聽說「崔杼弒其君」已被寫進歷史,才放心回家。
崔杼固然殘暴,史官固然正氣,這事在今天看來,令人唏噓的還是,崔杼再怎麼大權在握,也還得尊重史官的專業性——只有被認證的、家族傳承的史官燒錄的史書,才是權威的。所以崔杼只能用殺人來逼史官按他的要求寫史,沒有換掉不聽話者,再叫一個親信當喉舌。
但是,僅有唏噓是不夠的。崔杼為什麼弒君,才是問題的關鍵。
說起來還得感謝《左傳》,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講得一清二楚。看完你就明白,無論古今,哪個男人站在崔杼的位置上,他都會起弒君之心。
事情還得從崔杼娶寡婦棠姜說起。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崔武子即崔杼,他有一家臣叫東郭偃,東郭偃的姐姐東郭姜嫁給了齊國棠邑(今山東平度東南)大夫齊棠公,所以名棠姜。這一年(前548),齊棠公死了,東郭偃駕車帶著崔杼去弔喪,崔杼一見棠姜,驚為天人,便對東郭偃說,幫我個忙,讓你姐嫁給我吧。
人家剛死老公,你來弔喪,卻說出這樣的話,作為大夫,確實不妥,說白了,也是一種權力傲慢的表現。但身為家臣,東郭偃不敢直接頂撞,只是說,您姓姜,我們家也姓姜,同姓通婚,不行的。
崔氏是齊丁公的後代,東郭氏是齊桓公後代,都是姜姓,按當時的禮俗,同姓確實不能通婚。
但崔杼為了娶到心儀的美女,還是請負責占卜的官員為他起卦,得「困」卦之「大過」,占卜者說,這是大吉。崔杼又去問對易經非常熟悉的大夫陳文子,陳文子對他說,有變卦,大凶,這女子會克夫,不能娶。這時崔杼已那啥上腦,不信邪,對陳文子說,她是寡婦,再怎麼凶,也由她前夫承擔了,我不怕。
於是就娶了棠姜為妻。
沒想到,剛娶過來沒多久就出事了,「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齊后庄公(齊國先後有兩位君主諡號為莊,這是後一位)是好色之君,估計是崔杼請他到府上吃飯什麼的,總之是在某個場合見到棠姜,看上了,就跟她通姦,並「一發」不可收拾,「驟如崔氏」,驟是屢次,如是去,經常趁崔杼不在溜到崔府去共享婚房。
棠姜怎麼這麼容易得手,天生的水性楊花?
這倒不一定。有可能,一來是二婚,無所謂;二來,崔杼娶她,有點強迫性質,讓她不爽;第三,人家畢竟是國君,國君對大臣之妻進行人文關懷,你敢拒絕嗎?
那麼,崔杼知道嗎?
能不知道嗎?
問題是,這位齊后庄公,正是崔杼「確立」的。
莊公名光,原是齊靈公太子,但齊靈公不喜歡他,改立寵姬所生的公子牙為太子,並把公子光派去守即墨。靈公病重時,崔杼和另一權臣慶封聯手,殺了公子牙母子,把靈公氣吐血而死,然後把公子光從即墨迎回來上位。
自己確立的君主,戴著綠帽也要侍奉他啊。
可是,齊后庄公連綠帽也不讓崔杼戴,不斷加大力度羞辱他: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到崔家共享婚房之後,還順手拿了崔杼的帽子,賞賜給其他臣子。近侍勸他說,這樣有點過分了吧。莊公不以為然:「我不拿崔氏的帽子,難道就沒有別的帽子可賜人嗎?」
言下之意,就是故意要羞辱他的。相當於公開把崔杼的臉摁在地上摩擦摩擦再摩擦了。不過,這倒省去崔杼在家裡安攝影頭的麻煩。
開個玩笑。總之,換你是崔杼,你能不起殺心嗎?
更何況,沒有崔杼,就沒有莊公的國君之位。
從心理上分析,喜歡姦淫臣下之妻,也是大權在握者的一種宣洩,是權力傲慢症候群的一種臨床表現——不「臨床」,還真表現不出來。
問題是,莊公真的是精蟲上腦了,也不想想,人家既然有能力殺了前太子扶你上位,也就有能力把你弄下去換別人上來,這種事,終春秋之世比比皆是。不說其他諸侯,僅僅六十年前,莊公的祖上齊懿公,就是因為搶了臣下的妻子而被臣下所殺還拋屍野外的(見《左傳·文公十八年》,不贅述),還不夠引以為鑑嗎?
什麼叫不作不死,這就是了。
崔杼起了殺心,但還得有個機會。也是天助崔杼,莊公有一近侍叫賈舉,不知因為什麼事惹怒了莊公,曾被莊公鞭打過,但打過之後,卻沒趕走他,還留在身邊服務。賈舉懷恨在心,作為近侍,他對莊公羞辱崔杼一事最清楚不過了,也看得出崔杼已對莊公起了殺心,便想幫崔杼找個機會殺莊公。
這年的五月份,齊國的附庸國莒國國君前來朝見莊公,莊公在城北設宴招待莒子,崔杼稱病不出席。第二天,莊公借慰問崔杼的機會,又到崔府上想跟棠姜共建和諧。棠姜跟崔杼呆在內室,聽說莊公來了,兩人便從側門離開。這時便出現了讓人啼笑皆非的一幕:
莊公「拊楹而歌」。《史記·齊世家》作「擁柱而歌」。楹即柱,拊楹,是用手輕拍柱子帶節奏;擁柱,是抱著柱子。不管是拍還是抱,東漢經學家服虔在《春秋左氏傳解》中注釋:「公以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莊公以為棠姜不知道他來了,所以唱歌引起她的注意讓她出來見面。
腦補那場景,就差一把吉他了。不得不說,每個好色之君,內心都藏著一個多情的少年。
可是,莊公怎麼知道,這時候棠姜應該是跟崔杼達成了諒解協議,崔杼已跟賈舉串通,埋伏了甲士,要置他於死地了。《左傳》寫莊公之死這一幕,端的精彩非常:
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台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牆。又射之,中股,反隊(墜),遂弒之。
跟往常來偷情一樣,莊公進入崔家,賈舉就讓其他隨從留在外面,然後也跟著進去,並反鎖上門。莊公正痴情的唱「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結果棠姜沒出來,埋伏的甲士衝出來了。莊公一看情勢不妙,爬上崔家的高台求饒命,沒人理他;他又請求跟眾人結盟,許以高官厚祿,也不好使;最後哀求說讓我回到祖廟裡自殺吧,也不被允許。甲士的領頭者說:「國君之臣崔杼在重病中,無法聽從誰的命令。這裡靠近國君宮室,我們巡夜搜捕偷入私宅淫亂者,也不聽其他命令。」莊公急了也跳牆,被一箭射中大腿,從牆頭掉下來,眾人一擁而上,把他殺了。
崔杼當然不是什麼好人,他被莊公戴綠帽又偷綠帽,也純屬咎由自取;殺莊公,確屬以下亂上。但莊公因為這樣而死,不也是活七八該嗎?
雖是如此,也還是有忠於莊公的臣下殉死的。那些被賈舉擋在門外,想衝進去救莊公的,被殺了十幾個,其中有一個負責漁稅的大臣叫申蒯,趁亂逃回家,對他的家臣說,我把家人託付給你,國君被殺了,我得去殉死。家臣說您死了,我苟活的話,會玷污您的名節。說完一起赴死。
這樣的人,後人也沒資格說他們是愚忠。但是,名臣晏子的言行,倒是更值得點讚: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晏子得知消息,來到崔家門外,隨從問他:「要不要殉死?」晏子說:「又不是我一個人的國君,我幹嘛要殉死?」隨從又問:「那逃亡嗎?」晏子說:「又不是我的罪過,幹嘛要逃亡?」隨從說那咱就回去吧,晏子說:「國君都死了,我能回哪兒去?一國之君,難道可以這樣騎在百姓頭上胡作非為嗎?當臣子的,難道只是為了俸祿嗎?君君臣臣,一切應該從國家利益出發。所以,國君如果是為國而死的,臣下就應該殉死;國君為國而逃亡的,臣下也應該陪他逃亡。反之,國君如果是為一己私慾而死、而逃亡的,不是他最私寵之人,有什麼責任要陪他一起死?再說,確立他的人殺了他,我憑什麼要死,憑什麼要逃亡?可是,我又能回哪兒去呢?」
擰乾水分,「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這句,真是擲地有聲。
最後,晏子叩開崔府之門進去,頭枕在莊公的大腿上號啕大哭,然後又按臣哭君之禮,三頓其足才離開。這時有人對崔杼說,晏子非殺不可,崔杼回答:「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他是百姓仰望的好人,放了他,可得民心。
殺了莊公後,崔杼又跟慶封聯手重新確立了莊公異母弟為君,即齊景公。晏子還是不肯站他們,慶封又想殺晏子,崔杼還是說:「忠臣也,舍之。」(《史記·齊太公世家》)
所以,真正對歷史負責的史官,應該寫「君通崔杼妻,崔杼弒其君」,這才是客觀、中立、寫實的。不說莊公因何而死,只說崔杼弒君,那還是為君者諱,滑入另一種歷史虛無。
當然,因為秦火燒盡六國之書,所以齊國史書上除了「崔杼弒其君」外還有沒有別的,不得而知。但是,魯國史官記錄的《春秋》,也只有這一句:「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也不知道《春秋》原文就這樣,還是經過孔子定稿後才這樣的。《孟子·滕文公下》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修訂了《春秋》,天下的亂臣賊子都感到害怕。這話是說歷史真相自有讓奸人害怕的力量,但從只寫「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提「齊君通崔杼妻」來看,為君者諱的「春秋筆法」,確實也只是讓亂臣賊子害怕而已。
大膽猜測,能尊重史官專業性、權威性的崔杼,也許只是想讓太史在「崔杼弒其君」之前加上「君通崔杼妻」而遭到拒絕,才惱羞成怒殺人。因為,從一再不殺晏子看,該亂臣賊子還是有一定理性的。
所以,「在齊太史簡」這樣的正氣,今天得打個問號。可以這麼說,凡是不以鎮懾君主為目的歷史書寫,都是耍流氓。
2023-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