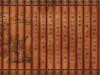中國古代美女的十大標準
7、楊柳細腰
纖、柔是中國古代美女腰肢的審美標準。
纖腰是自古迄今女性美的一個重要標準。《韓非子?二柄》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說明兩千五百多年前追求細腰已經在楚國形成風尚,「楚腰」也逐漸成了細腰的代名詞。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的「腰如束素」,將腰比喻成一束白色生絹,也反映了楚國人對細腰的欣賞。其實不僅楚好細腰,漢朝亦以纖腰為美。杜牧有詩云:「楚腰纖細掌中輕」,這「掌中輕」說的是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漢伶玄所撰《趙飛燕外傳》描述飛燕名字來歷時說她「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譙川秦醇子所撰的《趙飛燕別傳》則記載她「腰骨纖細」。魏晉南北朝時期同樣以纖腰為美。《南史?徐勉傳》記載南朝梁武帝賜給徐勉很多女樂,其中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這種以纖細為美風尚在後代一直延續下來,如曹植《洛神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謝靈運《江妃賦》「小腰微骨,朱衣皓齒」,梁簡文帝蕭綱《詠美人看畫詩》「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蕭綱的兄弟蕭繹《採蓮賦》「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李賀《將進酒》「皓齒歌,細腰舞」,柳永《促拍滿路花》「楚腰纖細正笄年」,朱敦儒《南鄉子》「宮樣細腰身」,王實甫《西廂記?驚艷》「解舞腰枝嬌又軟」等等,說明歷代都喜歡細腰。溫庭筠《張靜婉採蓮曲》中有「抱月飄煙一尺腰,麝臍龍髓憐嬌嬈」,腰圍只有一尺,可知細到什麼程度;柳永《木蘭花》「酥娘一搦腰肢裊,回雪縈塵皆盡妙」,一把就可以握住,比一尺細腰更勝一籌。還有更絕的,有的評書裡邊講:「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一點點,楊柳細腰賽筆管」,拿細腰和筆管比,什麼概念?
腰肢之美,不僅在於其纖細,還在於其柔軟、柔韌。柔並不是弱,而是要表現出一種韌性,柔而有力。如南朝梁羊侃的小妾孫荊玉,能反身貼地,銜得席上玉簪。若能像孫荊玉一樣,「反身貼地」,腰部定然是柔而有力的,這才能體現女性的柔韌之美。還有上文提到過的白居易詩句「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誇讚小蠻的腰象楊柳的枝條一樣纖細柔軟,可謂膾炙人口。白居易之後,用楊柳形容細腰似乎是約定俗成,如顧夐《荷葉杯》「腰如細柳臉如蓮」,柳永《法曲獻仙音》「柳腰花態嬌無力」,歐陽修《少年游》「漢妃束素,小蠻垂柳,都占洛城腰」,南宋?方岳《瑞鷓鴣》「滿斟綠醑歌檀口,慢拍紅牙舞柳腰」,王實甫《西廂記?鬧齋》「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關漢卿《木丫叉》「小蠻腰瘦如楊柳,淺淡櫻桃樊素口」等等。柳永《合歡帶》的「鶯慚巧舌,柳妒纖腰」極為誇張,小腰細軟得連柳絲都妒忌了;類似的說法還有南宋?姜夔《鶯聲繞紅樓》「人妒垂楊綠,春風為、染作仙衣。垂楊卻又妒腰肢」和元代散曲家張可久《折桂令?王一山席間題壁》「鶯怕歌喉,柳妒蠻腰」。《西廂記?驚艷》寫張生眼裡的鶯鶯,其裊娜多姿的嬌柔媚態就是通過細腰來體現的:「似嚦嚦鶯聲花外囀,行一步可人憐。解舞腰枝嬌又軟,千般裊娜,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
古人以腰肢纖細柔軟為美,也與舞蹈有直接的關係。女性若善歌舞,腰身必更婀娜。要想跳出「飄然轉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裾時雲欲生」這樣柔曼的《霓裳羽衣舞》,沒有輕盈的體態、細軟的腰身,是很難想像的。史載,漢高祖劉邦的寵姬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據說趙飛燕因體態輕盈、腰肢纖細能作「掌上舞」,小蠻因其楊柳細腰、舞姿曼妙而受到白居易的喜愛,對此前文已提及。
古人對女性細腰的賞愛,與中國藝術講究曲線美的觀念是一致的。古代詩詞曲賦中,女子的纖腰常被稱為「柳腰」、「蜂腰」,強調的便是細腰使體態呈現出的曲線起伏。富於曲線美的身材具有柔婉溫和的審美效應。而且,中國傳統上特別強調女性的柔順、服從,在腰部的審美上當然就要求能夠像弱柳扶風那樣隨風擺動。女性特有的陰柔之性決定了柔順是女性形體美的一個重要標準。
8、纖纖素手
白嫩細膩、修長靈巧是中國古代美女手指的審美標準。
古代美女,除了面孔之外,人體最頻繁外露的部分要數雙手了。古人在評論美手的時候,矚目最多還是手指的白嫩,常用「柔荑」、「玉」、「蔥」等物作比。如《詩經?衛風?碩人》有「手如柔荑」,寫貴族女子的手,用茅草根來比喻其白嫩。再如和虞《記室騫古意》「清鏡對蛾眉,新花映玉手」;蕭衍《子夜歌》「朱口發艷歌,玉指弄嬌弦」等,用「玉」字形容手指,細膩白嫩俱在其中。唐代詩人趙光遠有首詠手的詩:「妝成皓腕洗凝脂,背接紅巾掬水時。薄霧袖中拈玉斝,斜陽屏上拈青絲。喚人急拍臨前檻,摘杏高揎近曲池。好是琵琶弦畔見,細圓無節玉參差。」其中寫出了美人的種種手姿,末句描寫手指,「細圓無節玉參差」,優美又逼真。韓偓《香奩集》中有一首《詠手》也寫手姿,用「玉筍芽」形容手指,形象獨特:「腕白膚紅玉筍芽,調琴抽線露尖斜。背人細捻垂胭鬢,向鏡輕勻襯臉霞。」玉筍、嫩玉之類的說法後代詩歌中很多,張先《菩薩蠻》有「佳人學得平陽曲,纖纖玉筍橫孤竹」,寫的是美人吹笛;五代毛熙震《河滿子》的「整鬟時見纖瓊」,用的是「纖瓊」,和「玉筍」意思相近;五代孫光憲《菩薩蠻》有「嫩玉抬香臂」,給白嫩的手臂加上了香味;元曲六大家之一的喬吉有散曲《南呂?四塊玉》兩首詠手,其中的「玉掌溫,瓊枝嫩」,給玉掌加上了溫度。
另一個流行的字眼是「蔥」,漢無名氏《孔雀東南飛》有「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似乎是最早用「蔥」來形容美女手指的。後代承襲這個比喻的人很多,如白居易《箏》「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歐陽修《減字木蘭花》「玉指纖纖嫩剝蔥」,吳文英《點絳唇》「一握柔蔥,香染榴巾汗」等。吳文英另有《齊天樂》「素骨凝冰,柔蔥蘸雪」,素、冰、蔥、雪合在一起,白嫩得無以復加。趙鸞鸞的《纖指》云:「纖纖軟玉削春蔥,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掌是「軟玉」,指為「春蔥」,如此美手卻藏在袖中,平日難得一見,偶爾一展示,不免令人驚嘆。染成猩紅色的指甲更是亮點,紅白相映,艷麗非常。
古人對美女修長的手形、包括手指讚美有加,常用「纖纖素手」來形容。如《古詩十九首》之二《青青河畔草》有「纖纖出素手」,東漢末年《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有「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蘇東坡《勸金船(和元素韻自撰腔命名)》有「纖纖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纖纖」,纖細,形容小巧或細長而柔美。「纖纖素手」,形容手既白嫩又纖細,格外美麗動人。
一雙美手展示給人的不僅僅是視覺上的愉悅,而且更重要的是顯示自己靈慧的內心,即我們常說的「心靈手巧」。《詩經?魏風?葛屨》有「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寫會做針線活的手,強調其靈巧,「摻摻」就是纖巧的意思。李漁在《閒情偶寄?聲容部》選姿篇中認為:「兩手十指,為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系」,手嫩者多半相當聰穎,指尖者多半具有智慧。
李漁認為,手以「纖纖玉指」為最美,但具有「纖纖玉指」的女子太少,「十百之中,不能一二靚也」,因而在「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就可以了。
素手之外,手腕也受到關注。如曹植《美女篇》「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晉?傅玄《有女篇?艷歌行》「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南朝梁?丘遲《答徐侍中為人贈婦》「長眉橫玉臉,皓腕卷輕紗」;韋莊《菩薩蠻》「爐邊人似月,皓腕凝雙雪」等。「皓腕」也好,「素腕」也罷,都是強調美人手腕之潔白光彩。
9、三寸金蓮
纖小、弓彎、白淨是中國古代美女雙足的審美標準。
中國古代女性對自己身體最引以為傲的,不是西方美女那樣的肥臀豐乳,而是美麗的小腳,古人稱之為「三寸金蓮」。這不僅令眾多西方人感到困惑,也令對中國傳統美女文化相對陌生的現代人感到不可思議。「三寸金蓮」源於「女子以腳小為美」的審美觀念,女子到了一定年齡,用布帶把雙足緊緊纏裹,最終構成尖彎瘦小、狀如菱角的錐形。雙足纏好後,再穿上綢緞或布面的繡花的尖形小鞋(弓鞋),此即為「三寸金蓮」。
中國人的小腳情結可以遠溯至先秦時代,並以纖巧白淨為美。如《詩經?齊風?猗嗟》中有「美目揚兮,巧趨蹌兮」,把女人的美眸與纖足相提並論。漢《樂府詩集?清商曲辭六?雙行纏曲》有:「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透露了戀足的跡象。漢無名氏《孔雀東南飛》中有「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從步態上可以看出劉蘭芝美足之纖小。魏?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神女似乎有一雙纖足,走起路來搖曳生姿,讓人頓生愛憐之心。晉?陶潛《閒情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用「素」字讚美腳的白淨。東晉?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一個男子看見一個婦人在河水中洗腳而生出追慕之心,詩中的「明月」既可代表該女子,也可象徵其素足,水中的素足就好像雲間的明月,時隱時現,遙不可及,令人心癢難搔。唐?李白《浣紗石上女》「一雙金齒履,兩足白如霜」,用霜形容其白;杜牧《詠襪》詩有「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用「玉筍」用來形容腳之纖嫩;北宋?晏幾道《浣溪沙》「幾折湘裙煙縷細,一鉤羅襪素蟾彎」,也是通過象月牙一樣的襪子折射出美女雙足的纖細。北宋?蘇東坡《菩薩蠻》「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偷立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贊足之纖妙,這也可稱為中國詩詞史上專詠纏足的第一首詞。
女子纏足始於何時,史無明載,眾說紛紜。「金蓮」一說從南朝的潘玉奴開始,到五代李後主時期窅娘是一個質變。據《南史?廢帝東昏厚紀》記載,南朝齊少帝蕭寶卷荒淫無度,「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因而後人稱美人之步為蓮步,又稱女子之纖足為金蓮。明?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引《道山新聞》一文曰:「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為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裹月長新』,因窅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五代李後主李煜令舞娘用帛纏足,使腳纖小彎曲如新月狀及弓形,並在六尺高的金制蓮花台跳舞,飄飄然若仙子凌波,纏足因此而得名為「金蓮」。由此開始,纏足之風逐漸盛行於宮廷。從宋代始纏足之風遍及民間,「三寸金蓮」成了宋元以後對女性美的基本要求。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馬娘娘,就是因為有一雙天然大腳而受盡嘲笑。
在古詩文中,女人雙腳常以纖小、弓彎為美,文人常以「金蓮」、「香鉤」、「鳳鉤」、「新月」等作比。如唐?韓偓《屐子》詩有「六寸膚圓光緻緻」,讚美女足之纖小,唐尺六寸大概只相當於現在四寸多,夠小巧的了。前文所提杜牧《詠襪》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一尺去掉四分,剩下的也是六寸,與韓偓一樣大小。北宋?秦觀《浣溪沙》有「腳上鞋兒四寸羅」,鞋才只有四寸長,腳就更小了。南宋?趙令疇在《浣溪紗》中寫家姬的秀艷「穩小弓鞋三寸羅」,比秦觀更勝一籌。南宋?劉過有一首專詠美人纖足的詞《沁園春》:「洛浦凌波,為誰微步,輕生暗塵。記踏花芳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盈盈一段春。嬉遊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有時自度歌勻,悄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繡茵催袞,舞鳳輕分。懊恨深遮,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碧籠雲。」詞中不僅用「金蓮」、「新月」等比喻纖細的雙足,還用「亂紅不損」、「嫩綠無痕」等形容輕盈的步態。金?党懷英的《鷓鴣天》「雲步凌波小鳳鉤,年年星漢踏清秋」,連天上織女也學人間閨中女子,將腳纏成「小鳳鉤」的模樣。明?王次回的《菩薩蠻》:「多嬌最愛鞋兒淡,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三四分。一鉤渾玉削,紅繡幫兒雀。休去步香堤,遊人量印泥」,借鞋之窄小,形容腳之纖小,末句很有意思:不要去堤上散步,免得無聊的遊人看見鞋印,要量一量看小巧到什麼程度。清?蒲松齡《聊齋?績女》裡有一首《南鄉子》:「隱約畫簾前,三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著重台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為蝴蝶去,裙邊,一嗅余香死亦甜」,描寫了「三寸金蓮」尖、纖、彎、軟等特點,最後一句經典:「一嗅余香死亦甜」,以臭為香,真是痴戀啊。
「三寸金蓮」這種審美心理事實上包含了濃厚的性意識。大概從宋代起,女人的小腳開始被視為她身體最隱秘的一部分,最能代表女性,最有性魅力,對男人最具吸引力。清人方絢,迷戀三寸金蓮,有「香蓮博士」之稱,其《香蓮品藻》系統地論述女子小腳之美及賞玩之法,有「五式」、「三貴」、「十友」、「九品」等等說法,比如「香蓮九品」為:神品、妙品、仙品、珍品、清品、艷品、逸品、凡品、厭品。最高為神品:「農纖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顰笑天然、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此類戀腳癖,將對小腳的賞玩當成風雅的藝術,甚至認為一雙纖足集中了女性全身之美:「眉兒之彎秀,玉指之尖,乳峰之圓,口角之小,唇色之紅,私處之秘,兼而有之。清人李漁在《閒情偶寄》中認為小腳「香艷欲絕」,玩弄起來足以使人「魂銷千古」,還把小腳的玩法歸納出了48種之多,如:聞、吸、舔、咬、搔、脫、捏、推等。可以說,在古代小腳是女人除陰部、乳房外的第三「性器官」。
小腳除了可以滿足男子變態的性心理以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使女人無法遠行,被禁錮在家中。《女兒經》云:「為甚事,纏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纏足使無數女性經受了肉體上的殘害和精神上的折磨,「小腳一雙,眼淚一缸」,一語道盡了小腳女人的悲苦。
10、軟玉溫香
嬌柔、白膩、芳香是中國古代美女身體的審美標準。
「軟玉溫香」是對女子身體美的描寫,其中「軟」、「溫」是柔和、溫和的意思,「玉」、「香」兩個字頗有概括性,一個表現視覺和觸覺方面的白膩,另一個表現嗅覺和味覺方面的芳香。「玉」、「香」也常被指代女子,如「憐香惜玉」、「偷香竊玉」、「香消玉殞」等。有些詩歌中香玉連用,如溫庭筠詩《晚歸曲》「雀扇團圓掩香玉」、後蜀閻選《虞美人》「楚腰蠐領團香玉」、南宋?劉克莊《清平樂》「一團香玉溫柔,笑顰俱有風流」等。這裡「軟玉溫香」一詞就概括了古代美女身體的幾個特徵:柔軟、白膩、芳香。
古代美女以身體嬌柔為美。詩歌中描寫美女常用的字眼,體格是纖、小、細、弱,體膚是白、嫩、香、軟,體態是嬌、媚、輕、柔,五代張泌《滿宮花》的一句「嬌艷輕盈香雪膩」,基本上總結了女性美的所有主要特徵。東漢班昭在《女誡》中也提出:「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就是一位「聞靜以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的柔弱女子。從白居易《長恨歌》裡的楊貴妃:「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到清?洪昇《長生殿》裡的楊貴妃:「看你似柳含風,花怯露。軟難支,嬌無力」,都是一副嬌弱無力的美人形象。還有元稹的《會真詩》「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秦觀的《滿江紅》「翠綰垂螺雙髻小,柳柔花媚嬌無力」,劉過的《滿庭芳》「每為花嬌玉軟,慵對客、斜倚銀床」,楊無咎的《瑞鶴仙》「漸嬌慵不語,迷奚帶笑,柳柔花弱」等,都是以嬌弱女子為審美對象。
古代美女以肌膚白膩為美,在第一條標準里已詳細討論過,這裡不再贅述。下面重點探討美女之體香。
唐以前的詩歌表現女子體香比較朦朧,偏重美女的氣質和氣息,如宋玉《神女賦》「陳嘉辭而雲對兮,吐芬芳其若蘭」、晉?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阮籍《清思賦》「窈窕而淑清」和「清言竊其如蘭」、南朝梁?沈約《麗人賦》「芳逾散麝,色茂開蓮」、李白《清平調》「一枝穠艷露凝香」等,分別用「蘭」、「麝」、「蓮」、「露」、「芳」等表示美女身上或濃或淡的馨香。
唐以後的詩歌,描寫女性體香比較具體,且常常情色味很重。五代魏承班《漁歌子》有句「蛟綃霧縠籠香雪」,「蛟綃」即鮫綃,相傳為鮫人所織的綃,極薄,「霧縠」指薄霧般的輕紗,雪白馨香的肌膚從薄紗中透出來,令人心動;晏殊《浣溪沙》的「粉融香雪透輕紗」,意思也差不多;大晏(晏殊)的句子又被小晏(晏幾道)借用過來:「小瓊閒抱琵琶,雪香微透輕紗」;小晏還有《更漏子》「雪香濃,檀暈少,枕上臥枝花好」,「檀暈」指淺紅色,臥在枕上的如花美人猶紅似白,香氣濃郁,充滿誘惑。
體香有各種類型,曹植《洛神賦》「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是吐氣如蘭的溫香;《漢雜事秘辛》「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是撲鼻而來的芳香;五代?和凝《麥秀兩岐》「異香芬馥」,是馥郁芬芳的異香;劉過《浣溪沙》「誰把幽香透骨薰」,是慢慢滲透出的幽香;周邦彥《玉團兒?雙調》「睡半醒、生香透肉」,是透肌而出的生香;辛棄疾《虞美人》「露華微滲肌香,恰似楊妃初試、出蘭湯」,是美人出浴後散發的清香;《敦煌曲子詞?竹枝子》「百步惟聞蘭麝香」,是芳氣四溢的蘭麝混合之香。
吳文英善寫體香,有一首憶姬詞《風入松》很有想像力:「黃蜂頻撲鞦韆索,有當時、縴手香凝」,美人縴手在鞦韆索上留下的香氣日久不散,竟然引來「黃蜂頻撲」,可算是最為濃郁悠長的女人香。唐圭璋評論說:「因園中鞦韆,而思縴手;因黃蜂頻撲,而思香凝,情深語痴。」李清照有一首《醜奴兒》的艷詞寫的是她婚後的性福生活:「理罷笙簧,卻對菱花淡淡妝。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在涼爽的夏夜,女主人精心妝扮,身著性感內衣,雪肌體香一起透露出來,似乎在有意招蜂引蝶。寫女子體香的艷詞,莫過於蕭觀音的《十香詞》。《十香詞》是十首組詩,分別描寫女人身上十個部位,均以「香」字結尾:
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發)
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乳)
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頰)
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頸)
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暖甘香。(舌)
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口)
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手)
鳳靴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足)
解帶色已顫,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陰)
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肌)
女人的體香可以分為天然的和後天的兩種,前者是女性自身所生發的天然體味,稱為「天香」。李漁在《閒情偶寄?聲容部》上說:「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自薰染。佳人身上實實在在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嬌艷,而能偶擅其奇者。」歷史上最早以香氣著稱的女子,最出名的莫過於春秋時代的絕色美女西施。據說,西施身上便會散發出一種迷人的香氣,她沐浴過的洗澡水,被稱為「香水泉」,宮女們都爭先恐後地希望得到這種「香水泉」。如果把這種水灑在屋裡,整間屋子都會瀰漫著迷人的芳香。此外,還有漢武帝所寵幸的宮人麗娟,她玉膚柔肌,吹氣勝蘭,但是否是天香不得而知。趙飛燕的妹妹趙合德體自生香,則是有史以來最早記載有天香的美女。至於趙飛燕同樣吹氣如蘭,則是後天的薰陶。據說在乾隆皇帝的40個后妃中,有一個來自維吾爾族的美女,「生而體有異香,不假薰沐,國人號之曰香妃」。
一般的女性想要擁有誘人的體香,就需要用薰染的方法來增添身體的香氣,以彌補先天不足。李漁承認了「國色天香」的可遇而不可求,認為薰染是正當的。「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除薰染外,唐代元載小妾薛瑤英,則是幼時長期食用其母所做的「香丸」(用花粉發酵處理後做成內服美容丸),長大以後,肌膚柔潤、玉體生香而青史留名(明?張潮《幽夢影》)。
上述所列「十大標準」,主要是從外貌、形體的角度來說的。「婦人嫵媚多端,畢竟以色為主」(李漁《閒情偶寄?聲容部》)。美女的外在的容顏體貌當然是第一位的,但其次,美女的內在的氣質神韻也非常重要。這種內在美正是李漁所謂的「媚態」,「態之為物,不特使美者愈美,艷者愈艷,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無情之事變為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他認為,「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即便那些「狀貌姿容一無可取」的女子,卻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捨命相從」。不過,這種媚態是自然流露的,千萬不可矯揉造作,「態自天生,非可強造。強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陋。」美女的媚態或者說內在氣質是一種難以用語言表達的「韻味」,大概衛泳所說的美女的態(喜之態、怒之態、泣之態、睡之態、懶之態、病之態)、情(芳情、閒情、幽情、柔情、痴情)、趣(空趣、逸趣、別趣、奇趣)、神(神麗、神爽、神情、神困頓、神飄蕩輕揚)、心等,就是這種內在氣質的具體表現吧。
再次,美女還要有端雅得體的服飾妝扮。女子的衣著穿戴,提倡潔和雅。「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李漁《閒情偶寄?聲容部》)。衣服的色調要與人的臉色相協調,「面顏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李漁《閒情偶寄?聲容部》)。「三分人才,七分妝飾。」女性人人都需要妝飾,修飾打扮最主要的是要得體,「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妝與濃抹,惟取相宜耳」(衛泳《悅容編?緣飾》)。
最後,美女還要兼有德行與才藝,做到德、色、才、藝的完美統一。葉小鸞的父親葉紹袁認為「德才色為婦人三不朽」;清人吳震生提出「色期艷、才期慧、情期幽、德期貞」的標準;李漁認為,女子除了學會過硬的女工外,最好能讀書識字,又能懂得琴棋書畫,兼通歌舞,才藝雙全。這才是理想中的完美女人。
責任編輯: 宋雲 來源:360do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4/0412/387704.html
相關新聞
 中國在沒有引入阿拉伯數字前,古人怎麼書寫算式解答數學問題?(組圖)
中國在沒有引入阿拉伯數字前,古人怎麼書寫算式解答數學問題?(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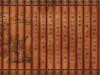






 美媒:中國到底如何援助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
美媒:中國到底如何援助了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

 何清漣:「大眾人」受困於「信息繭房」的實例
何清漣:「大眾人」受困於「信息繭房」的實例 黃世澤:產能過剩誰之過
黃世澤:產能過剩誰之過 梁京:美中對抗與AI競爭(上)
梁京:美中對抗與AI競爭(上)


 魏京生:什麼樣的民主更適合中國(五)
魏京生:什麼樣的民主更適合中國(五) 朱學勤:這一千年的革命
朱學勤:這一千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