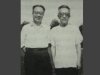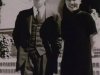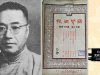;本跡"的涵義則胡亂說。"本跡"兩字是有淵源的,能用這兩字,這表示馬先生的多聞博識,但我想他並不一定得其實。"本跡"兩字來源於魏晉時代,當時講會通孔老有所謂的"跡本論","跡本"觀念貫穿魏晉南北朝兩百多年,最後有阮孝緒出來又總結了這個觀念,佛家天台宗也借用此辭來判教,可謂源遠流長,義涵深厚。但馬先生用之於評論新唯識論,卻顯得突兀,新誰識論之主題用此辭去贊是不大對題的,只是做文章罷了。其序言另一段又說:"擬諸往哲,其猶輔嗣之幽贊易道,龍樹之弘闡中觀",這兩句話,第一句將熊先生之作新唯識論比為王弼之注易經,王弼之注易不但注了經文,最後還作了《周易略例》,極有創見,但是要知道王弼注易經是根本不相應的,您怎麼可以拿王弼之注易來比新唯識論?如果真如所比,則新唯識論豈不是沒有價值了?王弼是用道家的玄理來注易經,而易經是孔門義理,熊先生的立場是純粹的儒家的大易創生的精神,其立場與王弼正好相反,這是極為明顯的,而馬先生竟看不出來。這表示馬一浮先生所用心的是如何把文章做好,而並不注重客觀上正確的了解。至於"龍樹之弘闡中觀"一句,更與新唯識論之主旨不相干。龍樹是所謂的"空宗",中觀論頭一個偈就贊緣起云:"不生亦不減,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所謂八不緣起,這是佛家講"性空"的基本立場,講的是實相般若下所觀照的緣起法的性相,其性是"空",其相是"幻"。這立場與熊先生寫新唯識論大相逕庭,態先生新唯識論不但批評無著世親的老唯識論,也不贊同龍樹的中觀,在此用"亦猶龍樹之弘闡中觀"來恭惟,非但其義不實,而且走了板眼。
馬一浮先生只能作文章,作高人雅士,不能講學問,他文化意識並不如熊先生強,他自己也承認悲願不夠。文化意識不足不能講學,悲願不夠也不能講學。所以他的架子擺得很大,他說現在一般人都不足以教,若要教,也"只聞來學,未聞往教",要人去他那裡請教才行,他決不接大學的聘書。他從年青時起便隱居西湖,二十七歲就不見外人,也不出來。到熊先生寫出新唯識論時,那時他和熊先生都已四十多歲了。熊先生聽說西湖有此一高人,想往見之,或告之曰:他不見人,熊先生想找人介紹,介紹亦不行。熊先生不得已,就自己將稿子附一封信寄去,結果好久都沒下文,正待要發脾氣,馬一浮親自來了,真是"惠然肯顧,何姍姍其來遲"。一見面,熊先生責問他為何久無回音,他回答說:"你若只寫信,我早就回了,你又寄了著作,我要詳細看,看看你的分量,如果分量夠,我才來相訪,現在我不是來了嗎?"兩人於是結為好友。由此可以想見馬先生的為人,這個人的名士氣太重,從學識方面說,他比梁先生、熊先生博學,但客觀的了解則沒有,譬如他好用新詞,但往往不通。我曾看他有一次寫信給賀昌群,賀昌群是念歷史的,常到馬先生門下走動,也認識熊先生。他向馬先生請教南北朝隋唐這一段思想史的問題,也就是中國佛學發展的問題,馬一浮並不稱佛教為佛教,他造了一個新詞曰:"義學"。我起初看不懂,我知道古人有所謂"義理之學",宋明有"理學",而馬先生要用"義學"來稱佛教,不知其所據為何?佛教中所說的理是"空理",義則是"法義",即是現在所謂"概念"。如說諸法苦、空、無我、無常等,"苦"、"空"、"無我"、"無常"便是此"諸法"之法義,它們是一些謂述性的概念,所有這些概念拿"般若實相"來貫通。所以佛教說菩薩之"四無礙智"—辭無礙、義無礙、辯無礙、理無礙—其中即有所謂"義無礙"一項。儒家講"性理",道家講"玄理","義"則是大家都有,儒家有儒家的義,道家有道家的義,怎麼可以用"義學"專稱佛教呢?
5.熊十力
即如我老師熊先生念茲在茲想接著現有的新唯識論寫出"量論"部分,也寫不出來。本來依熊先生的計劃,新唯識論應有兩部,上部"境論",講形上學,下部"量論",講知識論。但"量論"一直寫不出來,其實就是因為學力不夠。因為熊先生的所得就只有一點,只那一點,一兩句話也就夠了。一提到儒家大易干元性海、體用不二,熊先生就有無窮的讚嘆,好像天下學問一切都在這裡。當然這裡有美者存焉,有無盡藏,但無盡藏要十字展開,才能造系統,所以後來寫好多書,大體是同語重複。我奉勸諸位如果要讀熊先生的書,最好讀其書札,其文化意識之真誠自肺腑中流出,實有足以感人動人而覺醒人者,至於《新唯識論》不看也可,因其系統並沒造好。不過雖說熊先生所得只有一點,但那一點就了不起,不可及。當年馬援見漢光武,嘆曰:"乃知帝王自有真者",此語可移於贊熊先生,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學,這點抓住了,就可以立於斯世而無愧,俯視群倫而開學風,這一點是儒家之所以為儒家之關鍵,我們就從這點尊重我們的老師。但他的缺陷我們也應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則可以定我們這一代學問奮鬥的方向,此之謂自覺。
以上都講老先生的毛病,大家不要誤會我對前輩不客氣,其實我還是很尊重這些人,在這個時代,出這種人物,有真性情、真智慧、真志氣,已經是很難得了。我只是要強調"學"的重要,無"學"以實之,終究是浪費了生命,辜負了時代,這大體也是整個時代的毛病。
自覺就是從"客觀的了解"中覺醒過來,有正見,心有定向。所謂"客觀的了解",細言之,比如說讀先秦儒家,就好好正視它如何形成,裡面基本義理是什麼?這種屬於哲學義理的了解是很難的,了解要"相應","相應"不單單靠熟讀文句,也不光靠"理解力"就行。文句通,能解釋,不一定叫做了解。此中必須要有相應的生命性情,若不相應,最好去講文學、歷史、科學等。學問之路很多,各盡其長,各各在本科中不亂講即可,不一定每人要來講義理,講儒家。能相應者才來講,豈不更好?如周濂溪為宋明理學開基之祖,其觀念其實很簡單,只有幾句話就可以把中庸易傳講得很清楚,而且不失儒家之矩,這完全是靠相應的了解,不在博學泛覽。所以黃黎洲《宋元學案》引吳草廬對周濂溪的贊語是:"默契道妙","默契道妙"就是所謂的"相應",對中庸易傳之形上學了解很透闢。不但對先秦各家要有相應的了解,研究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都要有相應的了解。你有沒有那種了解,適合不適合講那種學問,這要自知。"自知"也是一種"客觀的了解",不能講就不要硬講,亂講。譬如講中國佛學,更是困難,中國吸收佛教以至消化佛教,前後四百餘年,消化到天台宗、華嚴宗、禪宗出現,真是人類智慧發展之高峰。近代日本人看不起中國人,說什麼有印度佛教,有中國佛教,中國佛教是假佛教。這都是胡說,中國佛教當然和印度佛教有所不同,但那不同不是並列的兩相對立的不同,而是同一個佛教的前後發展的不同,在印度只有空、有兩宗,並沒有天台、華嚴的判教。禪宗尤高致,只有靠中國人的智慧才能開發出來。但是禪宗雖聲稱為"教外別傳",究其實,也是"教內的教外別傳",其基本理路,仍緊守佛之教理而無失。中國佛教中之高僧大德,如智者大師、賢首等,都是大哲學家,像這樣高級的大哲學家,放眼西方哲學史,都找不出幾個可以相提並論,中國人實在不必妄自菲薄。當時人稱智者大師是"東土小釋迦",是當時人對智者大師有相應的了解,而民國初年,內學院歐陽大師還瞧不起智者大師,說他沒登菩薩位。其實智者大師自己說自己是"五品弟子位",此位在六即判位中屬"相似即佛位","相似位"即是"六根清淨位"。在西方哲學史中,我看只有康德近乎六根清淨,其它人大抵六根未淨。一個人能修到六根清淨,談何容易?大家都稱世親、無著、龍樹等印度和尚為菩薩,這是後人對他們客氣的稱呼,至於他們是否超過六根清淨而達到菩薩地位,則很難說。若因智者大師誠\實的自判為"相似位",就認為智者大師的話不可信,說什麼"台賢宗興,而佛教之光晦",而必以無著世新為可靠,這種評判標準是沒道理的。在修行上,達到六根清淨,固不容易,在學理上,能"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何嘗不是一大智慧?佛教是大教,義理涵蘊無窮,又發展那麼久,內部的各種系統當然精微繁複,要一一抉發其原委品論其高下,當然須要有很強的理解力與很高的慧見,智者大師之判教是有法度有所本的,這才是真正高度的"客觀的了解"下的工作,輕易視之,無乃太不客觀太不自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