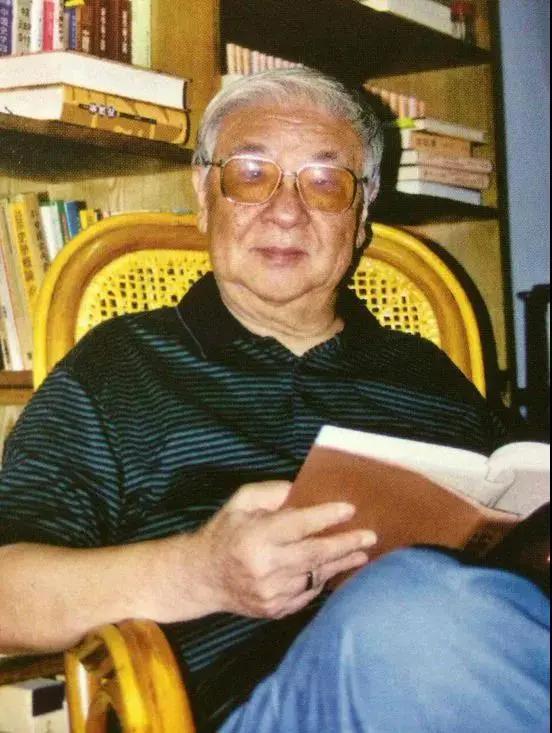蘇州人早晨出外吃麵的習慣,由來已久。
蘇州博物館有一塊光緒三十年《蘇州麵館業各店捐輸碑》,記載了當年蘇州生意最好的幾十家麵館:
觀正興、松鶴樓、正元館、義昌福、陳恆錩、南義興、北上元萬和館、長春館、添興館、瑞必館、陸興館、勝興館、鴻元館、陸同興、萬與館、劉興館、泳和館、上淋館、增興館,風林館、興興館、錦源館、新德館、洪源館、正源館、德興館、元興館、老錦興、長興館、陸正興、張錦記、新南義興,瑞安樓……
可見當時蘇州麵館的興盛,街巷都有麵館了。

朱鴻興雙澆:蝦仁、燜肉。
這些麵館業者最初可能是肩挑駱駝擔子,風裡雨里敲著篤篤梆子穿街過巷賣面人,積下來的辛苦錢開間門面,由此白手興家,皮市街的張錦記就是這樣發家的。蓮影《蘇州小食志》云:
皮市街獅橋旁張錦記麵館,亦有百餘年歷史者,初,店主人挑一餛飩擔,以調和五味鹹淡得宣,馳名遐邇,營業日形發達,遂舍挑擔生涯,而開麵館焉。
麵館既開之後,燜肉大麵湯味清雋,深得新舊顧客喜愛,相傳三四代不衰。張錦記亦名列光緒年間的《蘇州麵館業捐輸碑》中,是蘇州麵館的老字號。

老張錦記這樣的面擔子,如今間或還能覓得。
張錦記店主最初挑的餛飩擔子,蘇州俗稱駱駝擔子,一頭是鍋灶,後頭上擱置各種調味料與碗匙筷子,其下有抽屜數層,分置餛飩與麵條,最下格放置湯罐,內有原湯與燜肉,洗碗的水盒與用水則懸於擔外,叫賣敲的梆子則綁在前頭灶腳下,兩頭以扁擔相連,其上有薄木板凸起似駝峰,故名。或因擔子過沉重,挑擔者負荷似駱駝而名之。
蘇州的面以澆頭而論,種類繁多。所謂澆頭,是面上加添的佐食之物。所有的面基本上都是陽春麵,也就是光面。所謂陽春,取陽春白雪之意,非常雅致。陽春麵加添不同的澆頭而有燜肉、爆魚、炒肉、塊魚、爆鱔、鱗絲、鱔糊、蝦仁、滷鴨、三鮮、十景、香菇麵筋等。所有澆頭事先烹妥置於大盆中,出面時加添即可。另有過橋,材料現炒現爆,盛於一小碗中與面同上,有蟹粉、蝦蟹、蝦腰、三蝦、爆肚等等,不下數十種。

蘇州面的澆頭,不下數十種。
由於食客習慣喜好不同,同一種澆頭又分成不同的類別。朱楓隱《蘇州麵館花色》云:
蘇州麵館中多專賣面,然即一面,花色繁多,如肉麵曰帶面,魚面曰本色。肉麵之中,又分肥瘦者曰五花,曰硬膘,亦曰大精頭,純瘦者曰去皮、曰瓜尖,又有曰小肉者,惟夏天賣之。魚面中分曰肚當,曰頭尾,曰惚水,曰卷菜,雙澆者曰二鮮,三澆者曰三鮮,魚肉雙澆者曰紅二鮮,雞肉雙澆者曰白二鮮,鱔絲面又名鱔背者。
面之總名曰大面,大面之中又分硬面爛面,其無澆頭者,曰光面,曰免澆。如冬月恐其澆頭不熱,可令其置於碗底,名日底澆,暑月中嫌湯過燙,可吃拌麵,拌麵又分冷拌熱拌,熱拌曰鱔鹵、肉鹵拌,又有名素拌者,則鎮以醬麻糟三油拌之,更覺清香可口。其素麵暑月中有之。滷鴨面亦暑月有之。面亦有喜蔥者曰重青,不喜蔥者則曰免青,二鮮面又曰鴛鴦,大面曰大鴛鴦。凡此種種面色,耳聽跑堂口中所喚,其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也。
由此可見蘇州人吃麵的講究了。蘇州面的澆頭種類雖多,普遍的則是爆魚和燜肉兩種,爆魚以陽澄湖的青魚炸氽而成,至於燜肉麵的澆頭,選用豬肋肉加鹽、醬油、綿糖與蔥姜斟酒,以文火久燜而成。

同得興白湯楓鎮大面。
蘇州面用的生面,最初是各麵館自製銀絲細面。銀絲細面細而長,韌而爽,久煮不糊不坨,條條可數。煮麵用直徑三尺的大鑊,黎明時分鑊中水初滾,面投水中,若江中放排,浮於波上,整齊有序。再沸之後,即撩於觀音鬥中,觀音鬥上圓下尖,最初為觀振興所刨,面入鬥中,麵湯即瀝盡,傾入鹵湯碗中,盛若鯽魚背,然後撒蔥花數點,最後添上澆頭即成。最早入鍋的麵湯淨面爽,所以蘇州人有黎明即起,摸黑趕往麵店,為的是吃碗頭湯麵。

銀絲細面細而長,韌而爽,久煮不糊不坨,條條可數。
銀絲細面民國以後改用機制,各麵館應用起來格外方便。不過,1949年後,新樂麵館異軍突起,改用小寬面,各麵館爭相效尤,連老字號的觀振興、朱鴻興也用小寬面,小寬面入碗成坨,口感不爽,近十餘年又恢復銀絲細面。一種飲食傳統經年累積,眾口嘗試已成習慣,不是輕易可以變更的。不過,小寬面並未廢置,仍用於夏季的風扇涼麵,過去涼麵以電扇吹涼,故名。蘇州的涼麵皆用小寬面製成,也是一種飲食的傳統。

蘇州的風扇涼麵皆用小寬面製成,也是一種飲食的傳統。
蘇州的面基本都是陽春麵加澆頭,面的高下,在於湯底,麵湯分紅白兩種,紅湯以不同的澆頭滷汁,摻高湯與不同作料,和料酒、綿糖調製而成,湯成褐紅色,紅湯的高下則在於澆頭的烹調工夫。白湯出于楓橋大面,楓橋大面即楓橋的燜肉麵,其湯底以鱗魚與鱔魚骨再以酒釀提味熬成,江南初夏是鱔魚盛產期,端午前後,各麵館就掛起楓橋大面的幌子。

蘇州的面,湯分紅白兩種,紅湯以不同的澆頭滷汁,摻高湯與不同作料和料酒綿糖調製而成;白湯出于楓橋大面,湯底以鱗魚與鱔魚骨再以酒釀提味熬成。
紅湯色重香醇,白湯則湯清味鮮,除紅白兩種湯外,還有昆出奧灶面的湯,奧灶館創始於咸豐年間,在崑山玉山鎮半山橋,初名天番館,後更名為復興館。光緒年間,由富戶女傭顏陳氏捕手經營,以爆魚面馳名。其制爆魚將活鮮的青魚均勻切塊,以當地的菜子油煉成紅油。炸爆魚剩餘物的魚鱗、魚鰓、魚血以至青魚的黏液加作料秘制而成湯,甚得遠近食客的喜愛,生意興隆,因而引起附近麵館的妒忌,稱其面「奧糟」,「奧糟」為吳語「齷齪」之意,其後顏陳氏竟將麵館更名奧灶館,面為奧灶面。

今日崑山奧灶館。
雖然湯分紅、白,面用銀絲,然而各麵館仍有其招牌面,如觀正興的蹄膀面著名於時,其蹄膀澆頭燜得肉酥味香,入口即化,且以燜肉的湯作湯底,湯醇香滑,傍晚時分的燜蹄面最佳,金孟遠《吳門新竹枝詞》云:
時興細點夠肥腸,本色陽春煮白湯。
今日屠門得大嚼,銀絲細面拌蹄膀。
詠的就是觀正興的燜蹄面。炒肉麵出於黃天源。黃天源是著名的老糕團店,專賣糕團,兼營面點,或謂當年有一熟客每日來店吃麵,照例一碗陽春麵,一粒炒肉糰子,炒肉糰子蘇州夏令名點,以熟的白米粉裹炒肉餡,炒肉餡以鮮肉為主,輔以蝦仁、扁尖、木耳、黃花剁碎炒成,中加滷汁,現制現售。客人以炒肉團餡作澆頭,其後黃天源以炒肉為澆頭的炒肉麵流傳至今。

黃天源炒肉麵,以熟的白米粉裹炒肉餡,炒肉餡以鮮肉為主,輔以蝦仁、扁尖、術耳、黃花剁碎炒成,中加滷汁,現制現售。
至於鹹菜肉絲麵,則出於漁郎橋的萬泰飯店。萬泰飯店創於光緒初年,善調治家常菜飯,其面點著名,尤其開陽鹹菜肉絲麵為其所創。金孟遠《吳門新竹棱詞》云:
時興菜館銣家常,六十年來齒芳芬。
一盞開陽鹹菜西,特殊風殊說漁郎。
老丹楓是家徽州麵館,以售徽式面點著稱。《吳中食譜》云:
面之有貴族色彩者,為老丹楓之徽州面,魚、蝦、雞、鱔無一不有,其價數倍尋常之面,而面更細膩,湯更鮮潔,求之他處不得也。
老丹楓更有小羊面與風爪面,他處所無,老丹楓早已歇業,中西市皋橋旁的六宜館仍在,也有百餘年的歷史了,以爆青魚尾為澆頭,稱甩水面。
松鶴樓是蘇州飯店的老字號,創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御筆親題的金字招牌仍在,過去亦以面點著名,在光緒《蘇州麵館業捐輸碑》名列第二,僅次於觀正興,其滷鴨面最有特色。《吳中食譜》云:
每至夏令,松鶴樓有滷鴨面,其時江村乳鴨未豐,而鵝正到好處,尋常菜館多以鵝代鴨,松鶴樓曾宣言,苟若證其一腿之肉為鵝非鴨者,客責如何?應之所以如何。然其面不如觀正興、老丹楓,故善食者往市其滷鴨,加他家之面也。
所以至今松鶴樓的滷鴨面仍是過橋,舊時蘇州人行雷齋素,吃齋人逢戒齋或開葷,則往松鶴樓吃碗滷鴨面。

舊時蘇州人行雷齋素,吃齋人逢戒齋或開葷,則往松鶴樓吃碗滷鴨面。
雖然各麵館以不同的澆頭著名,仍以燜肉麵最普遍。燜肉麵是大眾食品,是蘇州麵館的基礎,但仍有高下之別。創於光緒十年(1884),位於閶門外帖墩橋旁的近水台以燜肉麵著名,蘇州人常言近水台的燜肉麵「上風吃,下風香」。
不過,朱鴻興的燜肉麵卻後來居上。朱鴻興創於民國十七年,原在護龍街(現人民路)魚行橋旁與怡園相對。其燜肉麵最初由店主朱春鶴親自至菜市選購材料,特選三精三肥的肋條肉製成燜肉澆頭,烹調細緻,將肉燜至酥軟脫骨,焐入面中即化,但化而不失其形。最後澆頭與麵湯和面融為一體,成中帶甜,甜中蘊鮮具體表現蘇州面特色,也是姑蘇菜餚的特質所在。

燜肉澆頭,烹調細緻,將肉燜至酥軟脫骨,焐入面中即化,但化而不失其形。
對於燜肉麵,我情有獨鍾。
當年家住倉米巷。倉米巷到現在還是條不起眼的小巷子,但卻是沈三白和芸娘的「閒情記趣」所在,芸娘這裡表現了不少出色的灶上工夫。出得巷來,就是鵝卵石鋪地的護龍街,過魚行橋不幾步,就是朱鴻興了。
每天早晨上學過此,必吃碗燜肉麵,朱鴻興面的澆頭眾多,尤其初夏子蝦上市之時,以蝦仁、蝦子、蝦腦烹爆的三蝦麵,蝦子與蝦腦紅艷,蝦仁白裡透紅似脂肪球,面用白湯,現爆的三蝦澆頭覆於銀絲細面之上,別說吃了,看起來就令人垂涎欲滴。
不過三蝦麵價昂非我所能問津,當時我雖是蘇州縣太爺的二少爺,娘管束甚嚴,說小孩不能慣壞,給的零用錢只夠吃燜肉麵的,蹲在街旁廊下與拉車賣菜的共吃,比堂吃便宜。所以對燜肉麵記憶頗深,離開蘇州,一路南來,那滋味常在舌尖打轉,雖然過去台北三六九,日升樓宥燜肉麵售,但肉硬湯寡,面非銀絲而軟扒,總不是那種味道。
後來有朋友游蘇州歸來,告訴我蘇州面恢復用銀絲細面了。聞之心喜,驛馬欲動,四年前的清明前後,少年時在蘇州的玩伴聯絡上了,約在蘇州相聚,當年年少十五六,現在都已鬚髮皓然了,於是欣然前往,餘興未了,中秋過後又去蘇州,兩次前往蘇州,都先托朋友訂樂鄉飯店。
樂鄉飯店地近北局,轉過去就是太監弄,蘇州著名的食店集中在此,朱鴻興也遷來營業。每天早晨奔飯店提供的早餐,穿過北局到朱鴻興樓上,泡一杯碧螺春,大嚼一碗燜肉麵,有時去松鶴樓樓下,吃碗滷鴨面和一客生煎饅頭,雖然是蜻蜓點水的逗留,卻已慰多年的思念了。
這次在蘇州居停三月,蘇州的飲食習慣,因社會的轉變,已有許多改變,喜的是出門過早吃麵的習慣仍在。我來蘇州原本無事,閒著也是閒著,不如對蘇州吃麵的習慣作一次考察,飲食文化工作者的田野工作考察比較簡單,只要兩肩擔一口,帶著舌頭滿街走就行了。
蘇州麵館林立,街巷皆有。我居拙政團後面的北園路,是個僻靜的所在,出門就有三家小麵館,出了北園路就是齊門路。齊門路與臨頓路相銜,也不是繁華的街道,有朱鴻興、近水台、蔡萬興分號,這些都懸蘇州著名的麵館,而且是百年的老字號,吃起面來很方便。

朱鴻興的三澆。
現在蘇州的麵館,不論大小,多是長條的板桌,進門買票,然後送到出面處,等待取面,和以往不同,或是當年糧票制度的遺痕。取面處和煮麵的灶頭,有一塊大玻璃相隔,裡面工作的情形一目了然。
灶上放妥作料的面碗堆砌若金字塔,面自鍋中撩起,麵湯未盡,即傾入碗,加高湯,然後轉至前櫃加澆頭,各種不同的澆頭盛於大號的鋁盆中,澆頭種類,有燜肉、爆魚、爆鱔、大排、炒肉、雪菜肉絲等等,然後取面,端烈長條裹上埋頭扒食起來,吃罷碗一推,起身就走,倒也迅速利落。
不似當年付錢後,堂倌一串吆喝,什麼澆頭的面,面軟或面硬,面澆或底澆,重青或免青,堂內相應,高低有致,而且堂倌報得很快又是蘇白,外人很難聽懂。不過,卻非常熱鬧有趣,不像現在靜靜等待取面似排隊領口糧,默默扒面似幼兒園排排坐吃果果,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甚是沓雜,很難細細品味碗中的面,似牛吃草,了無情趣可言。

多年前朱鴻興的水牌。
我在蘇州適逢盛夏,一領套頭衫,一條短褲,一頂遮陽帽,河人家繫舟的所在,朝陽初起,刷了兩旁的白牆黑瓦,餘下的金屑跌落在河裡,化作金鱗片片,一艘清潔河道的木船駛過,船櫓搖碎滿河的粼粼點點,頃刻又恢復平靜,人坐軒中食麵,然後捧清茶一杯,觀軒外流水逝者如斯,寧靜中頗有雅趣。
我們早晨常來吃麵,我吃的還是燜肉麵,也是偏咸,後來熟了,我要灶上不要太成,但原湯早已燉成,若要不成只有加水,但水添多了湯又寡。於是改吃燜肉爆鱔雙澆面。這時正是鱔魚當令季節,蘇州的爆鱔先將活剖的罐魚醃製下鍋炸酥透,然後回鍋焐透,香酥鮮甜而無腥昧,和杭州奎元樓的蝦爆鱔、無錫聚豐園的脆鱔不同。
我往往是燜肉麵一碗,爆鱔過橋一小碟,另加切的嫩薑絲一盞,吃時將燜肉與爆鱔焐於碗底,然後將薑絲傾於銀絲細面上一拌,此時爆鱔的甜鮮盡出,燜肉的鹹味略減,蘇州咸中帶甜,甜中蘊鮮的風味似可回復幾分。

江南一帶獨有蝦爆鱔面。
一日午睡方醒,想起往來石路,都經過中西市皋橋,石路在閩門外,是觀前街外的另一個鬧區。老陸稿薦就在橋旁,老陸稿薦是二百年的老店,以醬肉醬鴨聞名,既以醬肉聞名,其燜肉麵的湯底一定不錯,於是起身驅車前往,當時正是午後,我獨占板桌慢慢地吃起燜肉麵來,果如我所料,燜肉麵的湯不錯,但還是咸了些。
吃罷面又另帶醬肉和糟鵝各一斤,醬肉已不似當年紅艷艷入口即化,肥而不膩。夏令正是糟鵝上市的時候,但鵝瘦小如雛鴨,咸而無糟香,姑蘇美食竟然至此,可以一嘆!倒是出得門來,發現老陸稿薦隔壁就是六宜館,六宜館是百年徽州老館子。不過,現在已經沒落了,徽州館子向以面點精細著名。
第二天我們就去六宜館晚飯,菜已點妥,我又請老闆娘到樓下端碗燜肉麵上來,六宜館樓下長桌數條是賣面點的。面來一試,果然不差,面和湯與燜肉依稀有舊時風味,喜的更是湯不甚成,真的是破落人家留下一隻好的舊飯碗,以後再去六宜館,不論點多少菜,必來碗燜肉麵。

今日同得興麵館。
吃了這麼多燜肉麵,臨行前不久,突然想到竟遺漏了同德興麵館。同德興館在嘉御坊。於是趕往,老遠就看見黃綠底絲邊的幌子,中間寫了個斗大的面字,隨風招展。當時正是午飯時分,入得店來,人聲吵雜,擠了半天場買了紅湯燜肉麗的面票,然後依紅湯白湯兩行隊伍前去取面,等取了面捧著回來,原先的位子已被人占去,心中甚是不爽,只好在桌角擠了個位子,扒了兩口,也沒吃出什麼味道,就起身出門了。

紅湯燜蹄面。
第二天早晨天下著雨,我又驅車前往,這時早市已過,午飯未至,店裡很冷清,我才看清店裡的陳設,和他處不同,全是黑漆的八仙桌,長條凳,我揀了個向門對街的座位坐定,要了碗楓橋大面。楓橋大面是白湯的燜肉麵,吃了一半,我又要了碗紅湯的燜蹄面,堂內不忙,坐櫃的小姑娘走了出來問我說:「老師傅,吃得落嗎?」
答說:嘗嘗。她說來一兩面吧,我說也好。一兩是面減半,湯照舊,於我面前擺了兩碗面,我吃口紅湯的,叉嘗一口白湯的,慢慢品嘗著,果然名不虛傳,確有些舊時風味。
我抬起頭來,檐下滴著淅瀝的雨,檐外行人撐傘匆匆走過,於是,我低頭暗暗盤計,來此三月,前後竟吃了近四十碗的燜肉麵,真的是飽食終日,慚愧!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