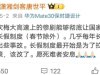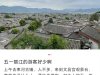但在村醫這裡,他沒有血氧儀,只有聽診器和雙眼。李營判斷重症的唯一標準是,「你看,嘴已經發黑了,嚴重缺氧」。
我們聊起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如何確定是否為細菌感染。
在大醫院裡,司空見慣的輔助手段是,血常規、尿常規、胸片、症狀體徵陽性部位的超聲檢查等。
但對於李營和他的病人來說,這些都夠不上。李營判斷是否存在細菌感染的標準近乎原始:「一些老人發燒好幾天,聽肺部有水泡一樣呼嚕呼嚕的聲音,再問問痰的顏色,是不是黃痰。」
給退燒藥和感冒藥、打點滴,是李營能做的有限的治療。
衛生室里還有什麼?血壓儀、擔架、消毒鍋。他沒有呼吸機,也找不來氧氣。衛生院從前給配了簡易呼吸機,即外界稱呼的「球囊」,需要人工擠壓送氣。但沒人教他怎麼用,「根本也使不得」,閒置很久了。
除了衛生室和村裡的私人診所,D 村老年人能選擇的診療也不多。
一直以來,鄉鎮衛生院被視作農村醫療的中堅力量,根據2021年11月底全國醫療衛生機構數,中國鄉鎮衛生院共有3.5萬個,村衛生室共有60.8萬個。在日前見諸報端的講述中,不難看出,各地鄉鎮衛生院的醫生們正努力應對疫情,他們中的一部分正感受著疫情的衝擊。
但在我拜訪的這一區域,包括村醫在內,人們向上就醫會越過鄉鎮衛生院往縣醫院走。村民談及,過去三年,鄉鎮衛生院更多在搞公衛,「不看病,做了三年核酸」。
我去了三次 D 村上級的鄉衛生院,大樓安靜,兩輛救護車在院裡停著。一樓門診往上,除了工作人員,看不到其他人。二樓住院層,護士站燈火明亮,護士們或坐或站,閒聊著,病房處在暗影里,房門緊閉,異常安靜,通道黑洞洞的。
村醫李營往往建議人們去縣醫院。距離村莊 30多公里的縣城有三家公立醫院,包括一家三甲醫院。在這波疫情中,這是村里老年人能夠得上的最好的診療條件。來這裡住院,報銷比例比鄉衛生院少20%。
我拜訪了縣裡唯一的三甲醫院,這裡的病床從12月27日開始緊張,樓道兩側全是加床。收治病人不分科室,心血管內科的病房裡,除了一位心腦血管疾病的患者,剩下三位都是「跟新冠相關」,平均年齡80歲,家屬說,「醫生講,肺是白的」。

普通病房裡,醫生給的手段大都是:打點滴、服藥、吸氧、做霧化。
一位12月28日入院的病人家屬告訴我,入院沒幾天,醫生說,沒有激素了,家人在外面找到8支,「剛把激素用完,炎症控制住了」,醫生又說,化痰止咳的藥也沒了。
在我的跟訪中,三石的母親是為數不多的,發病第三天就被送去縣醫院救治的老年村民。
他們在縣裡的三甲醫院待了三天,一直打點滴,「越輸感覺越厲害」,醫生加了氧氣,也打了激素。最後一天,醫生下了病危通知,「重症是進不去了,醫院治不了,讓回去。」
三石拿著片子跑去其他醫院,「大夫說,肺已經全白了,拿來也看不了。」
對於「白肺」的治療,過去幾周,北京協和醫院、朝陽醫院、上海同濟醫院的大夫們先後提到,可用的手段是吸氧、糖皮質激素,必要時需聯合托珠單抗或巴瑞替尼等藥物。如果病情危重的患者,需要插管使用呼吸機,甚至接受體外膜肺氧合(ECMO)治療。
但在這個縣城最大醫院的ICU里,一台ECMO都沒有,進價太貴,一台100-300萬,平常用到的機會也並不多。
三石聽兒子說過抗病毒藥物,但縣城的大夫說,自己也沒見過,「去市里打聽也夠嗆,只能去北京問問」。
1月初,李營和王家峰收到鄉里的通知,附了一條連結:「學習小分子抗病毒藥物的使用」。李營打開簽到,沒細看課程,「這個藥長啥樣,我都沒見到過。」
王家峰聽完了課程,他只覺得麻煩,「這個藥聽說不便宜,在農村會有人買嗎?」 最近,村里常用的一種感冒藥漲了 5 塊,他聽了滿耳朵抱怨。我遇到的一位村民正是因此轉向選擇幾塊錢的退燒針。
03 身病與命病
大流行進入第四個年頭,目前流行的奧密克戎毒株變得相對溫和,疫苗以外,人類用高效藥物、重症醫學等多種現代醫學的手段,能將它的危害降至最低。
這場人類和新冠病毒的戰爭,在一些農村老人身上是隱形的,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自然選擇的過程。在鄉村,不只一位老年村民跟我講,「扛得過去就扛,扛不過去是命」。
在許多鄉村老人身上,疾病被分成兩種:身病和命病。
當病毒作用於身上,引起一些輕微的症狀時,比如咳嗽或者流鼻涕,他們吃些藥,甚至不吃。如果身上的疾痛已經嚴重影響生活或勞作了,他們會求助衛生室,打退燒針、靜脈注射。
李秦就是前文中嫌藥價貴的老人,65歲的他和妻子先後生病,妻子沒吃藥,他發燒,身上痛,當天就去衛生室打針,比打點滴還便宜,「輸個液好幾十,打針才幾塊。」
問他打的哪一種針?他不知道,只覺得有用,上午兩點發的燒,打完針沒一會兒就退燒了。
李秦並不能理解肌肉注射的風險和副作用,也無法理解這樣的操作可能讓免疫系統難以發揮作用,只覺得「有用,能治病」,燒退了,他的病「就好了」。

村里,像李秦這樣的老人並不少見,三位80歲以上的老人跟我講述當時的驚險,大都是「一直燒」,「身上沒勁兒,吃不下飯」,「最後還是扛過了。」
當村衛生室的手段無法應對新冠病毒的時候,那就是命。鄉土的就醫邏輯與疾病類型、生計、倫理緊密相關。
三石的母親被送去了縣醫院,但姚重沒有。
結束上門打點滴的工作,村醫李營當天又返回姚重家勸說,「情況很不好,比前一天還不好,如果今天不送醫院的話,熬不過三天。」
「歲數大了麼,有點病扛不住了,」姚重的妻子答。
李營說,「不去醫院就得準備後事了。」
姚重妻子說,後事已經備好了。
奧密克戎襲擊之下,65歲以上的老人被認為是重點高危人群。在距離D村100多公里外的北京,醫生們告訴我,急診和重症里躺的大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在這裡,人們認為,與病毒的抗爭,現代醫學還能最後一搏,我們有抗病毒藥物、呼吸機、ECMO。
哪怕資源緊缺和匱乏,城市裡的人還能喊,搶藥,買呼吸機,找重症床位,渠道五花八門。
但在資源有限的村莊,很多重病的老人無法感受現代醫學奮力一搏的力量。
村民們普遍建構了一種解讀邏輯:「好多人不想給孩子增加負擔,在家養著吃點藥。農村不是城裡,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沒有勞動力,城裡有醫保,有養老金退休金,活一天拿一天錢,所以家裡人更願意救。」
村里人普遍認為,更值得救的是孩子,父母帶著孩子去北京輾轉求醫的故事,帶著辛酸、慶幸、驕傲的口吻被講出,在村莊裡,這樣的經歷我聽過不止一個。
探訪村莊的當天下午,我收到李營的信息:「那個病人(姚重)病危,快要停止呼吸」。
在河北農村,有一個講究,人死後,要在門口放三隻炮。出殯時,白事兒體面的標誌之一是,鞭炮要響。
我走的時候,鞭炮聲停了,村莊恢復了原本的生原生質地。午後,許多人走出家門曬太陽,放寒假的孩子嬉笑做遊戲。整個村莊露在外面,跟疫情有關的,僅有村口三間被廢棄的彩鋼房,封村時,村民住在裡面守著,防止有人偷偷溜出去。
部分受訪對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