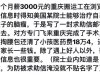《紐約郵報》專欄作家、《被偷走的青春》一書的作者卡羅爾‧馬科維茨談美國文化中出現的「蘇聯模式」,她呼籲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和成長負責,抵制覺醒主義對家庭和價值觀的破壞。(《思想領袖》提供)
英文大紀元資深記者Jan Jekielek採訪報導
卡羅爾‧馬科維茨:這發生在一塊紅色的飛地,一個紅色的小村莊,一座紅色的小鎮,一座紅色的縣城。就像……我需要這些人明白,這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
楊傑凱:《紐約郵報》專欄作家卡羅爾‧馬科維茨(Karol Markowicz)曾自稱是「紐約至上主義者」,她的一生都在紐約市度過,但在新冠疫情之後,她看到了美國文化中的蘇聯模式,於是舉家遷往佛羅里達。
卡羅爾‧馬科維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自由的人也可能像獨裁者一樣行事,在一瞬間就把矛頭對準他們的鄰居。
楊傑凱:她與貝瑟妮‧曼德爾(Bethany Mandel)合寫了《被偷走的青春:激進主義者如何抹殺純真並洗腦一代人》(Stolen Youth: How Radicals Are Erasing Innocence and Indoctrinating a Generation)。
卡羅爾‧馬科維茨:覺醒主義者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們卻能控制那麼多的人,他們通過這種強迫性順從來做到這一點。當我們把孩子們當作小大人時,我們就把自己所有的麻煩和問題都灌輸給他們,這確實會讓他們以後的生活變得一團糟。
楊傑凱: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一場更大的文化革命
楊傑凱:卡羅爾‧馬科維茨,很高興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馬科維茨:非常感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我非常喜歡讀你的書。我做過的很多採訪,主題涉及覺醒意識形態,所謂的性別肯定治療,圍繞新冠肺炎的災難性的疫情政策,類似的話題我自己有過很多的思考。而你把這一切都匯總到一本書里去,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那麼,請跟我講講你一開始看到了什麼,所有這些事情是怎麼聯繫起來的。
馬科維茨:正是新冠肺炎讓我了解了很多事情,我開始在我們的文化中發現一些模式,我認為這是一場更大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這場革命正在美國發生。比如新冠疫情期間,不允許你講出、說出你真實的想法,而你必須隱瞞你真實的意見以免受到所在社區或鄰居的孤立,或者更糟,你可能會被解僱,等等。這讓我想起了從自己家人那裡聽到的故事。我出生在蘇聯,我從我的父母、祖母那裡聽到的故事,好像突然以某種方式引起了我的共鳴,這種體驗以前從未有過。我意識到美國文化中正在發生的、我感受到的事,與那些蘇聯發生過的故事非常相似。雖然我一直都有點不敢去想美國文化中可能有什麼蘇聯的內容,但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非常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自由的人也可能像獨裁者一樣行事,在一瞬間就把矛頭對準他們的鄰居。所以我和我的合著者貝瑟妮‧曼德爾開始講述我們聽到的故事。
當時我們沒有一個總的主題,只是說一些不好的事發生在孩子們身上,對此我們需要說點什麼。我們的書原標題是「讓你的村莊遠離我們的孩子」。這就是我們當時在寫作時的想法。我們看到新冠肺炎暴露出很多不同的方式被用於對孩子們進行灌輸,孩子們在我們的社會中受到了怎樣的虐待,我們覺得必須說道說道。
我在書里也談了很多蘇聯的情況。在蘇聯,孩子們被看作是革命的接班人,他們是前途光明、繼往開來的一代人。對孩子下手並非偶然,讓家庭破裂並非偶然。為了便於灌輸,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與他們的父母分開。即使在像蘇聯這樣的地方,那些人也不得不為自己狡辯。比如他們不能說,「現在這些是我們的孩子了,這些孩子屬於我們所有人。」而喬‧拜登最近就這麼說了,他說,「這些不是你們的孩子,這些是我們的孩子。」
喬‧拜登:「什麼別人家的孩子,沒有這回事。沒有別人家孩子這回事。我們國家的孩子就是我們所有人的孩子。」
馬科維茨:我想即使在像蘇聯那樣的地方,這種思想也會遭到抨擊。所以他們不能那樣做。他們得這麼說:我們在一起,我們會幫助你撫養孩子。這不是要把你們分開,而是要讓你們共同成長。
保護孩子免受覺醒意識病毒的侵害
楊傑凱:沒有什麼一刀切的解決方案。這就是我的感想。比如有些孩子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有難以置信的責任感。與他們建立這種關係幾乎是合理的,當然,要有一些界限。但他們已經在拓展自己的界限。還有一些孩子一點責任感都沒有,像零一樣,是吧?你需要非常……
馬科維茨:是的,你看,我有三個孩子。他們差別太大了。他們看起來簡直就像不同的爹媽生的,個個都不一樣。他們生來就這樣,這是事實。我們幫著他們塑造應對的方式,只要不是個性方面的原因。當然,他們的個性可能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我們的目標是培養有韌性的孩子,讓他們能夠走向世界,而不是讓他們感到某種程度的焦慮,從而使他們變得虛弱,或者讓他們在大學裡對氣候變化感到極度擔憂,使他們無法過上充實的生活。所以當我們把孩子當作小大人對待時,我們就把我們所有的麻煩、問題灌輸給了他們,這確實會把他們今後的生活搞得一團糟。
楊傑凱:我認為認可這種意識形態的人會說,大家都在灌輸。實際上,卡羅爾,你在向孩子們灌輸你的意識形態。我有一個更好的意識形態,我希望把我的意識形態灌輸給他們。這就是一個事實,對吧?那麼,你沒有給你的孩子灌輸思想嗎?
馬科維茨:嗯,我肯定在影響他們。請注意,我很樂意給我的孩子灌輸思想。但是如果孩子什麼都聽家長的,那肯定不合理了。如果社會上每一種力量都把孩子們推向一個方向,那力量是巨大的。但是,你認為你應該能夠向我的孩子灌輸東西,這種想法也是我憎惡的。不,你不可以這樣,你不是他們的指路人。你是他們的老師,你是他們的醫生,你不可以把一下想法灌輸給他們,然後我在家裡卻需要把它們消除掉。
不得不說,我的孩子們確實過著他們自己的生活,不管什麼原因吧,你可以說由於我的灌輸,隨你怎麼叫吧,總之就是因為我的教育。他們確實過著自己的生活,當有人試圖說服他們信什麼的時候,他們頭腦是清醒的。我兩個大一點的孩子放學回家,就會說,今天我在課堂上聽到了這個,我需要考慮或擔心這個問題嗎?我開玩笑地稱他們是「覺醒警察」。因為當一個概念強行推給他們時,或者當他們聽到某人的觀點而不是事實時,他們頭腦是非常清醒的。這很好,我希望他們頭腦清醒。
你知道,我和貝瑟妮,我的合著者,我們走的路大不相同。我有三個孩子,他們都在公立學校上學,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一個現在在私立學校。貝瑟妮有六個孩子,她在家裡教他們。她會預先觀看他們要看的電影,她預先閱讀他們要讀的書。這些我都不做。我給了他們一條長長的繩子。我說,我相信你們。我想聽聽你們在外面學到了什麼。但我也在家裡提供基礎學習內容,我們兩家都這麼做。但貝瑟妮想說的是,無論她如何保護自己的孩子,她都無法從各個方面保護他們免受覺醒意識病毒的侵害。在兒科醫生辦公室里,她說,我在家教育他們,我們什麼都能做,文化之外的事,但我仍然需要帶他們去看醫生。如果你的兒科醫生被意識形態俘虜了,許多兒科醫生已經這樣了,你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在覺醒體制下,每個人的思考方式都必須完全相同
楊傑凱:是的,這很有意思。我喜歡你這麼講,你想給他們接種某種程度的覺醒主義,對嗎?這樣他們就能真正看清楚。你做了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區分。對於你應該相信什麼,有一種整體的看法,對吧?我一直在想,在我們的社會中,這種感知到的共識正在朝著某個方向推進,你被教導說它完全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而不是說,嘿,我要教給你評估那些東西的技能,這聽起來就像你在做的事情,區別很大。
馬科維茨:很難搞,是的。嗯,我可以肯定,這肯定是目標,就是給他們提供工具來評判他們在外面的世界聽到的東西。但我也要說這種新的覺醒主義,與自由主義或老式的左派相反,它走的是一條窄路,你得照他們的話去說,完全照搬,分毫不差。你在描述那些思想時也需要非常地具體,你只能以非常明確的方式來談論它們。比如,你不能說「我不是種族主義者」,你得說「我反對種族主義」。所以我對我的孩子沒那麼死板僵硬。我希望他們探索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觀念。而這曾經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能獲取廣泛的觀點,這樣他們就可以選擇自己的觀點,自我學習。而現在我們還做不到,因為在這種覺醒體制下,每個人的思考方式都必須完全相同。
從紐約搬到佛羅里達州的原因
楊傑凱:請解釋一下,你來自哪裡,也許還有你父母教給你的一些理念,讓你覺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馬科維茨:我出生在蘇聯,很小就來到了美國,當時我還不到兩歲。我在布魯克林長大,我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住在紐約,雖然有時短期離開一下。我原本想一輩子都生活在紐約,我們打算在紐約撫養自己的孩子。一年多一點以前,我們決定搬到佛羅里達,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決定。我們剛剛在布魯克林建造了自己夢想中的家園,我們確實計劃在那裡度過一生。但是後來我們覺得紐約的現狀已經失去了控制,特別是在疫情之下,而且在圍繞疫情的許多問題上也是如此。
不僅僅是因為疫情,但疫情確實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我們覺得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正在做一些真正的、理智的正常決策,我們對此表示讚賞。所以我們就搬家了。事情鬧得還挺大,因為我是《紐約郵報》的一名專欄作家。再說一遍,我是紐約至上主義者。因此,我要離開紐約的想法很轟動,人們都想聽聽這個故事。所以,真是太棒了,真的很自由,我們一家人真的找到了一種自由的方式。
楊傑凱:你的報導,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我從那時開始更多地閱讀你的文章,因為我認為你比很多人都要超前一點,非常有見解。但是,我想知道,你的父母告訴過你什麼,以致你能更清楚地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因為我想一定有那麼一個時刻,你看著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你周圍的人卻說,你在說什麼呢?
馬科維茨:是有過好幾個這樣的時刻,但我想說的是,像在臉書群組裡,我們那個非常開明的社區,對於給最貧窮的成員提供教育突然不再感興趣了。他們根本不關心紐約市各地貧困社區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事實上,不讓貧困社區孩子上學成了他們理念的一部分。同時,他們自己的孩子,他們把他們送到私立學校,當時是放開的。顯然,公立學校非常危險,但私立學校是允許上的。或者他們給孩子找家庭教師,或者他們搬到自己的度假屋,讓孩子上當地的學校。但他們對全城貧困兒童卻隻字未提。我覺得那一個時刻對我來說非常像蘇聯,就好像你說的是一套,但你相信的完全是另一套。還有,告發鄰居,人們會報警說,這家後院人太多了。他們似乎非常喜歡這樣,真的熱情高漲。
另外,當有人說「我認為學校應該開放」時,談話就會中斷。我覺得就像,我不明白為什麼自由的歐洲開放學校,但這種理念在美國只有唐納德‧川普(川普)的支持者們才認可。他們基本上都會說,「哦,你是右翼分子。」搞不好他們會把他們從俱樂部踢出去。這個人會說,「我一輩子都是自由主義者,你信的一切我都信,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開放學校呢。」那些人就會感到受到了嚴重的騷擾。有些人因為這些理念被解僱了。那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期。但隨後犯罪率真的開始飆升。
長期以來,紐約一直做得很好,我們都期望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然後,當它沒有繼續時,就像,他們拒絕接受,他們拒絕承認犯罪率在上升。所以你會看到這樣的帖子,「我就是害怕天黑後自己一個人走路」,或者「我十幾歲孩子的手機在當地地鐵站被偷」,等等。他們會收到這樣的留言,「不,不要相信右翼媒體關於犯罪的言論。」我會說,統計數據就是統計數據。他們會說,但是請注意,在20世紀90年代犯罪率更高。嗯,是的,但你談的是紐約市歷史上極其糟糕的一個時期。那個時候我們有過二十多年的相對無犯罪的時期,不是沒有犯罪,而是紐約市犯罪率較低,你就因為意識形態而忽略這個?你會說這不存在,因為你是站在想假裝這些不存在的一方?我真的看到了我一生中都在聽說的順從,你不得不相信,你必須讓它表現一下,我在書里談到了這一點。
我在《被偷走的青春》裡講了很多,表現一下就是為生存下去。極權主義國家之所以蓬勃發展,這是部分原因。比如,當喬治‧弗洛伊德致死案發生時,引發了騷亂,大家紛紛在櫥窗上打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我心裡就在想,我在書里也這麼說,「黑人的命也是命」真的是一個沒有爭議的理念。當你把這個標誌貼在窗戶上時,在你那個意識形態相同的社區里,你說話的對象是誰呢?比如,你想用你的標語說服誰呢?當然,他們並不是要說服任何人。他們想要表達的是,咱們是一夥的,我是其中的一員,請不要衝著我來。因為,你看,我的窗戶上都貼著這樣的標語了。在我看來這「很蘇聯」。我的曾祖母,抱歉,我祖母的父親,我曾祖父死於史達林的古拉格集中營。然而,當史達林去世時,我祖母和她的妹妹把史達林光輝的一生做成了一本剪貼簿,因為當重要的是要看表現的時候,你就這麼做了。我從很多不同的角度看到了它,想不看都不行。
覺醒主義者是非常小的群體,但通過強迫性的服從控制了很多人
楊傑凱:我們繼續與卡羅爾‧馬科維茨交談,她是《被偷走的青春》一書的作者之一。你之前提到有些人熱衷於對他人進行所謂的告發,或者說告發讓那些仿佛著了魔的人威風起來了,他們通常沒有多大的權力,但突然間他們可以成為管事的人。而且,在每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裡,這些人都是共產黨隊伍中能往上爬的人。每當我看到那些人興高采烈地告密的時候,我就想,為了什麼呢?值得這麼高興嗎?
馬科維茨:是的,感覺他們好像一直在等待這個時刻似的,告發自己的鄰居,並且……
楊傑凱:這不令人不安嗎?
馬科維茨:是的,是的。因為我認為在COVID之前,我不會想到在美國社會中我會遇到這種情況。這令人不安。令人不安是因為那麼多的人那麼快、那麼容易地就陷入其中,告發自己鄰居,讓人們因為意見錯誤就被解僱,叫停人們的工作,等等。是的,難以置信的是,它發生了,而且正在美國發生,而人們就站在那,支持它。感覺覺醒主義者是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但他們卻能控制那麼多人,他們通過強迫性的服從來實現這一點。
楊傑凱:嗯。你知道,有這麼一種觀點,自由永遠只有一代人的距離。
馬科維茨:能來到這裡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幸運,當然了,我現在仍然這麼認為,但我覺得一種非常令人不安的趨勢正在美國社會出現。你是對的。這不是我們可以忽視或不去關心的事情。也許明天我們就完蛋了。這已經是世界歷史上運行時間最長的民主和自由實驗之一,即使它不是最長的。我認為這是最長的,是吧?我認為沒有人打敗我們。也許它明天就結束了。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
楊傑凱:這可能發生在選舉中,而且已經發生了,你知道,就在我們周圍。我只是……你不能……你看看委內瑞拉,這個真正繁榮的自由社會楞是投票把自己投成了一個獨裁政權。
馬科維茨:嗯,有一個笑話,你可以把自己投進去,但是你得開槍殺出一條路來。
《被偷走的青春》一書描繪出了覺醒主義的整個畫面
楊傑凱:你和貝瑟妮描繪出了覺醒主義的整個畫面。這是怎樣的一個畫面?當然,你提到了各種各樣做了出色工作的人。
馬科維茨:覺醒主義是左派意識形態與這種強迫性服從的結合體。因此,過去的左派肯定努力推動著他們的計劃,而且做得很成功。比如在大學這個層面,新覺醒主義不允許在這種對話中有任何空間,這就像左派不能與左派爭論不同的觀點。覺醒主義走的是一條非常狹窄的道路。所以這就像老式的左派,對此我開了個玩笑,你可能會獲得女性研究的學位,但新的覺醒主義是你獲得了女性研究的學位但你定義不了什麼是女性。這很重要。有點像,老式左派們會感到震驚的是,覺醒主義者現在說,他們不能確定到底什麼是女性,他們不確定成為一名女性意味著什麼,他們無法定義。像七十年代的女權主義者、六七十年代的女權主義者會覺得這很讓人震驚。所以對我來說,這就是老式的左派意識形態和新式的覺醒主義之間的區別。
另外,關於平等與公平的討論是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我認為老式左派曾經支持「平等」,而「公平」是覺醒主義的流行語。它不講機會平等,而是講結果平等。任何曾經在共產主義國家生活過的人都可以告訴你平等的結果是不存在的,它不會發生,這是不可能的。某些人的結果會不同於其他人,就是這樣。
楊傑凱:在閱讀過程中,我記下了腦海中出現的一些主題。其中一個主題是關於對兒童的荒謬的醫療處方。
馬科維茨:是的,我們在醫學上對孩子們所做的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特別是對於男孩。我認為我們對他們治療過度了,我們正在剝奪男孩們非常自然的行為方式。再說一次,我有一個女孩和兩個男孩,他們是不同的,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女兒可以坐著看幾個小時的書,而我兩個兒子,如果逼著他們坐下來看幾個小時的書,會毀掉半座房子的。而他們都是同一對父母所生。所以我認為對男孩的過度醫療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在性別意識形態的辯論中,你也可以看到對孩子用藥的情況。比如,對孩子做什麼是可以接受的,阻止他們青春期的到來是否妥當,或者激素治療。這很瘋狂,因為直到最近我們才真正開始說這樣是不行的。我認為對孩子進行激素治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任何表現為性別焦慮的孩子來說都很普遍。現在這種做法終於受到了挑戰,而且挑戰得相當好。讓我吃驚的是,我們居然讓它發展到了這個地步。
歐洲免受了很多覺醒主義的影響
楊傑凱:在歐洲,無論是在性別醫學方面,還是在疫情治療方面,都制定了更多基於科學的政策。但出於某種原因,我們這裡並不了解這些。
馬科維茨:我們聽說了,但我們只是選擇了完全無視。對我來說,如果說歐洲在某些方面幹得漂亮,這很瘋狂,但他們在疫情防治方面的表現比我們好得多。我之前在觀察,驚訝地發現,歐洲那麼多國家從來沒有給孩子戴過口罩。然後當疫苗出現後,他們說,不,孩子們不需要這個。我以前也是這麼說的。有人認為這是一件非常極端的事情。我過去是支持疫苗的,我只是認為孩子們不需要疫苗。如果我不得不再來一次,我不知道我是否還會支持打疫苗,但當時我就是那樣。對我來說很明顯,孩子們,他們新冠肺炎結果不佳的風險已經為零了。再降也沒法降了,這不像到零之後你可以接著降。
然而歐洲非常快地就想明白了,他們也確實讓自己免受了很多覺醒主義的影響。他們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大陸。那裡的大多數國家都相當自由,這就是全部了。他們是自由的,他們沒有覺醒主義運動,他們沒有陷入狂熱之中,而那種意識形態真的很瘋狂。而且他們沒有遇到與我們同樣的問題。他們性別焦慮的人數遠低於我們,這恰恰表明那是一種社會傳染,不是自然發生的事情。例如,大體上歐洲對變性兒童的接受度很高,但他們的孩子中變性的發生率遠遠低於我們。
而且說真的,美國的左翼人士應該想一想,為什麼他們曾經什麼事情都追隨歐洲,而現在卻不追隨了。但沒有人可以提出任何問題。
楊傑凱:而且還出現了一種轉變,現在正在加速擺脫這種性別肯定治療的理念,這種理念就是如果你的想法跳出了常規思維,它就「肯定你,肯定你,肯定你」。
馬科維茨:歐洲正在拋棄這種觀念,英國肯定正在遠離它,因為……
楊傑凱:因為那種做法不起作用,造成了巨大的問題。我的意思是,他們發現了。
馬科維茨:是的。這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問題,我們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共產革命中的讓家庭分離正在美國上演
楊傑凱:我注意到的第三個主題就是這個普遍的想法,同樣,在性別方面,在新冠疫情方面,坦率地說,在其它方面,就是這種認為父母應該被排除在關於孩子的決定之外的想法。實際上這種做法居然是可以的。
馬科維茨:是的,這應該讓父母們感到害怕。我們以前的理解是,如果有人要求孩子保守秘密,別讓他們的父母知道,這個人就是在對孩子們幹壞事。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可以接受的地步了,作父母的不需要知道孩子在學校做什麼。如果孩子決定在學校里成為不同性別的人,使用不同的性別代詞,打扮成異性,這應促使父母們認識到,這裡存在著一個更廣泛的問題。讓家庭分離是這類革命中發生的事情。如果父母看到這種事情發生了,有人要求他們的孩子對他們保守秘密,我認為他們應該自己想像一下,還發生了什麼?如果這種事都發生了,還有別的嗎?
楊傑凱:這是文化革命嗎?讓人不敢相信。我們在蘇聯看到過,我們在共產主義的中國見到過。是的,是年輕人,我不知道我剛才說過沒有,是的,紅衛兵,毛澤東的紅衛兵是青少年,基本上把那些不按規矩來的老一輩人置於死地。
馬科維茨:對,一場文化革命正在我們這裡發生。我認為與那些革命非常相似。而唯一真正的區別是,我們知道它正在這裡發生,我們意識到了這種現象。因此,阻止它應該比其它地方更容易。我們在書中找出了這些歷史的相似之處,因為我認為它們很有啟發性。他們正試圖改變我們的文化,以實現他們的願景。如果我們放任他們,一旦他們成功,我們就無法阻止了。這就是說,現在就必須阻止這種現象。當你看到它在我們社會的不同方面發生的時候,應該儘快制止,而且人們不能掉以輕心。
我在寫這本書之前,我覺得我不會認同一場文化革命正在發生,但現在我看得很清楚了。我看到它已經無所不在了,這不是陰謀論,而是正在發生。
還有一件事,我們談到比如左派利用兒童成為他們的積極分子。我們收到了大量的留言或郵件等等,說這太荒謬了。把正在發生的事情想像成陰謀論,這是很荒謬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出版了一本書說,「是的,我們應該讓孩子們成為積極分子。」千真萬確,這就是他們的目標。這就好比,是一個陰謀論,還是一位左派高層領導剛剛承認了這一點?你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承認,所以你必須得想清楚。你知道,父母們必須自己把這件事想個明明白白,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
楊傑凱:好的,卡羅爾‧馬科維茨,很高興你能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馬科維茨:謝謝,楊,非常感謝。謝謝。
楊傑凱: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對卡羅爾‧馬科維茨的採訪。我是主持人楊傑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