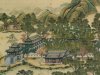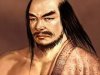漢代的文字,現在看來算不算陳舊的文字?從時間上說,當然是很久以前的文字了。但是,在我看來,任何好的文字,不論其時間多麼久遠,只要是好的,就都不顯得陳舊,都是新的。好的東西,總是能經受得住時間的淘洗和掩埋,總會突兀於歷史煙雲之上,對任何時代的人來說:它們是那麼地新!
我的這些類似感想,是因為常常忘不了曾經讀過的寫於2000多年前的一則短文--《漢書·文帝紀》所載漢文帝《卻千里馬詔》,只有短短的29個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給皇帝行賄,實在是為了討歡心。有人給漢文帝劉恆獻上千里馬,類似現在買一部寶馬奔馳車並辦好一切手續,直接把鑰匙送上一樣。漢文帝是個吃過苦、受過冷落,知道人間冷暖的皇帝,他謹慎地整飭了漢朝建國以來的前期動亂局面,開啟了修養生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時期,這樣的皇帝當然不是一輛奔馳寶馬能搞掂的。漢文帝並不是將行賄的人抓來訓斥一番,而是用了一種溫而厲的方式,抓這個典型,給全國的官員上一課,詔書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至?"譯成白話就是:天子出行,前有儀仗,後有侍從,好天氣一日行五十里,壞天氣一日行三十里。你送給我千里馬,叫我一個人騎上先跑到哪裡去呢?
文字就事說事,不展開,卻自有自覺延伸的意義和功效。詔書的寫作也可以是極其自由的,文無成法,文成法立。此詔極其節省,簡捷到極致,卻生動活潑,無絲毫蕪雜,也無絲毫遺漏。微言大義,輕輕一點,雷霆萬鈞,山崩地裂,翻江倒海。
《卻千里馬詔》,堪稱千古反腐戒貪的不朽雄文。讀之自可以養人浩然正氣。我甚至感到,因為這29個字,那個兩千多年前的皇帝似乎離現在不遠,讓人有類似音容宛在的奢望。所謂文章千古不朽,為文之人亦可謂千古不朽。
《漢書》所載文帝的幾份詔書,其治國的思想和為政的風格氣度貫穿其中。如《恤民詔》,雖短俏,但意味綿長,讀數十字,如行數十里山景,風光無限:"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這是命令,要為老百姓辦事。該詔書和《除肉刑詔》一樣,反映出漢文帝的"仁政"思想。天上發生日食天文現象,文帝趕緊藉機發揮,下《日食引咎詔》,罪己,向人民承認自己的過失並號召全國推舉有用的人才。其圓融通達之至,躍然紙上。他在當皇帝之前,是深受黃老思想浸潤的,當了皇帝,即將黃老與孔孟高度地統一起來,尋找到兩者的最佳結合點,並將其綰接在一起。
我剛買了一本雜誌,封面主打文字赫然標題:誰都拿歷史說事兒。好像在譏諷當今話說歷史的風氣。古人說:人不通今古,即"衿裾牛馬、衣冠狗彘"。歷史就那麼惹人煩嗎?惹你煩也沒辦法,它已經發生了。你不了解,將來更煩。不管以什麼方式,實現當代人對歷史的認知,都是好事情。
當代人讀古書,不論是推義理、求考據還是學辭章,無疑都在自覺不自覺清理自己的文化老底兒。也許是說得偏頗了一點兒,當代許多文化上的胡作非為,都源於長期的對傳統文化的久違和冷落,自覺不自覺地被"文化殖民化"了。這個"殖民化"還不是第一手的"殖民化",而是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手的"多水貨",是偽"殖民"、假"殖民"、莫名其妙的"殖民"。就是說,我們許多當代折騰得很兇、也似乎很風光的文化人和文化活動,其作派和德性都顯得人盡可夫。
文章千古事,讀書可醫愚。當代人面臨的,還不是品味漢文帝詔書的文辭之美,而是要知道歷史上,中國人曾經這樣表達過自己的思想理念。我們能看到的漢代文字,當然是"文",與我們現在使用的"話"有本質和成色上的不同。曾經有近人發出把古書扔進茅坑的激烈言辭,但即使看他的文字,也還是遠比現在我們認真學習古文的人的手筆要古雅得多。他要扔的古書至今發揮出嶄新的光彩,而當代許多新人的手下文字,卻充溢著陳舊的腐朽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