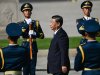從來沒有一種社會運動,像共產主義這樣,向命運索要如此深重的苦難和慘痛的生命損失作為祭品;也沒有哪一次理想主義的崛起,像共產主義這樣,最終竟造成心靈的百年悲愴,並用血海淚濤論證理想主義的殘酷。但是,時至今日共產主義的本質仍然沒有清晰地呈現於人類的智慧之鏡——人們甚至不清楚,共產主義究竟是一次偉大理想主義的失誤,還是魔鬼的罪惡;至於共產主義的文化源流,則更是雲遮霧鎖。
不清楚苦難和罪惡的原因,那麼,苦難和罪惡必定再次主導命運。無論對於個人、族群,或者人類整體,都是如此。更何況共產主義並不是過去時。儘管歐洲中心主義者傲慢而愚蠢地認為,蘇聯和東歐共產帝國的雪融冰消意味著共產主義的最終失敗,但是,中共暴政在東亞大陸的存在,已經開始預言共產極權的再次崛起和全球性擴張。因此,為了阻止罪惡,必須尋找到共產主義的文化原因。
共產主義的文化之源,是流淌在中世紀千年暗夜的極權主義血河;沿那條血河,還可以上溯至古猶太智慧中湧現出的真理絕對主義意識。共產主義的精神風格,同中世紀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相似得就如同兩個骷髏。
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這兩種精神運動都以創建絕對的真理,作為思想的終點,並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要求對人類心靈的控制權;只不過絕對真理一個表現為來自上帝的宿命,一個表現為來自物性的客觀規律。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設立終極的理想,來誘惑歷史,並以終極理想的名義,要求對人類命運的主宰權;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理想狀態屬於地平線之外的天國,一個是地平線之內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把普遍的社會仇恨奉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如此一來,從絕對真理得到合理性和神聖性祝福的仇恨,便衝決道德的堤壩,表現為殘酷至極的國家恐怖主義和獸性的泛濫;只不過前者仇恨的對象被設定為異教徒,後者仇恨的對象則冠名為「階級敵人」或者「敵對勢力」。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把摧殘精神多元化和推動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視為實現絕對真理統治的天職;不同之處只表現為,前者的絕對真理是來自天主教教廷對《聖經》的理解,後者的絕對真理是來自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對物性邏輯和歷史必然規律的洞察。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以拯救全人類,作為世界性政治擴張的道德基礎;只不過前者要實現的是天主教對世界的絕對統治,而後者要把所有族群都置於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社會概念之下。
這兩種精神現象,都設立組織嚴密的具有精神特權的團隊,而且其精神的特權又得到專斷的政治特權的加持;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精神特權集團稱為教士階層,一個精神特權集團稱為共產黨。
我們還可以從更多角度對中世紀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同質性作更全面的審視。然而,面面俱到,往往意味著主題淹沒於瑣碎之中;僅根據上述對比分析,已經足以使人看清,中世紀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遠隔千年時間所顯示出的精神風格的相似性——它們具有極權主義的共同的文化基因;共產主義是歐洲中世紀極權主義鬼魂的近現代復活。
不過,正如古希臘哲人指出的那樣,世間沒有完全相同的事與物,甚至兩滴海水也有差別。以共產主義名義復活的西方極權文化傳統也必定表現出時代的特徵——時代的特徵,那是中世紀鬼魂開啟近現代復活之門的鑰匙。從思想形式的角度審視,共產主義的主要時代特徵可以概括如下:
由於古希臘文明的復興是近代史的時代精神的鑄造者,所以,西方極權主義儘管本質上源於古猶太智慧的絕對真理意識,然而,它的近代復活的經典形式,即共產主義,卻不得不披上源自古希臘的思想外衣,於是,詭辯論與唯物主義的結合,宿命論與邏輯意識的結合,等等一些具有明確古希臘智慧個性的理論,便為馬克思主義作哲學的奠基;同時,由於從古希臘文化的自然理性崇拜中崛起的科學理性成為時代的力量象徵,所以,馬克思又用「科學」的名義,裝飾他的共產主義宿命論的思想之屋。
只配用淺薄的思想能力觸摸表象的庸人學者,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外形,便將其歸類為古希臘文明復興的思想範疇。這種歸類是錯誤的。因為,共產主義的本質不在於理論的外形,而在於理論外形所承載的極權主義靈魂——以絕對真理的神聖名義,要求對人類的精神和世界命運實施鐵血統治的權力,並論證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的合理性。
事實上,從歐洲到東亞大陸,共產主義政治實踐的全部內容,都表現為極端的極權專制政權,以及與這種權力模式如影隨形的國家恐怖主義。這種事實的結論正是共產主義本質的體現。創立唯一的絕對真理的思想暴君,否定精神自由,肯定宿命——這才是極權文化的靈魂。至於思想暴君被謊稱為上帝意志,還是必然的物性規律,並不決定本質。
「還魂的鬼是醜陋的」。中世紀極權政治以上帝的意志作為絕對真理,畢竟還為人類的救贖保留下一絲餘地,即生命的神聖感;只要生命神聖感沒有完全凋殘,人就不至於徹底墮落為魔鬼。馬克思將絕對真理表述為物性規律,意味著共產主義是以物性為最高信仰的宗教;人的精神也被歸結為物質的一種存在形式。這既是對人的概念的侮辱,也是對生命神聖感的根本顛覆:人本質上不過是一塊物質,一堆塵世的欲望,一塊終將在死亡中腐爛發臭的肉。
對人的本質懷抱如此陰鬱的觀念,人格的高貴與美就失去了可能。這正是共產主義政治實踐大規模虐殺人類時顯出無與倫比的粗俗與冷酷的哲學原因——殺人,就像劈開一塊塊腐朽的木頭。
理想主義是引導人類升華的希望。可是,人的本質被歸結為物質,物慾就合乎邏輯地成為人類命運的主導,成為理想主義的內涵。理想主義物慾化,人類升華為美而高貴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就被斬斷。充滿濃烈物慾臭氣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通向共產主義理想的經濟決定論的宿命之路,正是人由精神存在退化成一堆蠕動的物性貪慾的墮落過程。
人區別於萬物之處,在於精神意境;人類歷史的本質,表現為自然史之上的文化進程。科學理性則是客體邏輯在智慧中的精緻映像。正由於科學理性本質上是物質世界的邏輯,所以它才蘊含著巨大的物性能量。科學理性邏輯的表述應當歸類於自然史的領域,而不屬於人類心靈史的範疇,儘管科學理性是一種智慧的現象。因此,當馬克思把共產主義宿命論冠以科學之名時,實際上是把人類的文化降低為物性的邏輯史。
討論至此,相信許多讀者已經開始感到厭惡——注視墮落、醜陋、血腥的存在,當然令人厭惡。共產主義理論之所以能泛濫於歐亞大陸,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馬克思洞悉人性中的墮落、醜陋和對發泄血腥仇恨的渴望,並在人性的全部弱點之上,構築起他的理論基礎。
共產主義恰是西方極權文化的最俗不可耐的墮落形式。我對這種理論厭惡至極:我厭惡絕對真理的信仰,因為,它意味著思想的墓碑和囚禁精神自由的鐵牢;我厭惡以仇恨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因為,這種觀念陰鬱得像劊子手的眼睛;我厭惡把人視為蠕動的物慾,把人類的命運表述為經濟決定論,因為,那太粗俗,太接近奸商只能聽懂金錢召喚的心;我更厭惡塗在醜陋理論上的理想主義的油彩——就像裝嫩的老女人臉上厚厚的脂粉,經常由於皺紋的抽搐而掉落下來。
既然厭惡,為什麼還要引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作思想的關注?原因很簡單——只因為來自西方的魔鬼,馬克思主義,把惡毒至極的詛咒加諸於中國的命運之上,而中共暴政則將通過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詛咒人類的命運。
中共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專制集團。中共統治中國的過程表述曠古絕今的文化悲劇:在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之下,中國文化精神香消玉殞——那比生物性種族滅絕更加殘酷,因為,被屠戮的是曾經屬於金色種族的靈魂,而心的悲苦超越肉體疼痛。
中共建政以來的全部歷史,就是中國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中國早已喪失文化的祖國,心靈的家園;中共權貴是中國萬年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它背叛文化的祖國,出賣精神的故鄉;中共權貴的政治奴隸和西方極權主義心靈控制下的精神亡國奴——這便是今日中國人的真實地位。
遊學燕趙之地時,我曾在北京一所大學中,與十幾位藏人學生縱酒。那群康巴人形象英俊剛毅:長眉如雄鷹展翅,頭顱似鐵鑄銅雕的藝術品。狂飲大醉之後,藏人竟仰天長哭;康巴鐵漢的悲聲,直可斷金碎石。其中一人似向蒼天大地傾訴心之苦痛——「共產黨要剜出藏人的心,給我們換一顆漢人的心!」
當其時也,我亦感焚身裂骨之痛,卻又欲哭無淚,只能讓一聲長嘆飄散於荒涼的沉默中:「你們不知,共黨狗官首先剜出的是漢人的中國文化之心,並給漢人換上來自西方的魔鬼之心——漢人靈魂已死;活著的,是魔鬼的詛咒。」
如果把西方極權主義文化視為一種生命存在,那麼,這種生命存在的天性在於,運用鐵血強權護衛的絕對真理,通過控制人類的心靈,主宰歷史命運,獲得對世界的所有權。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就是展現魔鬼天性的基本方式。中共建政之後,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為共產主義的理論形式,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思想暴君的加冕;一輪又一輪的大規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精神虐殺的鋒芒最終都指向中國文化。難以計數的承載中國文化之魂的生命,或者屍橫刑場,或者在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上被荒涼的風吹散,或者變成鐵牢陰影下的一片黑紅的枯血。他們凋殘了,他們枯萎了,他們消失了,隨著他們一起死去的,是中國文化精神。
文化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典籍等一類非生命形式,一種是人的心靈。佛教密宗的傳承,極其重視上師的心口之傳,這意味著一種文化哲理——真正的文化神韻只活在心靈中,典籍等非生命形式是埋葬文化的棺木;開啟棺木,看到是文化的骸骨,從人的心靈中,才能找到生機盎然的文化神韻。中共對千萬文化人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大迫害,大虐殺,承載中國文化的心靈被摧殘殆盡,中國文化也因此失去現實的生命形式,中國文化的幽靈只能黯然退出現實,退回落滿時間灰塵的歷史陳跡中。
由於中國實行的是國家權力共產黨寡頭集團私有制,所以,中共權貴有能力把國家權力絕對控制下的國民教育體系,也變成推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常規設置。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再到碩士和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共產主義的基礎理論,從哲學到歷史學,從政治哲學到政治經濟學,都是不變的學習主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垃圾竟能占有大學本科教育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課時。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共產主義神學院」,即中共黨校和團校的設置,中國人從啟蒙到高等教育的完成,乃至成人教育,無不處於具有巴士底獄風格的精神鐵牢中;裡面關押著自由思想的可能,或許還關押著中國文化的鬼魂。
無論庸俗的政客學者基辛格,還是繁瑣的亨廷頓,或者其他更加渺小瑣碎的西方漢學家,當他們把中共官員及其御用文人解讀為當代中國文化的象徵時,他們既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也是在侮辱中國文化。因為,中共的理論和實踐都在表述一個雄辯的事實:讓神州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是中共權貴對西方極權主義文化魔鬼的承諾;擔當屠戮中國文化的行刑者,是中共實現魔鬼承諾的題中之意——只有中國文化血濺刑場,魂飛魄散,西方極權主義文化才能主宰中國人的心靈與命運。
中共強加在當代中國命運上的憲法,其序言中載明,所有中國人都應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奉為指導思想。這是中共權貴在最高政治法律意志之上雕刻的紀功宣言。在中國的土地上,憲法竟以國家強制力的名義,迫使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暴君的地位。這意味著,十五億中國人已被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征服,淪為精神奴隸;這座中共權貴的紀功碑,對於中國文化卻是恥辱的墓碑——中國已經文化亡國。
哀莫大於心死,悲莫甚於國亡。中國正處於心死國滅的大悲哀中。而更可悲之處在於,中國人已經失去理解並感受大悲哀的能力。中國文化曾經以其華彩如朝霞漫天的精神魅力,高踞於東方文明之巔。如今,當她死去時,卻沒有繽紛的花雨和心靈的哀樂為她送葬,也很少有淚水飄落在她的荒涼的死亡之上,因為,十五億中國人的心中已經沒有淚水,而只有貪慾——唯獨我,一個浪跡天涯的哲人與詩者,願為中國文化之殤,作淚如潮湧之祭;我願放聲痛哭,直哭得天慘地愁,直哭得日月無光,直哭得山崩地裂。怎奈我又知,這個世界冷漠得不再能被從真情中湧現的淚濤所感動。既然如此,不哭也罷;就讓我只把屬於蒼天大地的悲哀埋葬在虛無之中。
來源:袁紅冰:《人類大劫難——關於世界末日的再思考》節選
——《自由聖火》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