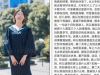孫仲旭(資料圖片)。圖/CFP
8月29日晚,網友「橋東里」在微博上透露,他受家屬之託告知:「青年翻譯家孫仲旭先生於2014年8月28日在廣州辭世,享年41歲。」有出版人稱孫仲旭因抑鬱症自殺,孫先生的兒子向業內人士證實這一說法,並稱「爸爸已經解脫了。」
孫仲旭生於1973年,畢業於鄭州大學外文系,翻譯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農場》《巴黎倫敦落魄記》,伍迪·艾倫的《門薩的娼妓》,奈保爾的《作家看人》,以及塞林格的《麥田裡的守望者》等,總計30多部。其中《麥田裡的守望者》對他的人生影響巨大,他曾說:「從譯《麥田裡的守望者》起,讓我走上了翻譯之路。」
昨晚,孫仲旭去世的消息傳出後,很多翻譯界、出版界、作家,包括普通讀者都感到震驚。孫仲旭本人8月4日還曾在網上發布最新翻譯的譯文《情感教育》,很多網友在這條譯文下留言表示哀悼。著名翻譯家余中先說:「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很喜歡孫仲旭的譯文,給他做過編輯,一直以為他很年輕,很有為。願他安息。」
孫仲旭的早逝特別讓一些青年作家感到傷心。青年作家阿乙說:「讀過孫先生五六本譯作,受益很多,廣州見過一次,謙卑之人,就活在書本上吧。」張悅然說:「今晚睡前讓我們選一本孫仲旭先生翻譯的書來讀,以此來悼念他吧。」
【悼念@孫仲旭】和奧威爾一樣,孫也是個太過認真的人,不能把作品僅當作作品,一個「他人的故事」;他每譯一本,便要沒入作者的內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從頭進去,從腳出來。他不只是譯者,他還是一個試棺者。當得知孫譯《1984》譯到嚎啕大哭時,我想我不得不重新審視奧威爾了。
試棺者孫仲旭
作者:雲也退
網際網路的功績之一,是讓一個人的故事,他的愛、困惑與死亡激起波瀾,而網際網路的惡劣,則是讓你看到絕大多數人對此毫不關心,甚至反應苛酷。沒有網際網路時,我們的世界就這麼大,我們知足於有限的、看得見的反饋,而現在,多少怨怒恚恨皆緣於親眼見到了虛無,而我們的奮鬥是在與它作無望的互搏。
孫仲旭去世,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在豆瓣上的個人作品豆列。浸淫文字和書之人,應該是沖淡的,因為他投入多大的努力,一年兩年,五年十年,體現在別人眼裡不過就是一塊統一規格的封面,真有「廣廈萬間,臥眠七尺」的味道。我讀過不少譯本,譯者在後記里談「譯事之艱」,例行公事地(在我看來是這樣)感謝所有要感謝的人,妻兒老小、師友、責任編輯,等等,這些字都是給自己寫的,自己在乎,但不敢妄企他人的在乎;甚至作者也是,多少次我看到卷首的「致中國讀者」,心中便想:「中國讀者」,這個人群有多大呢?其中又有多大的比例,會在乎這個「致」呢?
寫字從來便是一樁枉拋心力的事,寫字者最大的慰藉,甚至不是拿到高額酬勞——那已經不叫慰藉了——而是看到多少自己欽敬的前賢也長期苦於枵腹,憂於來日。看豆列,孫仲旭所譯之前輩作者,我讀過的很有限,但我知道西爾維亞·普拉思曾經四度自殺,雪莉·傑克遜英年早逝,雷蒙德·卡佛掙扎在赤貧線上,理察·耶茨的抑鬱很有名,喬治·歐威爾在年近不惑時仍在為生計恐慌,急於找份工作,最後好歹在BBC當上了戰時播音員。可他又太認真,整日憤恨於戰時媒體的滿口謊言、扭曲事實,他寫《一九八四》,部分靈感便來自在BBC所受洗腦的經歷。
普拉思,奧威爾,傑克遜,耶茨,深受耶茨影響的卡佛,還有早早隱居的J.D.塞林格,甚至包括伍迪·艾倫,此外,還有孫仲旭雖未翻譯,卻影響了耶茨、卡佛等人的菲茨傑拉德。這些人,因為孫的緣故好像結成了一個共同體。和奧威爾一樣,孫也是個太過認真的人,不能把作品僅僅當作作品,當作一具標本,一個「他人的故事」;他每譯一本,便要沒入作者的內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從頭進去,從腳出來。他不只是譯者,他還是一個試棺者。
他譯奧威爾和塞林格時,我便問他為何去做一些炒冷飯的事。在我看來,普通讀者如我,豈能放棄董樂山、施咸榮譯本,來選讀你的譯本呢?董、施皆有大師才子之名,縱你有強過他們的地方,如不做一些宵小之事,例如斷章取義地腆著臉吆喝自己,想有所「成」,可能性太小。孫仲旭說,他就是喜歡,喜歡,再加上編輯的邀約,這事就做了。
我知道他有多愛奧威爾,這位享壽不足五秩、病懨懨、陰沉沉的作家卻是他翻譯的起點,每重印一次,他就修訂一番。過去不在意,因為他不是我的菜,但當得知,孫仲旭譯《一九八四》譯到嚎啕大哭時,我想我不得不重新審視奧威爾了。
這不僅是出於對孫仲旭品位和人格的信任。讀文學的人,尤其是讀耶茨、讀普拉思、讀卡佛的人,都懂得只要有一個人痛哭失聲,這世界——原諒我講這麼文藝的話——便值得推倒重來。
很多老前輩和不太老的前輩都說,做翻譯,或者做廣義上的文字創作,儘量有份工作。命運待孫仲旭已相當不錯,剛認識時,他便與我說,像他這樣,沒學過法律卻能從事法務,領一份相當不錯的薪水,還能有大把餘暇做自己愛做之事,很好了。但說話時,我並不知道他會連年累月地翻譯,至今出版了37本書。37,幾近追上了他的卒歲,若他假自己以年,「等身」不是問題。
而現在我們知道,即便是如此的命運也不能削平這個平和的人內里的崎嶇;甚或正是這種命運,才讓他無法忍受繼續這樣下去,去面對又一個黑夜過後的白晝。我猜他無法忍受自己的分裂,以文學翻譯為生之酷愛,卻還得蹭蹬俗世聊以哺給,無法傾身於酷愛之中,猶如海因里希·馮·奧夫特爾丁根無法覓獲那朵夢中的藍花。就是這分裂,在那些不懂、不讀、不屑文學的人,自然也不會去「凝視深淵」的人看來,難道不值得他燒一柱高香,額手稱幸麼?
以前讀普拉思自傳小說《鐘形罩》,很疑慮為什麼人們要讚賞那麼沉重的書,一個女詩人親身記錄自己的毀滅,以女性少有的滑稽戲謔起筆,一步步進入常見的可怕的抑鬱心境,時間越過越快,因為生活的內容越來越寡淡、乏味、陳陳相因,再無新人可期,再無鮮美的雲在月上飛揚。我想,或許這跟看恐怖片的原理是一樣的:見到了別人的苦,合上書本後,才能享受自己的寧靜。
但,一本文學書真的只是恐怖片麼?編輯們都說,每次有英語新書都想著問問Luke,他們其實也都明白,這一本本的小說,而且大多是描寫人的某種失敗的小說,會磨損一個譯者,不只是他的光陰,還有對生的理解和認知。最好的故事都是悲劇,主人公無可挽回地毀於他的人性弱點:他們建房子,他們鋪路,他們相愛,然後,作者飛到空中或跳到對岸,高喊著「完了,完了,都完了」。我們掩卷,悵然仰首:是啊,怎麼就都完了呢?
試棺者孫仲旭,多少次浸入悲劇又廝搏而出,以至於他的非洲之行,看起來都像是面對虛無最後的掙扎,讓時間過得慢一點,甚至重煥新鮮。但是,還是讓我們不建房子也不鋪路吧;我們建一座房子在心裡,鋪一條路纏捲起來在靈魂里。我們在內部都會不死。在內部,一位傑出的譯者能得到他想要的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