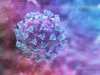十幾天沒有出過小區門了。我今天下午戴上口罩、護目鏡和手套,步行到朝陽區四得公園滑滑板。
我拿著滑板正常進入,開始滑板。期間沒有接觸任何人。四得公園今天人比想像的要多,還看到約4個人在跑步的時候沒有戴口罩。
坐在路邊休息的時候,突然保全上來,指出我不能用這個「車」在公園裡。我說這是滑板不是車。他就改口說在公園裡不能滑板。我第一反應就是覺得非常不可理喻,公園裡憑什麼不允許滑板?哪兒來的規定?
我要求他出示規定,他拿不出來,我說那你去找你領導(制定規定的人)來跟我說。我本質上是覺得:這樣的規定很無理。這樣的情形下,如果我因為沒有戴口罩被保全攔下我覺得情有可原,可是為什麼不讓我滑板?
我覺得在他沒有拿出明文規定之前,我可以繼續滑板,就滑走了。很快又被保全攔下。他直接擋在我前面(這是非常危險的行為,因為我這樣很容易摔跤)。然後我詢問明文規定,他依然沒有出示。於是我繼續往前走,想往前滑到門口就離開算了。
結果這時候保全在後面吼了一句:「你年紀輕輕的,別跟公園裡的大媽似的」。這句話立馬引起了我的不適,我認為不應該這樣侮辱女性,因為侮辱大媽也是侮辱我。我一邊滑一邊回了一句:「你為什麼要這樣侮辱大媽,難道你媽不是大媽嗎?」當時旁邊的幾個大媽還聽見了,後來我才知道她們覺得我在罵保全,根本沒有意識到我在捍衛的對象是所有女性。
我滑到靠近門口的跑道邊停下來,準備跟保全們說清楚我的訴求,提出我認為這項規定不合理的建議。這時候那個「罵大媽」的保全和其他幾個保全都過來圍著我,陣勢很大。我依然提出的要求是:給我看你們的明文規定,但他們依然堅持讓我出去,說明文規定在大門外面。
但我認為沒有看到明文規定之前,他們沒有資格趕我出去。我說:「這是公園,我是公民」。並且要求他們把規定拍給我看,因為我至此不敢相信,一個正常公園會禁止人們滑板。這個過程我全程都在手機錄影,也讓他們看到了我在錄影。一方面是為了保障我自己的權益,另一方面是因為我今天一直都在用視頻記錄北京。
這時候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突然一個路過的、自稱北京人的中年男人開始罵我:「這種人就應該把她給拘起來」,然後就進一步辱罵我,並且開始砸我的滑板。

他砸了我的滑板兩次,而且伴隨著類似「我艹你媽x」等極其齷齪的辱罵性的語言。他的妻子也在旁邊附和他:「三歲小孩的車都不讓帶你憑什麼滑板」。我驚訝於他的粗鄙,並且因為他砸我的滑板而開始暴怒。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非常,非常,珍愛我的滑板,珍愛到每次滑完回家都要仔細擦拭,捨不得摔它一次。
我甚至想衝上去打他,可是我打不著他。就算打著了,我的體力也比他弱很多。
令我最生氣難過的,是當時周圍的人,對於他這樣的行為無動於衷、甚至在表示默認。沒人覺得這樣一個男人,這樣對付一個女性,是不對的。甚至不停有人上前指責我,其中包括前面聽見我對保全提出他言語不當的「大媽」。
他們都覺得砸我滑板的人在理,覺得是我在違反公共秩序。他們覺得規定就應該被接受,沒人質疑這樣的規定是不是合理。
這個時候,終於有一個保全把「明文規定」拍照來給我看。是門口一個很小的禁止入內牌子,最下面一排有一個很小滑板的圖標。我當即說好,並且沒有再堅持要滑。
那個砸完我滑板的男人,還屢次要衝上去再砸,都被保全攔了下來。我還親耳聽見他在說:「正憋了一肚子火沒處發泄」、「我看根本不只是湖北人該罵」、「我今天就罵你了砸你車了怎麼了,大不了我砸壞了賠你」。
沒人覺得他這樣說不對。
那個時候我已經氣得開始發抖,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報警。結果周圍的人對我報警的反應竟然是:「警察現在夠忙的了,就你這樣的事你還要打擾警察」。指責我的人包含女性。她們沒有意識到,我在那樣情形下的無助和恐懼。
警察來的時候,那個罵我的男人已經走了。他是在我低頭看手機的間隙溜走的,圍觀的看到了,但沒有人覺得他應該留下來。警察聽完我的陳述問我:「你想怎麼樣?他人都走了我們能怎麼樣?」我說我要求他道歉,如果滑板壞了要賠償。
為了我驗證滑板有沒有壞,我問保全可不可以滑十米,保全點頭,我開始滑的時候,圍觀的人群還有人在罵我,說公園裡不讓滑板。我的滑板雖然有磨損,但是沒壞。警察說如果你還要報警,就跟他去派出所。
我知道去派出所也是不了了之,就離開了公園。
我反思整件事,我唯一的過錯是跟保全溝通的態度不好,但這基於我認為這項規定並不合理的認知。我可以為我的態度道歉。
回到家,我一邊擦我的滑板,一邊大哭。我甚至想,我已經是很堅強的人了,如果是其他更柔弱的女孩,被欺負的時候她們怎麼辦?當女性和男性起衝突的時候,這種體力上的不平等(即使我還練拳擊),都會讓人感到非常無助,是那種從生理出發的無助感。我今天只是據理力爭,圍觀的人就在說:「你怎麼這麼牛逼啊,你爸是北京市市長嗎?」
沒人覺得,無論什麼原因,男性都不應該這樣辱罵、威脅女性。但只要人們看到一個女性在公共場合跟人爭執,就覺得這個人是「潑婦」。那個男人也許知道,他只要沒有動手打我,我報警也不能拿他怎麼樣,但他依然可以損壞我的東西(還很理直氣壯,說:「弄壞了大不了賠你,賠得起」)、依然可以通過不接觸肢體來恐嚇我,讓我感到恐懼和威脅。
而所有圍觀的人,包括半路圍觀的人,都站在他那一邊,都默認了他使用暴力的權力。他們都默認地站在了更強權的一邊,卻從未質疑過強權本身是不是有任何問題。他們不會明白,我並不是在「破壞」秩序,而是在捍衛我們的共同權利。甚至還有大爺過來「教育」我。
從下午開始,我一直難以平復自己的失望和難過,好像課本里讀到魯迅描述的場景,穿越到了當下的生活里,我親眼見到了這個社會真的已經變得非常糟糕。就像我的好朋友小弦@弦子與她的朋友們 說的那樣,最可怕的甚至不是病毒,而是被恐懼扭曲的心理狀態。這是即使疫情結束之後都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她說:「大家只懂得不停讓渡自己的權利,其實讓渡自己的權力之後的結果就是沒人把你當回事,看看一直在自救的湖北人」。
我想到了那些被歧視的湖北人,被迫隔離的人,買不到口罩卻不得不出門而被歧視的人,那些被性侵後反而還要被反告侵犯名譽權的人,那些只是過著日常生活、做著日常工作就莫名其妙被剝奪了生命的人。他們都可能是我們。可是今天在場所有的人,包括女性,沒有人意識到,我也可能是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