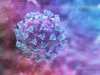武漢肺炎傳播到全世界,在中文媒體卻很難看到一篇說真話的文章
中文世界的輿論場,從未有過如今日一般,外表整齊劃一,內里四分五裂。
和平年代,看一篇說真話的文章都要「驚心動魄,一字千金」。
01
2月6日,李醫生用生命吹響最後一聲哨,朋友圈洗版點燃蠟燭,待以國葬之禮。
需要平民英雄、需要情緒出口、需要問責追責的民意把他捧上高位,他的逝去在整個疫情的進程中被賦予了符號化的象徵意義。
那一夜,連他確切的辭世時間都出現了多個版本,很多人回憶起《新聞編輯室》(Newsroom)里的經典一幕:
「醫生才能宣布他死亡,新聞不能。」
洶湧的民意幾乎在一夜之間退潮,奔赴武漢的調查組至今沒有結論,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他的微博下寫日記,平淡無奇的一段段日常,壘起了網際網路的哭牆,藏著無數人的緬懷、善意、感念和悲傷。
更多的人,可能已經忘了。
02
2月19日,歷時八年的「大家」公眾號被註銷,PC端界面也清理得白茫茫一片。那麼多作者八年來的作品蕩然無存,文字向來比病毒消亡得更快、更早、更徹底。
大家死了,剩餘價值下架了,三聯鳳凰穀雨財新被約談了,新聞實驗室在鋼絲繩上搖搖晃晃。
新聞專業主義的陣地被插滿紅旗,充斥著「戰狼式寫手」和「正能量寫作」。
03
疫情引發的全民關注和巨大流量,原咪蒙系團隊化身「青年大院+野火青年+姨母來了+地球上所有夜晚」的新媒體矩陣,捲土重來。
左手寫《沒有澳洲這場大火,我都不知道中國33年前這麼牛逼》,右手寫《為了感動我們,官媒有多拼?》,還要騰出一隻手寫《疫情中的日本,不全是你想像的那樣》。
左手「粉紅」,右手「憤青」,第三隻手「理中客」,左右逢源,里外通吃。連化作箭垛的咪蒙都自愧不如。
各路大V現身,痛斥青年大院系抄襲洗稿的素行不良,歌頌災難的醜惡嘴臉。
2月27日,咪蒙回應「青年大院」等矩陣號,與咪蒙沒有任何從屬、股權關係,同時稱「這一年,我學習、自省,業務也已經轉型」。
自覺轉型的咪蒙已經在上一輪淨網行動的風暴里湮沒,但是深得其精髓,進化得更為全能的青年大院系依舊招搖。
沒有一線調查團隊,沒有嚴謹客觀的敘事報導,沒有理性中立的觀點立場,裹挾著豐沛而盲目的情緒,開著新時代對沖寫作的聯合收割機,奔襲在韭菜的田野上,追趕在羊群的草原里,馬達轟鳴,只為流量而已。
2月28日,有消息稱「青年大院」被階梯處罰,目前,「青年大院」及其矩陣號均已無法在微信中被搜索到,但已關注用戶仍可正常打開閱讀。
2月29日,原南方周末記者方可成,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博士,營運的「新聞實驗室」因為下場手撕青年大院,被禁言。方可成曾說:
「我有一個夢想,人人獲得優質信息。」
在新聞實驗室「防失聯」的郵件里,他這樣寫道:
「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次疫情都是一次重要的反思時刻:我們應該堅守住哪些價值,我們應該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應該怎樣與彼此相處。」
04
3月6日,發布作家方方武漢日記的公眾號二湘的空間,在屢次圍追堵截中,從六維、七維一路升級到十一維,某一周共發布7篇日記,5篇被404,1篇被禁止收藏轉發,唯一倖存的一篇,主要內容是買菜。
方方在微信被一再封殺,微博關了又開,朋友圈裡只剩下轉發時標題的殘骸《記住,沒有勝利,只有結束》…
唯獨在財新的專欄里,躲在重重的付費牆後,才能看到每篇文字的原貌,但饒是剛硬如財新,依然是不能轉發,不能分享。
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長於大院的家族庇蔭,遊刃有餘於體制內外的胡舒立,財新能否如今日般敢於挑戰禁區,敢於仗義執言,亦或是如大多數行屍走肉的「傳統媒體」,或吹拉彈唱,或噤若寒蟬。
3月7日,編劇六六奉命赴武漢挖掘抗疫故事。3月9日的六六日記里,導言赫然寫著「幸虧我來了,再不來素材都沒了,宣傳能進駐的時候,基本都到了收官時刻。」
這段「幸虧」的言論旋即被輿論猛烈反撲:千萬人沉重的苦難變成了輕飄飄的素材,收官時刻需不需要為了宣傳進駐再推遲幾天?
3月7日,在此次疫情報導中頻頻爆出神操作的長江日報再次出擊,繼《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殘忍的》之後,「開展感恩教育」洗版,該內容旋即被刪除,同步刊發此文的「武漢發布」「鳳凰網」等公眾號也同時刪掉了報導。
耐人尋味的是,鳳凰網在刪掉此文的「404」現場,留下了魯迅先生的名言:
「面具戴太久,就會長到臉上,再想揭下來,除非傷筋動骨扒皮。」
05
3月10日,人物雜誌社專訪武漢抗疫一線醫生的文章被刪,創下微信公眾號歷史上一件堪稱「大型集體行為藝術」的里程碑事件,無數公眾號自發啟動接力,截圖、拼音、二維碼、條形碼、音頻、摩斯密碼、數十種外國語言、譜成歌曲……
無數世界名著用了十幾年都沒有做到的壯舉,此文只用了一天就實現了。
在一片中文的土地上,一篇無處容身的文章,幻化成了無數文字語言形態的版本,全網流傳,微弱的鳴響在黎明前的暗夜,綿延不絕。
06
鼠年的春節,詩人牛皮明明寫了一篇文章《80年代人的生猛,是現在年輕人不曾有過的叛逆》,緬懷逝去的80年代,那些搖滾的、詩意的,自由的,獨立的,充滿生氣的、一無所有的果決勇敢。
當時,各行各業都準備投身一場新生的浪潮,朝氣蓬勃,大家都覺得只要好好做事,一切都會變好的。
這個時代,快車道在發展中頻頻切換,一切似乎已經真的變好,只是沒有人會在閒聊時再提及「文學」「詩歌」「新聞」,「理想」變成油膩中年大叔哄騙小姑娘的套路,「情懷」則是帶貨的眾多姿勢中,較為優雅的一種,所有人張口閉口都是「房價」「股票」「工作」「焦慮」…
那些陽春白雪在紙醉金迷面前一文不值,那些寥寥數語就可以打動人心的力量被紅黑交織的流量爽文輕易瓦解。
熱搜上是孫楊是巨嬰還是被冤的爭論,是肖戰粉絲與同人網站的互撕,是莫名其妙的「冠狀君」「阿中哥」「叉醬」…
社會階層籠罩在「大蕭條將至」的恐懼中,和「風景這邊獨好」的迷之自信里,矛盾不已。
時代不是掉落了一粒灰,明明蒙著厚厚的塵。
07
六十年代,鮑勃迪倫在《答案在風中飄》中追問:
白鴿要飛過多少片海洋,才能在沙丘里安眠?
炮彈要多少次掠過天空,才會被永久的封禁?
一個人要長出多少雙耳朵,才能聽見四周的哀鳴?
一邊是調查記者的名存實亡,寥若星辰,一邊是自媒體的觀點極化,野草叢生,人們感慨著信息繭房帶來的自我強化,和搜索已死下的內容蕪雜,幾乎要捫心自問,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尖銳的批評,那麼不盲目的清醒,和讓人疼痛的真相嗎?
若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若舉目皆是讚美,則自由無意義。
如同過往的每一次一樣,風暴中心的這一場404,很快就會散去,但那呼嘯而過的哨聲,曾為你我而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