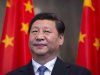專訪熱衷救助難民的德國女權代表蕾貝卡·索莫爾(RebeccaSommer)。索莫爾是德國人權活動分子、藝術家、記者和攝影師。其電影作品多次獲獎。2012年回到德國之前,她在聯合國總部擔任特別顧問,也曾在日內瓦做聯合國人權方面的工作。

她的工作重點是原住民族和國際法,和難民及UNHCR合作,參與原住民權利宣言的國際談判達十年之久。
她受聯合國委託製作了電影《原住民族與聯合國》。
此外,她還參加聯合國氣候談判。
自2012年起,索莫爾積極參與難民人權工作,並建立了支持難民的機構:「逃難與人權工作小組」。
但是,救助難民多年、特別是經歷2015年的難民危機之後,現實讓她拋棄了幻想。
這次對索莫爾的專訪首發於波蘭網站euroislam.pl。
這家歐洲著名網站,是波蘭最早探討難民與伊斯蘭問題的網站。
負責採訪的是Nataliavon der Osten-Sacken(以下簡稱OS)。
在長期接觸伊斯蘭和難民的過程中,這個極左女權代表拋棄了以前的天真幻想,終於憤怒地覺醒了。
看來,還是活生生的現實教育人!
下圖為發表該訪談內容的德國網頁diekolumnisten。
Image
請一起來欣賞這段發人深思的訪談吧!
(一)
OS:索莫爾,你為難民和移民工作多年,是著名的人權活動家。
在2015年難民潮之前,你就因——主張德國應該無上限地接收這些人員而聞名。
是什麼影響了你觀點的改變呢?
索莫爾:我從來沒有支持無上限地接收移民,因為一個國家無限接收難民完全是不可能的。
(編者按:事實上,她以前是主張無上限地接收難民的)
我是人道主義者,是人權分子。
最初一些年,我以為:
到我們這裡來的人,是真正逃難的人,他們會很高興到了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以為他們會有入鄉隨俗的意願,融入這個社會。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噩夢般的清醒一步步到來。
原因有太多方面,我沒法再對事實視而不見。
2015年科隆之夜,自然是一個轉折點。這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都一樣。
(編者按:2015年跨年夜時,德國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爆發了由中東伊斯蘭難民實施的大規模性侵案,多達數千德國女性遭受強姦和性侵。)
最後,我不得不承認:事發時的這種行為,完全符合與我有過關係的絕大多數穆斯林。
德國科隆跨年性侵案震驚全球!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對自己說:
「索莫爾,你現在必須急剎車。那怕僅僅因為你是女權主義者,對女人負有集體責任,也必須如此。」
此前,我一直試圖說服自己。
我還為他們反覆出現的、基於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文化的行為與思維模式,以及奇怪的世界觀,進行辯護。
比如,我說他們是新來的,以此來說服自己。
我曾經天真地認為,他們那些中世紀式的落後觀念,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改變,從而相信自由平等的歐洲價值觀。
我幼稚地以為,每個人都會為這些美好的價值觀,歡欣鼓舞並加以接受。
但是,我不斷重複的、救助難民的親身經歷,使我認識到:
只要真正接觸到穆斯林難民,你就會吃驚地發現,他們是伴隨著另外一個可怕的價值觀成長起來的。
他們從小就被洗腦、被灌輸伊斯蘭教,總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傲慢地俯視我們這些非伊斯蘭的人。
我將之稱為,他們「頭腦中的頭巾」。
另外,他們到了這裡以後,許多人立馬落入原教旨主義伊瑪目的政治伊斯蘭圈套,其原伊斯蘭教旨主義得以加強。
他們被禁止與我們這些非伊斯蘭的人混雜,也不能和我們的生活方式混雜,他們還被禁止接受我們的世界觀和科學。
而德國政府官方,對此完全沒有半點控制。
一個讓我清醒的例子,發生於2016年。
我照顧一組敘利亞難民很長時間,他們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陪伴他們走難民審理流程,幫助他們在政府機關辦理各種手續,給他們找房子、家具、電腦、自行車、衣服,幫助他們找培訓企業、語言班、找工作、申請助學金……
我為各種個案,花費了無數的個人時間。
在一個偶然的時候,我發現他們在對我玩兒塔基亞。他們欺騙了我,讓我失望了。
不過,事先就有其他人警告過我,讓我注意穆斯林的這種塔基亞策略。
(編者按:塔基亞,即是欺騙不信伊斯蘭的卡菲勒的策略)
給我提出這種警告的人,不僅僅是逃離戰爭,而且是不得不逃離穆斯林。
但是,我當時卻聽不進他們的警告。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發現:
這些由我幫忙解決了所有問題,和我一起吃喝玩樂,既不禱告、也不去清真寺、也不過齋月,對原教旨極端穆斯林出口不遜的人,舒服地坐在我的花園裡,卻在背後輕蔑地說我是一個「愚蠢的德國婊子」。
這不僅讓我很傷心欲絕!
畢竟,我是他們的救助者、朋友,我把自己當成他們姐妹和母親,真的對他們充滿了信任。
這成了我恢復理智,重新讓頭腦清醒的一個觸發點。
雖然他們被看作成功融入、是西方人與阿拉伯穆斯林之間友好交往的活生生範例,代表了希望;
而我,對他們完全只有幫助、保護和支持,向他們伸出了友誼之手,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到德國來。
或是,他們給我的,卻是意想不到的惡毒言行侮辱!
這,或許就是我的天真善良,換來的回報。
現在,我的資料夾里,已經有了我經手的救助案例的檔案,
我跟蹤觀察,我曾經照管或者還在照管的一些難民的變化過程;
我也有我們工作小組其他義工經手的一些案例;
只是,這些觀察更仔細,更有批判性。
可惜的是,許多熱情的志願者,已經因為遭遇和我類似的傷心經歷,放棄了活動。
而新來的志願者,則經常和當初的我一樣天真幼稚。
不過,與媒體宣稱的相反,自願者根本就沒有原來那麼多;
而和我一樣已經長時間作志願者的人,現在已經體制化,他們要通過這種工作來掙錢。
因此,他們不會向別人訴說自己的失望,因為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OS:結果是什麼呢?
索莫爾:許多人到現在仍然不願去工作,仍然不會德語。
他們呆在自己的伊斯蘭圈子裡,幾乎沒有、甚或完全沒有德國朋友;
另外一些人則成了犯罪分子,或者日益伊斯蘭極端化。
或者,我們以後會發現他們原來是Al-Nusra(努斯拉陣線,敘利亞恐怖組織)或IS的戰士。他們至今仍然仰慕這些組極端織。
雖然也有個別例外,他們找了工作、也說德語,但是他們大多數人依然有「頭腦中的頭巾」。
他們頑固地持有「穆斯林高人一等」的傲慢,對我們這些非伊斯蘭教的人,有著一種不可言狀的高傲和歧視。
現在,我已經完全沒有興趣,去為這些穆斯林國家來的沉溺於極端伊斯蘭的人干義務工作了。
我現在已經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
已經捕手的個案,我當然會繼續管。但是,捕手新的個案時,我必須確認對方真的是難民。
必須確認他真有理由,到我們這個法律規定男女平等、能吃豬肉、甚至可以一起裸體坐在沙灘上的世俗國家。
但現在,這種自由雖然高貴的,卻已變得無比脆弱。
你可以設想一下:這些大量「腦子裡戴著頭巾的人」,突然來到德國,僅僅他們的數量,就可以改變這裡的一切!
這種情況我們現在就已經可以看到。
現在,我已經變得很謹慎,變得極其多疑。
他們大可以到一個穆斯林國家,去尋求庇護或工作、以及他們所謂的伊斯蘭生活。
而不應該來到德國,並試圖把那些仇視女性的、落後野蠻中世紀價值觀強加給我們。
從長遠上看,這必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傷害。
所以,我現在首先是,幫助那些不得不逃離穆斯林國家的婦女和宗教上的少數派:
政治難民、記者、脫離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穆斯林,尤其是幫助女性。
現在,有些女性憑藉在德國享有的經濟保障,要和自己的丈夫分手。
她們本來就是被強迫結婚的,不得不和自己內心恨著的男人共同生活,並且必須笑著伺候他們。
穆斯林婚姻中,存在很多心理暴力和強姦。
女人不具有作為人的價值,是洩慾對象,而不是伴侶;是能勞動的牲口,是生育機器。
這就是女人,作為一個好的穆斯林女人的標準。
大多數穆斯林對自己的女人毫無尊重,如同對我們不尊重一樣。
當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夫妻都是如此,但絕大多數都是如此。
許多有德國護照的穆斯林,也是如此。
指導他們這麼做的,就是伊斯蘭。
所以,我現在要提出警告。
我有足夠的所見、所聞,有足夠的經歷,手頭有掌握的切實真相。
OS:你提到了「塔基亞」這個詞。你是怎麼理解這個概念的?是怎麼接觸到這個概念的?
索莫爾:多數歐洲人不知道塔基亞這個詞。
如果有人提醒,注意這種他們從宗教上認為合法的欺騙行為,馬上就會被扣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
「塔基亞」的意思就是欺騙。
這一原則策略,允許穆斯林為保護伊斯蘭和穆斯林,對我們非穆斯林進行極端無底線的欺騙。
與非穆斯林打交道時,穆斯林在一定的情況下,允許用不同的方式進行欺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塔基亞。
所謂一定的情況,典型的就是有助於伊斯蘭教的利益,也可以是有利於屬於穆斯林個人的利益。
比如,通過謊言獲得非伊斯蘭人的信任,由此讓非伊斯蘭的人變得軟弱和容易受傷,最後戰勝他們。
所以,背信棄義就是註定的事。
穆斯林可以欺騙任何非伊斯蘭的人。
只要能從欺詐行為中,為自己和阿訇們謀取好處,就不是道德上的卑鄙,他不必為此感到羞恥。
為了從非伊斯蘭的人身上榨取到好處,他可以向你示好、示愛,只要不是出自內心就行。
塔基亞解除了穆斯林對非穆斯林的責任——這是我對和穆斯林男人建立關係的女性提出的警示!
而且,我特別要向——與穆斯林團體締結協約的政治家們提出警告:
穆斯蘭的任何誓言、即使是以阿拉之名發的誓言,都因「塔基亞」欺騙原則一錢不值。
畢竟,阿拉已經規定信徒們可以不守對非伊斯蘭的人發的誓言。
而且唯一的前提就是:撒謊欺騙者,必須內心堅信古蘭經和阿拉。
塔基亞甚至允許穆斯林假裝非穆斯林,只要能贏得對方的信任。
不論對方是個人還是國家,就可以做任何事、說任何話。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可怕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
雖然「塔基亞」欺騙策略來自於什葉派,但遜尼派也採用這一原則,儘管他們極力否認。
「塔基亞」欺騙原則,甚至允許他們吃哈拉姆食品、假裝無神論者。
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在穆斯林國家,對非穆斯林撒謊並不是卑鄙無恥的事。
相反,他們認為是穆斯林的功德。
容易輕信的德國志願者們,遇到的就是這樣一個——他們完全不了解的狡猾宗教策略。
因此,在幫助難民的工作中,經過一段時間你就會發現,許多難民都在通過欺騙操控你,以求儘可能多地得到你熱情的幫助。
而他們首先向你隱瞞的,則是他們事實上是非常原教旨主義的極端穆斯林、是非常拒絕我們的價值觀和這個自由社會的。
訴說不盡的真實個例:
他們跟你講,自己上大學學了醫學、法學或者資訊技術。父母去世了,未成年的弟弟在土耳其的路邊挨餓,他們請求你幫助他們——把快餓死的小弟弟們接來;
或者跟你講他們全家都在戰爭中死亡;
或者一個自稱世俗化的、具有現代思維的溫和派穆斯林丈夫,要求你幫忙把他深愛的妻子(當然和我們一樣生活自由)和孩子接來。
然後,他們的叔叔、伯伯、嬸嬸、姑姑和父母,一大家子就突然全部出現在了德國。
一個死光了的家庭,突然有15口人,分住在三套住房;
弟弟突然來了,父母根本沒死,而是安全地生活在土耳其;
而他自己,也和他說的完全相反,他並不無助,而是敘利亞的一個Al-Nusra鬥士。
他的兄弟,也完全不是什麼溫和穆斯林。
你會發現,他們的畢業證書是買的;
或者,當事人的家庭雖然窮,但卻是生活在敘利亞的一個安全地區,只是為了享受豐厚的福利才來的德國。
又或者你幫一個家庭團聚了,自稱溫和的丈夫卻突然問你,能不能幫忙他把另外一個老婆和其他的孩子也接來;
或者號稱深愛現代生活方式的妻子,卻蒙頭蓋面地來到德國,講述自己多麼不幸,只因丈夫是一個極其虔誠的穆斯林並且殘忍地毆打她。
從這些實例中,我意識到:
穆斯林是在利用他人的天真、利用我們這些非伊斯蘭的人——他們眼中的懦弱者。
在他們看來,這種欺騙,根本就不是什麼需要譴責的糟糕事。
儘管伊斯蘭教本身,就足夠帶來衝突,但問題卻不「僅僅」是伊斯蘭。
這些新到來的伊斯蘭難民,往往是年輕人。
他們是在很古舊的、很守舊的、部落意識濃厚的社會結構中,完成的社會化過程。
其中一些東西,比如血親復仇和榮譽謀殺,還占據他們腦子的統治地位。
他們本來就出身於親近暴力的文化,弱肉強食是法則,使用暴力是顯示男人氣與強勢的正面行為。
而對國家、其他非伊斯蘭的人、尤其是對女性,妥協退讓則意味著軟弱,而軟弱是可以被利用的。
他們原來的國家,充滿著持續許多個世紀的族群衝突:
遜尼派-什葉派、穆斯林-基督徒、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庫德人、阿拉伯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等。
到了德國之後,他們又把這些衝突搬進了難民營和公眾空間。
不過,伊斯蘭神學卻成為將他們聯接在一起的紐帶。
最後,他們還是兄弟,共同的對手是我們。這就是事實!
然而,負責相關事務的政治家、左派、綠黨、那些叫喊「沒有人是非法的」的人,要麼對此一無所知,要麼對此不予重視。
這兩者情況,都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事實上,在伊斯蘭主導的社會氛圍中,強者為上。
如果你,衷心對他們施以援手,就不符合他們的世界觀。在他們眼裡,你就是愚蠢,是弱者。
他們就是這麼看我們的:認為我們是傻瓜,我們的社會是懦夫的社會。
多數歐洲人都不能理解這一點。因為這樣的行為,不符合我們賴以為基礎的、經過改革的、開明的基督教-人道主義價值觀體系。
但是,如果我發現穆斯林有矛盾的地方,無論是說的話還是行為,那我就會提醒自己要警惕、小心,這就是塔基亞!
OS:你在難民營工作過。你注意到了什麼呢?
索莫爾:許多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人,在難民營聚集,其中也有很有遭受穆斯林壓迫、迫害、強姦、酷刑折磨、整村被燒光的人。
紛爭衝突的緣由很多,但最常見的是——穆斯林壓迫或者鄙視非穆斯林。
難民營中,穆斯林占多數,他們許多人好像相信自己是某種「超人」。
而所有不信伊斯蘭教的人,都低他們一等。
這種衝突在狹小的空間內,更加激化。比如,有穆斯林不允許非信徒和他們共用廚房或衛生間,非信徒直接被傲慢粗暴地趕走。
經常有穆斯林男人騷擾女性,也騷擾單身到來的穆斯林女性。
在有些案例中,有土耳其、阿拉伯甚或吉普賽移民背景的穆斯林保全也參與其中。
在這種案例中,也全是穆斯林敵視其他人,不論是來自哪個國家的。
我自己就經歷過一個案例,一個來自厄利垂亞的女難民受到穆斯林保全的性騷擾。
我們不得不報警,但是卻沒有結果。
OS:你講到志願者受到性騷擾,但是媒體卻從來沒有這方面的報導。這是為什麼?
索莫爾:女性志願者受到性騷擾或是強姦的情況,其實早就反覆發生。
但是,我們都沒有報過案,因為我們都不想被看成難民的敵人、不想給難民營造成麻煩。
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在我身上發生過的「自我欺騙」也在起作用,就是不斷的為他們開脫:
他是新來的,不了解我們的文化。
顯然,這種天真幼稚的託詞,沒有與伊斯蘭教教育出來的男性,在面對非信徒和女性時,所表現出來的優越感聯繫起來。
伊斯蘭難民的這種優越感,在面對歐洲「婊子」時,尤其突出。
因為,他們正是腦子裡裝著這種東西,來到歐洲的。
我的團隊中,尤其是給難民上德語課的人、每星期都要和難民接觸多次的志願者,就反覆受到性騷擾甚至強姦。
有這樣一個可怕的例子:
一個女志願者給一個巴基斯坦人上了三個月的德語課,每星期兩次,每次一個半小時。
她認為,一切進展非常好,想繼續很平常地表現出人性化。
當她被邀請去吃飯時,她以為,他只是想對她付出的義務幫助表達謝意;
而這個難民想的卻是,這個婊子要性交。
這位女性根本就沒有想到:
伊斯蘭圈子的許多男人,只會把她這樣不信教的女性,看作不道德、只能永遠供男人支配發泄的對象。
而且,這個巴基斯坦難民開始的時候,表現得很和善、懂禮貌、有教養。也就是採用了前面說的塔基亞欺騙原則。
這就讓她更加意想不到了。
隨後發生的事情,自然成了很令人意外的憤怒:
她要離開的時候,這個一直「友好、客氣」的難民,突然揪著她的頭髮,把她拖進了衛生間裡強暴毆打。
他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走:這個婊子為什麼會一個人來到他的房間?
(二)
OS:你怎麼描述伊斯蘭難民對女性的態度呢?
索莫爾:如果問穆斯林難民怎麼看待基本人權,比如個人自由、自主、男女平等等。
那麼,我周圍大約75%的穆斯林都會說,他們不同意這些東西。
所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歐洲女孩子和年輕婦女,充滿信任地和他們建立關係,我就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
她們不了解對方的伊斯蘭文化,根本不知道難民們私下裡怎麼說她們。
她們不知道,他們中許多人,其實在故鄉已經有女人。
會在家庭團聚時到這裡,來和丈夫團聚;
或者已經有家庭安排和表妹訂婚,只等著表妹來德國就結婚。
另外一個真相是,大多數穆斯林難民開始的時候,不會顯示自己的信仰,或者表面上還會背叛信仰。
他們吃德國飯,也喝酒,只為了充分利用和德國女性的關係,從而換來的各種福利和享樂。
(編者按:到中國的巴基斯坦和其他伊斯蘭國家的流學牲,其實也是這樣看待中國和中國女人的。)
這些女性天真地以為,他們的伴侶是例外,周圍流傳的各種故事都不符合真相。
這些人中,即使是觀點溫和、積極融入社會,並與德國或其他女性結婚的,我也高度懷疑。
他們的不寬容到了自己的女兒或是別的女人身上,就會赤裸裸地體現出來。
說到底,幾乎每個穆斯林移民,都想要一個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穆斯林女人。
當然最好是戴頭巾的,不穿短衣服,服侍男人,從來不拒絕丈夫,沒有男性朋友,聽從丈夫的命令。
沒有丈夫的許可,不出家門,一切聽從丈夫。
這種和穆斯林的婚姻不需要愛。女人只是穆斯林的一個有特定任務的物件。
而天真的西方女性,充其量只是他們安逸的吊床和跳板,最後用完之後還要踢掉。
因為她們是「蕩婦」,她們就不是合適的「材料」。
說她們是「蕩婦」,是因為她們跟他們睡。
如果西方女人要和他們分手,那麼她就有可能被謀殺,如同發生在Kandel的案件一樣;
或者他會幹一切毀壞她名聲的事情。
(編者按:它們也用相同的眼光,這樣輕蔑地看待中國女人。我們每一個家長都有義務,將這個真相告訴你在外工作和上大學的孩子。)
OS:新移民的性別比例和教育程度如何?我們聽說,逃離戰爭的女人和年輕人,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專業人員。
索莫爾:所謂的難民和移民,絕大多數是男人,2015年以前的情況也是這樣。
不過,最近一些年,有許多家庭團聚的案例。
因此才有了遊說集團編造的神話,說只有家庭、女人和孩子,為逃離轟炸才逃到的德國。
在我經歷的救助難民工作中,直到2015年,我遇到的都幾乎全部是年輕男性。
我幫了許多人,幫助他們把親屬接到德國,而且也很清楚地知道,辦理這些手續會花費大量時間。
許多被接到德國的女人,現在已經懷孕或者已經生了新的孩子。
自2012年到德國來的穆斯林難民,其主要部分是敘利亞人。
對於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我只能很遺憾地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沒有受什麼象樣的教育。
我知道,開始的時候,媒體聲稱:從敘利亞來的難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和不同專業的專家。
但是,這是完全不真實的。
我也曾經散布這樣的謊言,因為我相信難民們跟我說的話。
可真相是,這樣的信息被到處重複引用,但是事實上,只有少數記者真的見到了難民。
而且,既便這些人真的受過什麼大學教育、職業培訓,那也是和我們的社會體系無法兼容的,他們必須從頭開始。
和所有落後國家來的年輕人一樣,他們中的大多數還需要上學,需要接受職業培訓,完成最基本的教育。
而所有這一切,都需要花費數以百億計的龐大資金。
在大多數情況下,我認為多數伊斯蘭移民都沒有能力養家餬口,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
要說受教育程度,索馬利亞和奈及利亞等非洲來的人,也一樣的情況不容樂觀。
再有就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好鬥,信仰的伊斯蘭也很原教旨主義、很極端。
根據我的經歷發現,他們往往受教育程度很低,學習德語極慢。
我就知道,有些人經過三年學習,依然不會說簡單的德語,儘管他們拿著我們大家的錢,不斷地留級重複學習。
而阿富汗、巴基斯坦人:情況也一樣。
我現在還在照顧幾個難民,他們必須從ABC學起,絕大多數要靠國家救濟生活。
如果看看這些人從2012年以來的發展,恐怕他們的情況不會再有改變了。
當然,正面的例外也是有的。
一位敘利亞女人是IT方面的人才,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現在每個月能掙3000歐元。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必須提一下:
她是無神論者,與虔誠信仰伊斯蘭教的老鄉們,已經沒有了關係。
用她自己的話說,她作為一個有現代思維的婦女,在敘利亞受盡了伊斯蘭枷鎖的苦。
按她的說法,「所有虔誠的穆斯林都一樣」。
OS:聽說,來自穆斯林國家的新移民,對本地的自由派穆斯林構成了威脅,是這樣嗎?
索莫爾:我們在德國有特別多的有阿拉伯、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婦女。
她們在德國已經生活多年,在穆斯林家庭結構內,爭取到了一定自主權利。
我有些朋友和熟人逃脫了榮譽謀殺,用新的身份生活,至今還在逃避家族的追殺。
你想,這種事情是發生在德國!
她們不蒙頭,與伴侶未婚同居,爭取到了和這裡的正常人,一樣生活的自由。
她們講,現在許多穆斯林生活的人口密集地區,來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伊斯蘭難民,導致她們的自由又受到了限制。
這種原教旨極端穆斯林,一旦認出這樣一個曾經的伊斯蘭女人,就會不斷與她搭話,批評她穿著太西化,對她進行漫罵甚至發出威脅。
一些女性伊斯蘭難民也在這麼做,她們督促別人戴頭巾、穿「正經」衣服。
而我們的國家,卻依然在為這些缺乏融入意願的人,大把大把地支付社會救濟金,無助地看著他們威脅、攻擊已經融入社會的自由者。
我們本身也在倒退:
許多已經在我們這裡生活很長時間的人,現在又開始戴上了伊斯蘭頭巾。
另外,榮譽謀殺的數量,也在瘋狂增長。
去年,發生在漢堡大學的事情,讓人震驚。
一些穆斯林學生,以各種恐怖可怕的方式,攻擊不戴頭巾的女生,完全影響了大學的運作。
而現在,漢堡大學裡,其它好鬥的挑釁方式已經成為了日常。
比如,要求無豬肉的清真食堂、男女分離的專用祈禱間……甚至只供穆斯林學生行走的道路!
在德國,首先是政治伊斯蘭化。穆斯林在非常努力地進行各種滲透。
他們無休無止地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抱怨受到了侮辱、歧視,聲稱一切都是別人的錯,所有的人都應該對他們退讓。
可怕的是,我們許多政界人士現在也持這種觀點。
這種錯誤觀念的來源是,我們希望任何人在德國都不受到迫害,因而產生了錯誤的寬容觀念。
但是,卻沒有人注意到,受到穆斯林歧視的——正是我們的價值觀和我們自己。
這種黑白顛倒的情況,現在真的讓我很憤怒!
我已經開始對德國人、尤其是對我們女人們,感到傷心和失望了。
我們好心好意地和接納他們,收穫卻是——我們現在要爭取自己祖母們,就已經爭取到的女性自由權利。
OS:聽柏林自由派穆斯林Seyran Ates介紹,包辦婚姻在德國是一個大問題。
索莫爾:我喜歡Seyran Ates,她真是一個很棒、很勇敢的女性。
是的,來自土耳其、中東和巴基斯坦的難民,使穆斯林社區急速壯大,包辦婚姻因此越來越多,甚至兒童買賣也增加了。
這樣的案子,我們也曾經報警,但是警察和官方機構對此很難處理,有時甚至會以「這屬於他們的文化傳統」為理由推脫。
這樣,我們突然在一個國家內有了兩套法律體系!
然而事實是,有些女童被買賣、被當作性奴和勞作的奴隸,她們被剝奪了自由,始終受到控制。
而這一切,竟然就在號稱擁有「民主自由」的德國!
我知道一個案例,一個姑娘被賣了8000歐元;
另一個案例中,一個波蘭的女孩被綁架,成為一個穆斯林家庭的性奴。
我們有些政界人士,在我看來就是罪犯。
他們主張維護這種未成年人的婚姻,說是廢除這樣的婚姻,對已經被嫁出去的女性不好。
這種政治伊斯蘭化傷害的,現在還包括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德國人,特別是女人。
有一個案例中,一個巴基斯坦人強姦一個六歲的德國小姑娘,可是基於他的「文化與宗教背景」,他只被判了一個緩期的刑罰。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婚姻中的家庭暴力。
在穆斯林家庭,丈夫毆打妻子幾乎就是常態。
因為遇上女人不聽話,丈夫什麼時候可以打女人,經文中就有說明。
這也是法官們輕判的理由。甚至還有法官採用雙重標準,用這種錯誤的寬容,掏空我們的法律體系。
我們的法院可以說是偏左的,許多法官有支持移民的態度。
這導致移民或有移民背景的德國人,得到「文化和宗教特權」的案例在不斷增加。
而發放這種伊斯蘭特權竟然也有女法官,我認為這是特別糟糕的事:女人對女人實施傷害!
在如在最近的一個案例中,女法官竟然為一個土耳其強姦犯找開脫的理由。
這個男人把一個女人的頭,夾到床架的格柵中,強姦了她數個小時。
法醫鑑定,受害的女人明顯遭受了極端的暴力,渾身上下都是青斑。
但是,法官對受害者提出的問題卻是:「有沒有可能被告認為,您同意他這麼做?」
受害者回答法庭,她不能判斷。
然後,這個強姦犯就被無罪釋放了。
所以,公眾早就已經在說,強姦和其他重罪,現在有了宗教特權護體。
我們的法律逐漸不再起作用。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一夫多妻。
而我們有的政客,已經在呼籲允許重婚了。
OS:犯罪情況呢?
索莫爾: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我只能講我所在地區的情況,以及從媒體得到的信息。
在漢堡和施荷州,一個阿拉伯家族已經造成了地區恐慌;
在柏林,按專家的說法,一個阿拉伯家族在20年內擴展到了1000多人,主要從事毒品生意。
一個平行的司法體系已經形成,我們的法律體系已經不起作用。
法官、律師、警察好像都怕他們。政府部門已經失去了對他們的控制。
我覺得,女法官克瑞斯汀·漢森就是被謀殺的,因為她曾經想對這些犯罪的阿拉伯家族進行清掃。
眼下,柏林的那個大家族已經進入第三代,對柏林人而言極度危險。
他們形成了一種仇恨和蔑視的文化。
據知情人透露,他們作案時非常冷血,完全沒有情感波動。
他們毫無顧忌,手段殘酷,同樣受到穆斯林宗教意識形態的支持。
這些家族,正在中東伊斯蘭難民中,招收成員。
2012年的時候,人們就在難民營前看到豪車,接走個別的難民或與他們搭話。
我們的志願人員和難民營社工發現,這些人不是難民的親戚,而是來找難民干髒活的黎巴嫩人。
他們到處有洗錢的店鋪,找來難民讓他們在麵包店、披薩店、理髮店、街頭小店、賭場、水煙館去掃黑工,在毒品交易中送貨。
可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依然領取我們國家的救濟金,戲耍我們的民主制度。
而我們呢,我們就讓他們耍!
我的說法是:穆斯林世界笑話死我們了!如果考慮到以前的這一切……我們也真的是傻到家了。
我們這裡還有,其他的中東和北非的伊斯蘭家族組織。
許多人反覆過來避難,領取德國的政府救濟,甚至直接留在了這裡。
他們的生意包括:偽造護照、販賣性奴、強迫組織賣淫。
被買賣的性奴中,還有12歲的少女。
不少這樣的伊斯蘭家族,還採用強姦的手段,然後進行綁架訛詐,製作兒童色情視頻。
我負責照料的人中,就有一個14歲的少女,她來自塞爾維亞,多次被穆斯林成年人輪姦並被錄影,拍出來的視頻在網際網路上廣為流傳。
而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才10歲。她的遭遇對我是一次可怕的打擊。
我知道還有更多這樣的性虐待案例。
我給媒體寄了許多信,卻沒有任何結果。警察也很為難。
我個人認為索馬利亞難民特別危險,因為他們的伊斯蘭極端化信仰和落後的文化,決定了其對婦女的歧視。
OS:聽說現在德國學校的情況,相當糟糕。你怎麼看呢?
索莫爾:對城市小學四年級學生的最新調查表明,50%的孩子有移民背景,教育水平急劇下降,按研究人員的說法已經降到新興國家的水平。
問題最多的是穆斯林家庭的學童,而這些孩子正是有移民背景的學生中的最大群體。
我已經說過,這是一種弱肉強食的文化,其好鬥攻擊性也是一個問題。
與德國家庭不同,穆斯林家庭用體罰教育孩子,如同我耳聞目睹的,父親和哥哥的毆打司空見慣。
這樣做的結果是,穆斯林孩子很好鬥,遇到問題很快就動用暴力,而且採用典型的群狼戰術。
其他文化圈教育出來的孩子更習慣於討論、說理,從小就被教育言論自由和寬容,面對穆斯林家庭的孩子,他們一開始就處於失敗的地位。
講理、討論,這在穆斯林孩子的眼中,是懦夫軟蛋的表現。
這就讓其他文明家庭出身的孩子們,成為潛在的受害者。
另外,這些穆斯林孩子們行動的時候,總是成群結隊。
你要是和一個孩子有衝突,那麼你面對的就是一群人,是幾十個孩子,因為這些孩子們的世界觀也是:「穆斯林針對所有其他人」。
這樣的衝突已經造成了許多嚴重的身體傷害,可老師們卻束手無策,因為法律給他們的強力反應手段極少。
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難民教師培訓項目,在我看來是一個額外的問題:
在故國曾經當過老師的難民,經過快速培訓成為老師。我認為這裡有不少問題。
首先,許多女性戴頭巾,這違反中立原則,給孩子們樹立了一個負面榜樣。
其次,一年半到兩年後,他們還不能掌握足夠的德語,帶來的危險是,孩子們也說錯誤百出的德語。
第三,這種新培訓出來的老師,並沒有受過和德國老師一樣的專業教育。
第四點是我最擔心的:這些老師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不相信進化論或科學,而是只相信古蘭經規定的東西。
有些女老師甚至不和男性握手。
我不想把我們的未來交給這樣的人,也不想看到戴頭巾的老師成為學生的榜樣。
頭巾所意味著性別的隔離是應該的,頭巾所傳達的無言而又意味深長的信息是:我臣服於男人。
頭巾就是信仰的宣示,象徵著把世界分為伊斯蘭和非伊斯蘭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
這種信息,還把女人的頭髮視作陰毛。
我們為什麼要讓這種東西,進入我們的學校呢?
(三)
OS:據我所知,政府有家庭團聚計劃。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索莫爾:有安全官員告訴我,今後三年之內,將會有數百萬人到德國,有到德國與家人團聚的,也有新的避難申請者。
這是災難性的!
我們都知道,融入過程問題極多,但是我們有的政界人士還是走老路,使用「沒有人是非法的」這樣的虛假口號。
我經手照顧的難民不少,可是真正成功融入的,掰著一個手的指頭都能數過來。
我說的成功融入,是指認可德國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身邊有些德國朋友。
我周邊的那些人,都是只和自己的同鄉或者穆斯林交往,生活在一個平行社會,把宗教價值看得高於法律。
這樣,他們的生活與我們的社會是隔離的。
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就將根本不用再適應德國社會。
一個明擺著的穆斯林平行社會,就會得到加強。
我還看到家庭團聚帶來的問題。
我覺得,什麼人想留下來,什麼人屬於傳統的移民,這需要甄別。
一個人是否真的有避難的理由,需要更仔細的審核,可以檢查手機、臉書、推特,不管採用什麼辦法。
因為畢竟要搞清楚,當事人的家庭究竟在哪裡?
我們這裡有許多未成年的難民,其家人生活在安全的地方,但是等著被接到德國。
如果孩子可以回到大家庭里去,為什麼要把全家都接到德國呢?
我們都知道,有些人在這裡,就是被家人先送來打前站的!
比如,我從貝魯特得到消息,那裡有極多的人等著,被接到德國實現家庭團聚。
(省略一段)
家庭團聚這事讓我擔心的是:
家庭在中東穆斯林社會,是按照父權原則組織起來的家族、大家庭。
家庭團聚,就是進口伊斯蘭家庭體系,促進平行社會的形成、給融入造成問題。
有了家庭,年輕人就不需要再適應社會,而是留在自己人的圈子裡,繼續按照原來的伊斯蘭傳統生活。
本來對我們這裡的一切充滿好奇、抱開放心態的小年輕,就因為拒絕非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家庭到了,一轉眼就堅定地反對我們,對我們充滿鄙視和拒絕。
我不希望看到平行的伊斯蘭社會在這裡擴展,最後剝奪我們的自由,要我們女人的命、要所有人的命。
(省略一段)
OS:你認為德國應該怎麼對待伊斯蘭?
索莫爾:政治伊斯蘭,這種意識形態必須受到阻止,而不是繼續被恭維呵護,包括修建如此之多的哈喇寺。
(編者按:哈喇寺即清真寺)
首先,要有法律規定,哈喇寺宣教傳教時什麼東西可以講、尤其是什麼東西不許講。
所以,在細緻審查現有的哈喇寺、調查清楚其經濟來源之前,不能再隨便允許新建更多的哈喇寺。
許多哈喇寺在要求信徒拒絕非信徒、拒絕融入。
這一點在德國電視一台記者Schreiber,最近一次對多家哈喇寺的報導中,講得很明確。
很多哈喇寺,甚至在推動教徒極端化。專家們在多年前就已經發出警告。
哈喇寺依靠土耳其、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的資金建立起來,伊瑪目也由他們資助。
而許多伊瑪目連德語都不會說,政府卻對此漫不經心。
同時,我也反對學校開設宗教課。
我支持學校禁止師生戴頭巾,支持禁止公職人員戴頭巾。
點評:
活生生的現實,總是最能教育人的。這位白左極端女權代表人物的認識轉變,就鮮明地說明了問題。
當然,我不得不承認,她經過親身和穆斯林交往、幫助到德國的伊斯蘭難民,從而獲得了對它們最真切、最深刻的認識。
而這一點,正是七八個讀者,大家共同希望我編輯發布這篇訪談的原因。
可能你們看到我多數時候,都是在寫外國的事。
其實,外國就是中國的鏡子。如果我們自己把握不好,外國事也會成中國事。
別簡單地將這個訪談當成笑話看,想想咱們自己國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