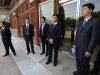每到草木衰黃、柳枝枯萎、沙河冰封,我就會想起2018年的那個冬天,師爺陡然去世,河流頓失滔滔,而我們這些人,則陷入不可抑制的悲傷不能自拔。
三年,日子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世界又是另一番模樣,對於長期生活於動盪困頓,洞察世事變遷於幽微的師爺而言,卻從此安靜了。他不必為病毒的變異而緊張,不用為長期的禁足而犯愁,也不會再為此岸的莫測變幻或喜或憂。
那是寧靜的彼岸,紛紛擾擾的世事再也不是牽絆。但此岸,卻有多少人還在訴說著、懷念著、憑弔著,這個已經離我們遠去的朋友。
十月份少安回京,我倆去麗都旁邊四得公園散步,銀杏正黃得晃眼睛,少安抬手一指:師爺在的時候,經常在這兒散步,就這棵樹下,我還給他拍過照。於是我也去拍了一張,仿佛時空可以重疊,我們曾在同一條路上輕快地走過,在同一棵樹下盤桓,然後為不同的事情發出聲調相同的慨嘆。
而前些日子,或許是師爺祭日將近,夢中有人對我說,施濱海留下的許多文字記錄和作品意義非凡。聽罷此言,我大哭,說一把火全燒了全燒了,剩下的被兄長當廢品賣給收荒匠了。哭著哭著到了十里堡師爺家樓下,我說我知道是哪個樓、哪棵樹,撒一些花瓣祭奠一下。可是,逼仄擁擠的樓群中怎麼都找不到是哪座樓了,樹沒了,坐標沒了,記憶就沒了。夢裡抽泣不已,結果把自己給哭醒了。
三年前的12月6日,是吳偉大哥的生日,原本是個喜樂的日子,卻意外傳來師爺的噩耗。那場火足夠大,大到他無法從烈焰中奪門而去,在十里堡的那間出租屋裡,堆滿了師爺幾十年來積攢起來的書籍和手稿,甚至陽台上都密密麻麻地擺放著屋裡放不下的書籍。我只知道他在生死之間,站在了十二層的陽台上。
很長時間我都會想,一個人身處絕境,是慨然赴死,還是尋求一線希望掙扎著活下去。少安和我都曾設想過,站在陽台上無助的師爺,或許認準了樓下那棵大樹,能夠成為救命稻草。但是,奇蹟卻沒有發生。我只能去感受,那縱身一跳的時刻,有多少不舍和眷戀,就有多重的慘烈和絕望,死神的面容有多麼猙獰,活著對於世人就有多麼美好。
師爺去世後,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朱學勤老師打電話給我說,他真是一語成讖。當年《走向未來叢書》編委之一賈新民跳樓身亡時,他寫道:一些人死了,更多人活了下來,後死者難以融入此後的變動,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遲延數年,還是跳樓而去。這裡既有個人病因,也有巨變留下的創痛,至少是幫助我理解,我所經歷的歷史就像一部被反覆重放拉壞了膠片的無聲電影,再也跳不出這一部位:每隔10年至多20年,總有一群人從樓上跳下,無聲無息。老賈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他是一個悲劇,集合了一切的悲劇",我們的80年代乃至20世紀就是這樣結束的。
施濱海畢業於華東政法大學,做過媒體記者,大概是跑法制口,八十年代他在香港成報做董事,後來因為不可言說的原因坐過兩次牢,說是經濟原因,我當然知道,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經濟問題情色解決的老套路,後來,師爺在南方早年購置的房產一夜之間不再歸自己所有。八十年代末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而師爺的命運與一個被圈禁到死的趙姓老人聯繫在一起,他終於游離於社會的邊緣,成為我們中最不堪的那一個代表。
但有一點,朋友們卻是有共識的,如果他願意,他是可以靠出賣自己出賣別人過上優渥的生活,這樣的機會很多,但他沒有突破底線,他寧願困頓度日,寧願讓個人對他抱有成見,也絕不向強權妥協半步。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對待自己的真誠,對待生命的真誠。
我認識師爺的時候,師爺生活已經比較潦倒了,即使潦倒,買書讀書他從來都不吝惜,因為買書這事兒,他也沒少被喝茶,半夜還被帶走過,HK那家著名的書店,他是常顧客,所以在備註的名單里。施濱海的好友黃鐘說:"濱海和我有一個相似的愛好,或者說毛病,就是有錢無錢,都喜歡買書、讀書,以及溝通關於書的信息。以至於每次搬家,最為頭痛的問題,就是書的安置。不過,書在,夢想就在。"
師爺最困頓潦倒的時候,不得不賣了小西天的房子,搬到離我東邊住宅不遠的地鐵沿線,有時候吃完飯我開車送他到十里堡,他下車前我總是要嘀咕他幾句:必須走路回家哈,走路鍛鍊身體,還省錢。那一段時間,師爺還真是熱愛身體,我看他微信運動里每天都能走上上萬步。有一次我們約好去秀兒家裡吃飯,也是這樣的冬天,冷冷的,到處一片枯黃蕭瑟的氣息,我從朝陽北路開車到十里堡,遠遠見到包子鋪門前的馬路牙子上站著一個手捧鮮花的人,那鮮花在灰白的天空下熠熠生輝。不用說,這麼浪漫的一定是師爺。
師爺長年在北京生活,卻是地道的上海人,少安總開玩笑叫他"壽頭",他說這是他媽媽憐愛地罵他時的稱呼,大概是豬頭的意思。上海城裡的男人,長成師爺這麼魁梧高大的並不多,有時候我們很懷疑他是不是真的上海人,只有每年過年的時候他說要回上海陪90多歲的老媽媽過年,我們才選擇性相信他確實是上海人。也因此,師爺即使潦倒,身上仍然有上海男人的派頭和排場,他總是希望生活過得更精緻一些,但這個時代辜負了他。
師爺走後,我才知道他其實是蒙古血統,去世前的十天左右,他來村里吃飯,羞答答地說他找了一個蒙古女朋友,我叫他帶來我們審查審查,師爺有些慚愧地說:自己生活拮据,未知此事能否長久,等確定了再說吧。但其後不久,一切都成了前塵往事。師爺走後,我還擔心過這個蒙古女郎,他們倆在北京就像一對一的單線聯繫,雖是男女朋友,但各人有各人的住所,並不每日朝夕相處耳鬢廝磨,那女子與周遭又毫無交集,當一個人永遠逝去之後,她怎麼能夠知道他活著還是死去,她該怎樣去想像和面對她所不知道的一切?但師爺去世一年後,有個小西天的老鄰居,又巧合地成了十里堡的新鄰居,主動跟我聯繫上,說了許多身後事,包括這個經常在樓下手動洗車的女朋友,或許她是知道的,只是我們不知道她已經知道和她知道後面對情人驟逝後的心境,也許,不重要了。
還是這個老鄰居小夏,後來告訴我,師爺發生意外後,他從小區住戶的描述中驚詫地判斷出可能是幾天前偶遇還約好了出差回來一起喝酒的師爺,於是去門崗打聽,去出事的房間探查。房門先是鎖著不讓進,有一天忽然打開了,他卻看到很多收荒匠在裡面一捆一捆地搬書搬文稿,收荒匠說是師爺的家人處理的,小夏沒有資格去阻攔,惟有看著一車車三輪開出小區。他慌忙中問人要了幾本書,說是帶幾本回去給小西天的朋友們,做個念想。因為這件事,我跟少安心痛了很長時間,那都是心血啊,師爺幾十年的心血,一把火沒有燒盡,卻最終未能擺脫送進攪拌機化成紙漿的命運。
我搬到鄉下後,多次忽悠師爺和吳偉大哥搬來做鄰居,他倆遲遲不動,我一邊嘴上罵他倆是交際花,到處參加飯局,一邊在心裡想,到底是有些年紀了,不過是為了孤單的人生多沾染些塵世的熱鬧,不讓孤單在孤單中消亡。師爺走後,我總想,要是他真的聽話搬過來了,或許,就不會發生那樣的意外了,但是,生活,從不理會美好的假設。
師爺從八十時代過來,腦子裡都是那個時代的人和事,每次他和吳偉、史義軍到徐慶全家,聊的都是四九年以後的人和事,我驚訝於他們幾個對人對事的記憶都超強,有時候說起一件事發生的時間地點都能精確到哪一天哪一刻。這兩年他一直在寫華國鋒的傳記,我總問他什麼時候出版,他說初稿完成了,但出不了,即使HK,也受限了。有一回去上海,朱學勤老師和我聊起華國鋒為什麼會突然配合老人們一起將王張江姚拿下的事,其中有些細節可讓人參詳,回京第一時間我就跟師爺講,生怕他錯過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師爺說,他去上海跟朱老師已經聊過了。
三年前的今天,師爺遽然長逝,少安說:"濱海!你走過險惡的江湖,你吃過很多苦頭,但是從不抱怨甚至也很少發愁。你暗夜讀顧准,到會心處猛拍大腿激動難言。你永遠不倦地奔走、觀察與思考,力圖看清這個時代。你有平常人的毛病,但你更像一個聖徒般地忠實於信仰,誠心對待朋友。你以"壽頭"自嘲,不計較利害得失,必要時奮不顧身。我們之間的友誼長達三十年,我們有多少暢快的長談和相互打趣。失去你我真的好痛心!"大理的朋友普明也說:"覺得他待人溫和,雖受過迫害但內心堅定。知道他落魄,但沒想到會是這個結局。我覺得曾為撬動鐵幕而付出過代價的每一個人,都值得尊敬。願他安息。"而我當時寫道:"他以這最後的轟然墜地,宣告一個苦難生命的結束,宛如一個時代的寫照,一群人命運的臉譜。"
師爺周年祭日時,一眾生前好友和前同事還曾相聚在四川大廈,憑弔這顆受盡苦難卻從未與魔鬼做過交易的乾淨的靈魂,懷念他從90年代開始為推動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變革所做出的貢獻。如今,師爺已經魂歸上海,安葬在青浦的一家陵園,十月下旬,徐慶全老師代一眾朋友去祭奠亡魂,亂世如斯,情義恆遠。
然時間永是流逝,記憶終將黯淡,越來越少的人會在這個日子想起曾經有個朋友,和我們一同歡喜,和我們一起暢飲,和我們一起穿梭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我們一起去八寶山參加別人的葬禮卻最終把自己變成了葬禮的主角。我只想在未曾忘卻這世界忘卻我之前,記住生命中長長短短路過的朋友。
師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