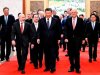進入2022年的春夏之交,歷史似乎正在進入一種另類的輪迴。三十三年前,北京的僵化體制和政治老人以相當於1968年蘇聯出兵干預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的規模和模式鎮壓了北京的大學生運動,然後面對政治的失敗不得不以開放市場經濟和暫時的政治妥協延續著政權。而在2022年,北京再一次面臨著類似的政治失敗。
外界大概很難想像,五月五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關于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的講話言猶在耳,五月二十五日,上周三的下午,李克強總理召開了一個全國十萬行政幹部的電視會議後,堅持了兩年近半的「動態清零」政策隨即土崩瓦解。這標誌著中國過去十年以「治國理政」為口號的治理政治的失敗。
這一周,國務院下屬的醫保局拒絕為國民核酸普測買單,各地方的常態化核酸政策如同釜底抽薪一般;從天津到上海,地方政府口風大變,強調復工復產,拆除街壘和隔離設施,甚至撇清封城責任,試圖在五月三十一日之前如同清零一般清除所有清零痕跡。仿佛文革初期的高潮結束,中國政治又回到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調整期。
不過,李克強政府調整政策的背後,固然是看到了經濟大蕭條的來臨,也看到了人心思變。對動態清零政策下不正常的生活,人民已經難以忍受,當下的中國輿情就像一個堰塞湖,尤以上海和丹東為代表。封城兩月的上海,民怨之廣、之深大概是1950年代初「三反」運動之後從未有過的。甚至,上海市民的絕望情緒,已經波及上海的外國人、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的信心與安全感,他們正在變身「上海難民」紛紛逃離上海,上海封城的極端模式也成為過去兩個月里中國社會輿情的焦點。
在丹東,這個昔日東北最早現代化的都市(安東),不同於被嚴格控制、噤聲的東北、華北和雲南各地,居然罕見地不斷流出封城下的衝突視頻,有警民之間、民眾之間的衝突,在在顯示人民對動態清零的忍受已經達到極限。
上海的大部分區域都已經被封控了一月有餘,居民小區的門口往往由防疫志願人員持續把守。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比如運送食品等基本物資、居民需要出門接受核酸檢測、有人突發急症時,沉重的鐵門才會開啟。
抗疫策略與政治路線
重要的,丹東以外的人民更關心一江之隔的朝鮮,封鎖模式下突然爆發疫情卻也沉著應對,與中國在鴨綠江畔和社交媒體上對朝鮮舉措的嚴防死守形成鮮明對比。在國際社會結束疫情狀態恢復正常之際,中國依靠警察和宣傳兩大暴力機器進行清零的政策也面臨著「盡銳出戰」、難以為繼的窘境。在烏克蘭戰爭的衝擊下,面臨經濟急競速滑冰坡,中國越來越陷入內外交困、閉關鎖國的孤立陷阱,從今年二月冬奧會開幕以來,中國政治高層圍繞是否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的爭論終於公開化,兩種應對疫情的政策路線差異最終上升為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鬥爭。
在這個背景下,過去兩周北京大學生的異動自然被外界賦予了許多想像。他們是在接續三十三年前學生運動的薪火,還是一次無意識的集體行動,自然引發強烈關注。事實上,北京高層對京津大學生的抗爭也是高度敏感,尤其在每年「64」紀念日到來之前,更如驚弓之鳥,擔心北京大學生的不滿可能引發更大規模、或者不可測的抗議運動,不僅讓「動態清零」在政治上破產,而且可能波及今年秋天的二十大。因此,才有北京高校一改過去幾月的校園封閉,在最近幾天紛紛「清校」,力爭將學生們在紀念日來臨前趕出校園。
在這個意義上,過去兩周北京大學生們自發的抗議和集結,像是給堰塞湖一般的輿情大壩捅了一個窟窿,一個看似堅硬牢固的管控體制和堅持清零的政策決心,在高度緊繃的「二十大安保」行動來臨之際逐漸崩解,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其對北京政權的動搖和分裂,固然在規模和烈度上無法與三十三年前的大規模學生民主運動相提並論,卻同樣暴露了當下一個十分接近極權主義政體的阿吉里斯之踵。
觀察北京幾家高校的學生抗議現場,或許能夠發現,京津幾所高校的抗議,從北大、北師大到政法大學和天大,行動和訴求都相當溫和,僅僅以聚集的方式要求擴大校園裡的生活自由和返鄉自由,也僅僅是在校園半封閉兩年多、特別是今年初春季學期的全封閉狀態下的第一次、或許也是最後一次的抗議。北京當局幾乎難以招架,所能做的不過是6月3日之前火速打發學生們離校、回鄉,將所謂「不安定因素」的風險降到最低水平,也根本動搖了官僚集團對「堅持動態清零」的信心。
「新冠三屆」和馴化的大多數
儘管這些北京大學生的輕微抗議,相對所有外省大學生們來說,已經算是極其勇敢地邁出了聚集抗議的一小步。那些京津之外的大學生,包括上海的,可能更能代表這一代學生的精神。他們無比的懦弱和馴服,服從於校方越來越緊、越來越近乎羞辱式、集中營式的校園管控,忍受著生活不便、與社會隔離、也與同學半隔離甚至互相監視的狀態,不敢逾越半步。無他,只因為過去十數年馴化教育的成功,和威權主義家庭和學校教育制度的高壓,以及就業市場(特別是公務員考試)對政治審查的要求。而且,他們將以前所未有逾千萬的規模即將投入一個已經急劇萎縮、面臨蕭條的就業市場。
因是之故,這一代的大學生堪稱「新冠三屆」。與小資產階級、底層民眾、老年人等群體一道,他們淪為新冠疫情的最大受害者。相比之下,只有北京精英大學的學生們略為超脫。尤其是文科發達的北大、北師大和法大校內,在過去幾個月和過去兩年的半封閉中,頗有一批學生以校園為Fiesole,即1348年黑死病當中薄伽丘筆下《十日談》的背景,在目睹和反思疫情期間種種怪現狀的同時,開始了一個過去二十年少有的哲學時刻,如維根斯坦對哲學的定義,以思考和會談向語言迷霧下的荒誕現實展開戰鬥。
其時,也是北京居民在半封城下聚集亮馬河邊、溫榆河畔露營、聚會開始的大眾哲學時刻。北京的學生們不過是在校園裡,較之市民更為主動地開啟了這一哲學時刻。何況,與北京、上海等地公民社會組織在過去十年被打壓殆盡的情形相比,北京校園裡尚保有一些微弱的社團,如幾年前在介入工運方面頗為積極的北大馬克思主義小組,北師大也有傳承十餘年的哲學社。這些星火一般的社團和思考最終將學生們對動態清零的切身不滿轉變為一場原本微不足道卻像捅破天的微型行動。
若與三十三年前的廣場行動相比,北京大學生們的微型行動確實難以擴展,也難以被賦予更多的歷史意義,但在對動態清零的全民不滿的人心轉向中,他們再次代表性地發出了聲音。這些聲音很微弱,在當局的政治安全防控機制下卻被無限放大,不期然地改變了歷史的進程,迫使一個堅持了兩年半的「清零」政策在過去一周土崩瓦解,中國人民迎來了如同「解嚴」一般的解放快感。這或許正是當下中國政治最為詭異也是最為脆弱的要害所在,也是對中國未來政治演變的一次微型預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