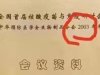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抹茶可可碎片星冰樂。
關於這篇我新寫的文章,我首先要說一說它的題目。
「光,是誰燃燭照亮,」是歌曲《盜墓筆記·十年人間》的第一句歌詞。而這首歌呢,則是八一七稻米節的主題推廣曲(作者註:稻米,就是《盜墓筆記》這部作品的粉絲),由歌手Lao乾媽(李常超)演唱。
但是,我這篇新文章,與這部作品和這首歌曲,似乎並沒有多大的關聯。
我很抱歉,自己在文章的題目和正文中,引用了梨衿老師寫的歌詞。
在此,還望老師本人和各位稻米能夠諒解一下。
好的,接下來,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1.
光,可尋來路艱險,亦可照前方坦蕩。
光,補填殘陋世相。何須度量?
天地蒼茫,歲月無常。
且問:
「光,是誰燃燭照亮?」
……
2.
13日晚上,我打開電腦。甫一進入臉書的好友動態頁面,就看見了這樣一句話:「蔣彥永醫生於3月12日在北京因病去世。我很快寫文章悼念。」
當反應過來它的意思的那一刻,我的呼吸,登時開始變形,強烈的眩暈感,使得我險些跌坐在地上。
原來,不知是在昨天的什麼時候,有一顆星星已經落下來了啊……
我是一個愛好寫作的女生,曾經為很多人和事,寫下過許許多多的文字。但是,或許是因為自己只是個零零後,太年輕了。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形容蔣彥永醫生,也從來都沒有用那種很正式的方式為他寫過什麼。
唉……
如今,那些我在心裡構思了無數遍的,想要寫給這位總在告訴自己,一定要做到絕對不講假話的先生的句子啊,已然成為了悼詞……
啊,春天!春天,就要來了。蔣醫生,讓我再度遇見您的春天,就要來了。再也沒有您的春天,就要來了……
3.
「誒?那是誰啊?」
當第一次聽見手執書卷的祖父提起「蔣彥永」這個名字時,我好奇地問道。
「他,是……一名醫生。」
「啊!就是醫院裡那些穿著白袍的叔叔阿姨嗎?他也會像他們一樣,不是給我打針,就是讓我吃藥嗎?」
「也是,也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說呀?」當時只有五歲的我,總愛刨根問底。
「唉——」祖父聞言,不禁掩卷嘆息。
「孩子,你還太小啊!不懂!」
儘管那時,我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答;但是,小小的我,卻因此記住了一個名字。
3.
鬼使神差地,我在搜索框內,輸入了蔣醫生的名字,按下確認鍵。
「薩斯吹號者,六四屠殺見證人蔣彥永醫生病逝。」
這樣的一則引擎,瞬間映入了我的眼帘。
——吹號者。
是的,是的。常聽人說,那些吹號者的命運啊,往往是無比悲苦的。當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號角的銅皮,使那粗糲的號角發出聲響的時候,常常會有著那細到幾乎看不見的血絲,隨著號聲飛出來……
——見證人。
啊,想想那坦克人,那在六四的翌日隻身立於長安街,阻擋坦克軍隊駛入天安門廣場的身影;想想那個密碼被我的媽媽默認為「198964」的存錢罐;想想那一把為不能到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擺放的空椅子……我又怎能不「獨愴然而涕下」!那一幕又一幕的場景啊,仿佛如大樹生根一般,一遍遍地在我的腦海里無限放大,遍及我腦海的每一個角落,似乎在不斷地向我傳遞著這樣一個信息:不能忘!不能忘!他們的命運是如此悽慘,不能忘!
……
4.
最後,我用已經成為我的「黑歷史」的,仍然在創作的一部偏群像的小說《渴望》裡,史學泰斗秦玉初先生在自己九十歲生日那天對十八歲的小女孩越今安說的一席話,作為這篇《光,是誰燃燭照亮》的結尾吧:
「今安,作為零零後的你,才是十幾歲的年紀,你有選擇。你可以假裝你壓根不清楚八歲生日時收到的存錢罐的密碼為什麼被你媽媽默認為「198964」,可以假裝你完全不了解那些以張慈盈老師為首的年邁的母親是怎樣以偉大的愛對抗無盡的謊言與暴力。可是,人一旦知道了什麼事情後,就難以回到他還不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了。所以說,你完全可以選擇經歷所有在「一九八九六四」時期,那些和你同齡的、已經不在人世的同學們所經歷過的事情——以及那之中蘊含著的他們的希望和痛苦。學習所有他們面對這些希望和痛苦時所做出的努力。你要替他們讀很多有趣的書,體會很多有趣的事:如去更好的學校里深造啦、如談戀愛啦、如結婚啦……也許會被勒令退學,也許會被迫分手、也許會離婚……但是,他們,連這種最呆鈍、最庸俗、最刻板的人生都沒有辦法去經歷。你能明白嗎?而你,要去經歷,並且牢牢地記住他們所有的思想、情緒、感受、記憶與幻想,他們的愛、討厭、恐懼、失重、荒蕪、柔情和想望;你要緊緊地擁抱著他們的痛苦,你可以變成他們,然後,替他們活下去。連著他們的份兒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你可以把這一切的一切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下來,但,你這樣的記錄,並不是為了求得「方寸心安」。雖說你才十八歲,雖說你有很多選擇。不過,你只是為此感到憤怒的話,並不是某些人說的「你不會去『饒恕』他們」。什麼人做什麼事都有點理由。連沒有法律和人權可講的「戒嚴」都有點所謂的「心理學」、「社會學」上的理由。世界上,似乎只有那些同學的理想被鮮血染紅是不需要理由的。所以說,你完全有著牢牢記住的權利。不是因為你心胸多麼「狹窄」,而是沒有人應該被這樣對待。那些同學啊,肯定是在不知道自己的結局會是怎樣的時候,留下了許許多多。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沒有了」。可是,他們留下的東西又顯得如此之清醒,像是他們替所有不能接受的人——比如今安你,接受了這一切的一切。今安,我請你永遠不要去否認自己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遺孤」,去否認自己是個「倖存者」。那些同學,是何等的善良、也是真的愛過。他們的善與愛,只是「失禁」了。忍耐並不是一種美德,把忍耐當作美德,只是這個偽善的世界想要維持它那失調的秩序的一種方式。生氣才是美德。今安,你可以用「生氣」的筆調去參透、去記錄。你想想,能看到你所記錄的東西的人是何等的幸運。他們不用去接觸,就能看到這個世界的背面。」
……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