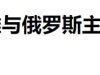【按:俄羅斯的歷經災難、不可預卜、瘋狂、不負責,至今還是世界之災也是人類之謎,甚至從政治層面解讀不了,而不得不延伸到文化和文明層次,便令人唯有想起帕斯捷爾納克借日瓦格發出的浩嘆:「我僅僅是讓全世界,都為我的家鄉俄羅斯的美麗哭泣。」幾年前,應「文化小革命」節目組(隸屬「對話中國」)之約,談《日瓦戈醫生》,從小說到電影,我做了這個綱目(現收入《海慟》),主旨是講一個醫生兼詩人,身處兩次世界大戰、俄國變天之間,人間成地獄,種種苦難和折磨,日瓦戈在艱難世道下,堅守人性的底線,而做人的艱難,又展開於婚戀的波折之中,顯示了人性的複雜和戲劇性;弔詭又在於,血海似的「反法西斯」戰爭,竟讓蘇聯人感覺並不比史達林暴政更恐懼,似乎是他們視死如歸的某種理由。這部小說寫出如此曖昧深邃的意境,怎能不成世界名著?而那三角琴如泣如訴的「拉拉主旋律」永遠令人午夜夢回。】
惡世、好人、離難——《日瓦格醫生》
【20220303按:俄羅斯因其狂妄而「失智」的領袖,而遭全球唾棄,殊為悲慘,然而,俄羅斯就是一個複雜悲劇的民族,他們過去的領袖史達林打敗希特勒後,蹂躪本民族,殘酷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但是俄羅斯存活下來了。俄羅斯的偉大藝術,文學、音樂、繪畫皆為世界之冠,歐洲也要對她頂禮膜拜。曠世傑作《日瓦格醫生》,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將他對俄羅斯的痴迷,移情於筆下的女主人公拉拉,成為精神豐富、內涵複雜而深廣的俄羅斯本身的隱喻,多災多難的俄羅斯女性的象徵。日瓦戈如此浩嘆:「俄羅斯,他的無可比擬的母親,這是具有不朽光輝、歷經災難、作不可預卜之險的俄羅斯,是名揚四海、頑固、奢侈、瘋狂、不負責、殉難的、可敬愛的俄羅斯。」這是一本我讀得最久的小說,前幾年寫過一文介紹它。】
【英國觀察】20211030期:英國天才大導演大衛里恩通過其經典之作《日瓦戈醫生》,演繹了俄羅斯人在共產主義暴政之下的苦難經歷
《日瓦戈醫生》,據經典介紹,是一部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小說波及了1903年夏到40年代末近半個世紀的俄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觸及了道德、政治、哲學、美學、社會、宗教等一系列問題,是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廣闊的歷史容量、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容量的長篇作品。它最初被蘇聯禁止,後由一位義大利出版商帶出蘇聯,而蘇共總書記蘇斯洛夫親自飛往羅馬,要求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干預,因為出版商是意共黨員,而他竟提前退黨,於1957年出版了義大利文版,1958年成為西方最暢銷書,並獲諾貝爾文學獎。
小說
八九前在國內有沒有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的中譯本?藍英年的譯本是1987年出版的,我到海外才看到,因為在網絡上,還是一個殘本,中間缺章,反而更加勾魂。我到美國後,最早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外面的那條拿騷街上的一個舊書店裡,買了一個英文本,吭吭哧哧讀了很多遍、很多年,也是唯一我啃過英譯本的外國小說。
小說對男女主人公,有某種近乎雌雄分體的並列敘述主線。尤里,一個醫生兼詩人,幼年喪父,寄人籬下,一生披肝瀝膽,受盡苦難,最終幾近暴斃街頭,卻堅忍不拔地追求真理和幸福,他是那樣一種人:他們不是英雄,也沒有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在極端狀況下,他們既有不墜世俗的真誠、善良、純真,也有堅韌執著的信念。
如果換到中國和中文語境中,一個知識人遭逢亂世,身處黑暗之中,如何守住做人的底線,雖不得不隨世道險惡而沉浮,但是不害人不作惡,不隨從權勢整人、牟利、構陷,即使做個好人,也不必強出頭抗惡,而是行善、扶弱濟貧、施展不忍之心,那就是《日瓦戈醫生》這本書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回首反右、文革、六四、盛世這六十年,便知此絕非易事,偌大神州有幾人?
女主人公拉拉,才是本書的第一主角,也是精神豐富、內涵複雜而深廣的俄羅斯本身的隱喻,多災多難的俄羅斯女性的象徵。日瓦戈如此浩嘆:「俄羅斯,他的無可比擬的母親,這是具有不朽光輝、歷經災難、作不可預卜之險的俄羅斯,是名揚四海、頑固、奢侈、瘋狂、不負責、殉難的、可敬愛的俄羅斯。」雖然老帕將他對俄羅斯的痴迷移情於筆下的拉拉,令人有墜入西方女性主義之嫌,但是我的感覺,卻是相較於日瓦戈一顆永遠的稚童之心,拉拉則遠不是只有「婦人之仁」。這種張力,其實也是這本書的魅力所在。
這本巨著,與其說它延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小托爾斯泰的知識者命運的俄國文學傳統,不如說它是在宏大歷史中演繹「愛情的受難」,十月革命前後俄羅斯大地上發生的戰亂、變革、宗教、人性、多重戀情等等,都不過是老帕瘋狂文學野心的烹飪材料:「我僅僅是讓全世界,都為我的家鄉俄羅斯的美麗哭泣。」
書的結尾處,末章有一段議論很有趣,是借著日瓦戈的朋友戈爾東的嘴說出來的:
「集體化是一個錯誤,一種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認錯誤。為了掩飾失敗,就得採用一切恐嚇手段讓人們失去思考和議論的能力,強迫他們看到並不存在的東西,極力證明與事實相反的東西。由此而產生葉若夫的前所未聞的殘忍,由此而公布並不打算實行的憲法,進行違背選舉原則的選舉。
「但是當戰爭爆發後,它的現實的恐怖、現實的危險和現實死亡的威脅同不人道的謊言統治相比,給人們帶來了輕鬆,因為它們限制了僵化語言的魔力。
「不僅是處於你那種苦役犯地位的人,而是所有的人,不論在後方還是在前線,都更自由地、舒暢地鬆了口氣,滿懷激情和真正的幸福感投入嚴酷的、殊死的、得救的洪爐。
「戰爭是十幾年革命鎖鏈中特殊的一個環節。作為直接變革本質的原因不再起作用了。間接的結果,成果的成果,後果的後果開始顯露出來。來自災難的力量,性格的鍛鍊,不再有的嬌慣,英雄主義,干一番巨大的、殊死的、前所未有的事業的準備。這是神話般的、令人震驚的品質,它們構成一代人的道德色彩。」
原來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戰爭中蘇聯人的視死如歸,竟是因為同二三十年代史達林大清洗的恐怖相比,戰爭相對還要算輕鬆的,這是希特勒納粹德國遭遇頑強抵抗的一個從未被歷史解釋過的蘇聯式的內因,也顯示出歷史的複雜、迷惑以及細節遠非學術可以窮盡,或許這也使得赫魯雪夫、勃烈日涅夫不靠特務恐怖便無法維持統治。
作者
鮑里斯.列.帕斯捷爾納克,猶太人,文化造詣極高,其父是美術、雕塑、建築學院教授、著名畫家,母親是著名鋼琴家,他從小受家庭薰染,對歐洲文學藝術造詣很深,精通英、德、法三國語言,他自己既有詩人天賦,又受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影響,曾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後轉入歷史哲學系,一九一二年夏赴德國馬爾堡大學攻讀德國哲學,研究新康德主義學說,並非一個普羅作家。
中譯本最早的譯者藍英年,有一本回憶錄《歷史的喘息》,是中文裡極少見的老帕的介紹,說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與那些新作家格格不入,一度布哈林欣賞他。二戰後蘇聯文壇寬鬆,他在1946年開始寫這本書。此時,他也認識了奧莉加.伊文斯卡婭,藍英年稱之為「帕斯捷爾納克的紅顏知己」,也是小說中拉拉的原型。後來就是她把小說交給義大利出版商菲爾特里內利,在義大利出版。
此書脫稿後被蘇聯當局封殺,蘇聯作協長期敵視和批評他,以致義大利出版《日瓦戈醫生》後,又被諾貝爾文學獎選中,他竟不得不拒絕接受,晚年染上憂鬱症,孤獨死去。他一生的隱喻,就是詩人勃洛克所說的「我們是俄羅斯恐怖時代的兒女」,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形容這本書說得更徹底:「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回來攪擾我們了。」
從俄羅斯文學的脈絡來看,蘇俄有兩個托爾斯泰,老的叫列夫,乃舊俄大文豪,其文學位階,不遜於莎士比亞,在圖拉省莊園寫的《戰爭與和平》,幾乎是世界名著之冠;小的叫阿列克謝,生涯恰處於新舊交替的亂世,承俄羅斯文學之遺續,卻並未開啟蘇聯文學之端倪,他有一個《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兩姐妹》、《一九一八》、《陰暗的早晨》,戰亂中小布爾喬亞的掙扎,是從老托小托到帕斯捷爾納克的一個不變的主題,從《戰爭與和平》到《日瓦戈醫生》);小托更描摹蘇俄變天之大驚怵,在故事中經營主角們從苦悶彷徨走向革命覺醒。
但是,日瓦格醫生在1911年十月革命的時候並不是一個革命的反對者,當街上出現被沙皇馬隊砍殺的遊行示威者的時候,他奮不顧身地去搶救革命者,後來他只為了堅守內心的那一點信念,和革命發生了衝突,革命以粗暴的方式蹂躪他,他承受不反抗,也絕不沉淪,這就是他的人道主義,也稱人文主義。所以帕斯捷爾納克是超越了兩位前輩的。
電影
其實中國人最早接觸《日瓦戈醫生》,不是小說而是電影。
赫魯雪夫列此書為禁書,也無緣拍成電影,卻給了《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英國大導演大衛.連恩一個機會,拍了一部史上最高票房大片。電影改編應是非常成功,將小說繁複多頭的線索簡化,凝聚到尤里和拉拉的幾度重逢又離散;從彼得堡到西伯利亞,革命災難中一男二女(日瓦戈妻子冬妮婭)的悲歡離合,以及瓦雷金諾雪屋的燭光、雪原狼嚎,還有電影的主題曲,以俄羅斯三角琴彈奏,雋永無比。結尾落在他們遺失的孩子並不知道自己是誰,那種語言已經用到盡處的沉重,摧人心肺。
自然,這部電影討好,在於它是所謂「西方話語」而非「俄羅斯話語」,也不是對蘇俄革命的暴露才受歡迎,而是把一個西方式的故事放到俄國動亂環境裡去再現,主題是人性問題。這種知識分子式的亂世情愛,是西方文學的一大正宗,大紅大紫的《英國傷員》也是這種題材。至少西方傳統的看法,亂世是一個可以超越道德約束的外在強制,仿佛越是道德的人在此越可以被道德赦免,由此便越見人性的生動和真實。
另外,此劇其實具有很濃厚的女性主義色彩,主人翁是拉拉而不是尤里,作者寫她以女性承受男性權力的欺壓,與科馬洛夫斯基的關係暗示著舊俄制度的蹂躪,其丈夫巴沙是新制度的象徵則遺棄了她,只有尤里這麼一個舊知識分子懂得愛她,這是此片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