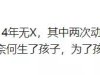近年來,癌症逐漸年輕化。2020年,一項發表於《臨床腫瘤雜誌》的論文明確指出了這一趨勢。以15-39歲年輕人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在2007-2016年這十年間,各年齡段年輕人的癌症發病率都在不斷上升。
很多年輕人不得不「帶癌上班」。複雜而殘酷的現實是,他們背負著癌症治療費用這塊巨石,很多患者上有老下有小,對自己和對家庭的責任纏繞在一起,讓他們不敢停。
他們無法像老年患者那樣縮小自己的世界,一定程度上與社會斷開聯結。他們必須在職場擠出一方生存的空間。
職場上,一個罹患癌症的年輕人可能遭受到哪些阻礙和隱形歧視?生活中,他們的人際聯結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們該如何消解漫長的孤獨和恥感?
更本質地,癌細胞如同一枚潛藏在身體裡的炸彈,改變了生命的刻度,也改變了一個人看待世界的眼光。
《健聞諮詢》和三位年輕的癌症患者聊了聊。以下是她們的故事:
"遲早要屈服於現實」
和同齡人一樣,陳晨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求職期。癌症患者的身份,給她更添了許多不易。
去年夏天,她從北京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她的不少同學已經帶著一份堆滿了大公司名字的簡歷,搬進了金融機構和網際網路大廠的格子間。
陳晨沒有這塊敲門磚。18歲時,她確診乳腺癌,做了右乳全切手術。大學幾年,她的時間被上學、看病和做家教切割。她也跟風去大廠實習過,沒做多久就辭職了。原因很簡單,大廠的實習工資一天一百,而做家教一個小時就有一百四。同學勸她,實習是為了積累經歷。治病費用壓在身上,她想,經歷算什麼,我要的是錢。
但她也做不到像很多同齡人那樣「卷」——身體吃不消。不加班,是她找工作時最看重的一點。畢業後,她在一家頗有名氣的諮詢公司工作過。加班是日常,區別只在於加到幾點。偶爾因為身體原因請假,隔天她一定會被經理叫過去說一頓,績效也會被打低分。
連續多日加班到凌晨一點後,又是一個半夜,陳晨頂著經理的怒視走出公司,很快提出離職。現在她在一家日企工作,日企的文化更有人情味,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月薪幾千塊,她挺滿意,找到工作就行,有錢就行。
畢竟,對於罹患癌症的人來說,當前的求職季堪稱「地獄級」難度。癌症降臨的那刻,職場上很多扇門倏地關上。
首先確定無疑的是,「鐵飯碗」端不上了。《公務員錄用體檢標準》第八條明文規定,惡性腫瘤不合格。而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對癌症的歧視已變成一種默認的規則,招聘方和應聘者對此皆心知肚明。
對正常人來說只是走個過場的入職體檢,卻是一道癌症患者難以逾越的障礙。陳晨透露,走投無路之下,一些患者到網上購買偽造的體檢報告,也有人奔向組織體檢代檢的機構。
近年來,被癌症擊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一項發表於《臨床腫瘤雜誌》的論文指出,癌症正呈現年輕化趨勢。研究結果顯示,2007年至2016年,40歲以下各年齡段的癌症發病率均持續上升。
疾病帶來的痛苦不分年齡段。但和老年患者不同的是,年輕人即使罹患癌症也無法淡出社會生活。他們有著更漫長的人生,有著更為複雜和現實的壓力,必須在職場擠出縫隙。
工作資歷不同的人,遇到的困難也不同。陳晨要撬開緊閉的職場大門。更多患者則是在工作期間查出癌症。他們中的一些人積累了多年工作經驗,是團隊負責人,是高管。治療結束後重回公司,他們要面對的是職場環境在生病前後的巨大落差。
四年前被診斷出直腸癌的周璐是一名會計師。工作多年,她的業務能力受到公司上下認可,還被交託了大量事務性工作。兩年治療期結束後,她趕緊回到公司,卻發現自己驟然清閒下來。領導很客氣,只是每一句對她身體的關照都像在暗示,她未來升職的希望渺茫。
李漾曾經周密的職業規劃也被癌症打亂。她在一家銀行總行任HR,確診乳腺癌前,手下管著一個不小的團隊。治療結束後,她去幾家網際網路公司面試過,但每次到了最後環節,她都「邁不出這條腿」,因為知道自己有所謂的既往症,很難通過體檢。她已經很久沒有更新過簡歷,對大廠生活的想像成為遙遠的記憶。
不僅如此,留在原單位的她不得不面對一個變得更加苛刻的上司。從前做慣的工作現在經常被挑刺,「說我這個不夠全,那個不夠細」。她因此懷疑過自己的能力,後來終於意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領導知道她沒有退路了。
之後的一連串事件印證了她的判斷。公司進行架構調整,領導給李漾增加了一大塊工作內容,但沒給她增派人手。推選後備幹部時,她意外落選。去年年底績效考核的低分又是一次打擊。
她記得「圖窮匕見」的那刻。一次開會時,她因為身體不適告假提前離開。聽同事說,她剛走出去領導便說了一句,「遲早要屈服於現實。」
職場可以殘酷到何種程度,沒有人比癌症患者更了解。他們有過不甘心,也大多產生過強烈的想要離職的念頭。但最終,他們只能勸慰自己接受現狀。
不敢不工作
縱使在職場遇到諸多不公平,癌症患者也要緊緊抓住這根稻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癌症治療費用這塊巨石太重。
曾有親戚建議陳晨不要工作,好好在家養身體。她覺得好笑又無奈:不工作,她哪來的錢養身體?
面對這塊巨石,不是每個患者都有經濟條件良好的家庭可以提供支持。陳晨在單親家庭長大,與母親相依為命。治療期間,僅醫療費就花了十五萬,母親將家中存款盡數投進來也只是剛剛夠用。此外還有一大筆生活費用。母親從家鄉到北京陪她看病,一個月房租就接近五千。
那兩年,陳晨幾乎天天打工,甚至化療期間也會去,「因為真的很缺錢」。
即使工作多年的人,有著穩定的收入和一筆存款,一朝確診癌症,也會人生瞬間傾覆。
36歲的周璐有時想,人生怎麼就到了這一步。得了癌症後,她多了很多不敢,最大的不敢就是不敢不工作。丈夫的收入不高,她的父母也已經退休,靠養老金度日。家中的經濟重擔,她卸不掉。
她不敢細想生病以來花了多少錢,基本治療費就有小几十萬,更不用提在營養品和營養針上的開銷。她也不敢細想之後還要花多少錢。醫生說,基於現在的病情,後續她可能還要用到一款靶向藥,一個月至少一兩萬。
她甚至不敢細想自己的年紀。身邊同齡人都在努力掙錢,她花錢如流水,用朋友的話說,之前那麼拼,掙的錢全交給醫院了。與此同時,升職無望,薪水碰到天花板。每每思及此,她壓力陡增。
而當一個人有了子女,肩上的擔子變得更具象,也就更加不敢停。
周璐原本個性散漫,女兒的出生徹底改變了她。她一下子意識到自己是母親了,要承擔起責任了。這些年,周璐一邊工作一邊帶孩子,還跟朋友一起做了點小生意,每天不超過晚上12點不會睡覺,全年無休,就連坐月子的時候也不例外。
得知自己患上直腸癌的那一刻,周璐「整個人哭都不會哭」,愣在那裡。但有時,她看著孩子,覺得生活似乎也沒有太大變化。她每天照顧孩子衣食起居,輔導功課,忙碌依舊。所謂孟母三遷,她總想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教育環境,那就需要一個位置更好的房子。這個問題不能想,一想就焦慮,她焦慮存款不夠,也焦慮房貸供不起,哪有本錢停下來?
周璐加的幾個病友群中女性居多,其中很多都是媽媽。她們互相鼓勵時最常說的是,「一定要強,自己強了才能保護孩子。」
「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不能頹廢。」周璐強調,「都是責任。」
兩枚炸彈:復發與恥感
帶癌上班如同隨身攜帶炸彈。第一枚是癌症的復發和轉移。
治療結束不等於治癒。前者只表示病灶部位的癌腫已被切除,病情得到緩解和控制,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臨床治癒的標準則高很多,要求患者在治療後生存超過五年,且沒有任何復發跡象。病人即便捱過五年,也不意味著可以高枕無憂。復發和轉移如同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日懸於癌症患者頭頂,令其惶惶。
迄今,周璐已被這枚炸彈砸到過三次。第一次最難熬。手術僅兩個月後的一次檢查結果顯示,腫瘤轉移到了肝上,已經長了四顆。得知消息時,周璐幾近絕望。她問醫生為什麼,手術時淋巴結清掃得不是很乾淨?醫生也給不出一個答案。
之後又出現過兩次轉移。這兩年,每次一聽到指標不好,她的心就懸起來。確診四年了,癌反反覆覆就是斷不了根,好像一隻打不完、干不盡的怪獸,剛被打走一回,生活好不容易恢復一點平靜,它又來了。周璐筋疲力盡。

圖1:周璐在接受治療。
還有一枚炸彈是恥感,無聲,卻一樣不容忽視。
住在小城市,周璐覺得自己臉上好像貼了一個「癌」字,別人看她的眼神都變得不一樣。熟人見到她總會多問一句,最近身體怎麼樣,聽得她心裡難受,「每天都在講癌癌癌,那個字特別恐怖。」
剛回到單位那段時間,周璐整夜睡不著,經常驚恐發作,脾氣變得暴躁,大把大把掉發。她到醫院一查才知道,自己患上了焦慮症。
焦慮的重要來源在她身上——她失去了肛門。剛確診時醫生就告訴她,腫瘤的位置離肛門很近,考慮切除肛門。她試過保肛,為此增加了放化療次數,隨之而來的是體重的急速下降,以及服用大量止痛藥劑才能勉強緩解的劇烈疼痛。
但肛門最終還是沒保住。手術前醫生讓她自己選,保肛還是保命。當天平的另一端是性命,她只能捨棄肛門。醫生將一段可用腸管拉出,縫在腹壁上,從此她的肚臍左邊留下了一個永久性的造口,以及一個每天貼在身上的造口袋,用於收集排泄物。
身上多了一個造口,周璐的神經時刻緊繃著。她不敢用力,所以不再搬運重物。她也怕擠壓到造口,所以再沒穿過緊身的衣服。
更尷尬的是,她的排便變得沒有規律,無法控制時間和地點。她可能在開會,可能在作報告,可能在吃東西,同時就在排便。雖然每天次數不是特別多,但也有她處理不好的時候,會漏氣或漏味。她覺得自卑和苦悶,但不知能對誰訴說。
也有人主動選擇不「隱身」。很多乳腺癌患者會在結療後做乳房重建,陳晨沒有,她找不到這樣做的理由。這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做出的決定。所有人都勸她:做乳房再造吧,這是為你好,你的生活品質會更高,你也會更有信心。家人這樣說,戀人這樣說,主治大夫也這樣說。
陳晨沒有被動搖。身體的殘缺在別人眼中可能顯得可怕,但她自己不在意。她活著不是給別人看的。
孤獨的,隱身的
最傷人的往往不是制度性的歧視,而是來自身邊人的不理解。患病後的種種痛苦,健康人很難真正共情。
得病後,李漾只休過三個月的病假。她考慮過辭職養身體,但父母一聽就強烈反對,怎麼可以不上班,沒有社保怎麼辦。她的父母都在體制內工作,思維傳統,在他們眼中,李漾所在的銀行總行是穩定、體面的代名詞,這麼好的單位能留就留。
為了工作的事,她和父母吵過不知多少次。今年年初,又一次激烈的爭吵後,父親讓她去精神衛生科看看。她去了,做了全套的心理測評,結果顯示一切正常。李漾只能慢慢練習隔絕父母的聲音,「他們是控制欲很強的人,沒辦法。」
令癌症病人更心寒的是家人朋友嫌棄的目光。在封建觀念中,一個人罹患癌症,會被認為沾染了晦氣,變成了不吉利的象徵。
陳晨的姥姥關心她,但自她生病後,姥姥的心中便長了一根刺。她覺得陳晨丟了她的臉,拖了家族的後腿,讓她被街坊鄰居瞧不起,讓她這輩子都沒辦法再在朋友面前炫耀了。
還有一個她從小認識的好朋友,知道她生病後態度大變,明明在一個地方生活,但「怎麼叫都不出來」。多年情誼冷淡下來。她心裡明白,現在的人都是向上社交,你病了,人家就覺得你是個沒用的人了。
被家人嫌棄,被朋友疏遠,陳晨一開始會「揪在裡面」,想不開。癌症又不是傳染病,她也不是因為做了壞事才生的病,為什麼要被這樣對待?
後來她逐漸意識到,除非有過類似的經歷,否則旁人很難對患癌的苦痛感同身受。今年,她一個朋友的父親確診胃癌,朋友一個人忙前忙後,近距離感受到父親患病時承受的巨大痛苦,後來對她感慨,現在才知道原來她這麼不容易,原來抗癌這麼艱難。
有時,社會對癌症的歧視還會包裹著一層「為你好」的外衣出現。
大三那年,陳晨拿到了保研資格。輔導員勸她放棄,理由是讀研究生的壓力大,不適合她。她想反問,不適合讀研,那麼她就適合996的生活嗎?但她不想鬧得難看,畢竟大學四年輔導員幫過她不少。最後,她簽下了放棄保研的承諾書。
這種「關照」浸潤大多數患者的日常生活。病史被別人得知後,他們被同情,被憐憫,與此同時,他們也被隔離出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要被視作正常人,患者首先要調整自我認知。有的病友回去上班後會「玻璃心」,理所當然地覺得自己應當被照顧,李漾不認同這種心態,畢竟公司不會因為關懷個別員工而將業務進度滯後。重回單位後,她懷疑過自己的能力,但看到其他同事能做的事她也都能幹,還能幹得挺好,她的自信心逐步恢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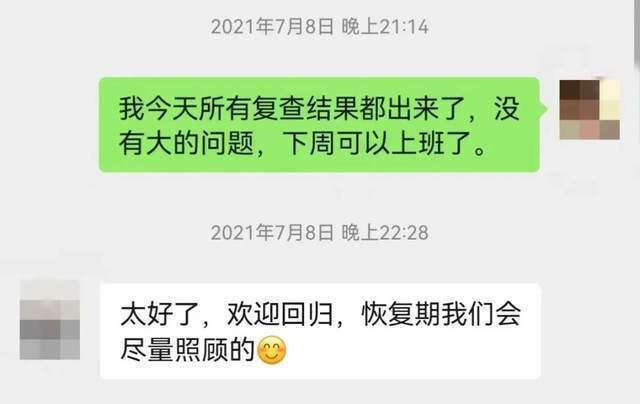
圖2:公司同事表示,會儘量照顧重回單位的李漾。
重回正常人世界的渴望,使得疾病成為一個秘密。在陳晨的公司,沒有人知道她生過病。每月一次的例行開藥是個麻煩事,每次請假時她都要絞盡腦汁編理由,想到這個她就頭疼。
守住這個秘密,因為「不必」,也因為「無用」。「畢竟,最後都得靠自己爬出來。」陳晨說。
當人生無法被規劃
癌症治療結束後,患者大多需要每半年做一次複查。生命的刻度自此改變。
長期的職業規劃不再現實,取而代之的是重重的憂患意識。李漾放棄了跳槽去網際網路大廠的打算,但銀行也並非朝陽行業。
李漾心裡有數,得為自己找好後路。她曾在小紅書發布過幾條有關治療的博文,沒想到收到了許多點讚。她意識到其中有賺錢的空間。這兩年,她考下了三級公共營養師證,學營運,練文案,狂補各種專業知識,現在,她經營著一個主打身心食療的自媒體帳號。
這條路不好走,但至少她已經上路。李漾盤算,萬一哪天退崗回家,她還有一技之長,可以養活自己和孩子。
被疾病改變的還有金錢觀。受家中女性長輩影響,李漾最大的愛好就是買衣服。生病後,她把衣服全部理出來,跟自己說,就這麼多了,真的穿壞了洗壞了才可以扔掉。
到底是努力攢錢還是及時行樂,更多的人在這兩個選項之間搖擺橫跳。
比如陳晨。大多數時候,她在吃穿用度上能省則省。在北京,她不想把大半工資都花在租房上,於是另闢蹊徑——住青旅,這樣即使住在朝陽區的繁華地帶,一晚也只要七十元。但有時她很捨得。她喜歡看電影,一張電影票的價格低則四五十元,高則八九十元,付款時她很少猶豫。
她的存款小目標是十萬元。至於什麼時候才能實現,陳晨決定「隨緣吧」。
人生正是滿懷抱負的階段,突然遭遇劫難,平靜實現起來並不容易。
為緩解焦慮,李漾加入了幾個心理陪伴營,「能量」成為她生活中的高頻詞。微信群中大家互相誇讚,這被「身心靈」同好稱作「加持能量」。遇到新朋友,如果發覺對方的「正能量」很低,她會主動減少接觸。
今年夏天,李漾托朋友找大師算了一個星盤,想知道自己何時轉運。對面發來一條簡單的消息:2029年。
後來,在很多個她感到焦慮的時刻,她都會想起那個預示著遙遠未來的星盤。
她安慰自己,「反正要等到2029年,現在都是積累期,不著急。」
當生命以半年為期,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找到了全新的坐標。
有時想到戛然而止的職業道路,周璐覺得灰心。這種時候,她會想想那些經歷戰亂的國家,無數的婦女兒童流離失所甚至被虐殺,反觀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戰爭的國家,她覺得自己應該知足。
她教育女兒,人的一生會發生太多意外,能健康平安活到老,這已經是很大的本事了。從前,她希望女兒門門功課都要考到90分以上,現在,她會讓女兒多運動,出去玩。

圖3:周璐和女兒在火龍果園
李漾也是如此,她對孩子教育的重點從追求高分轉為對健全人格的培養。她希望兒子成為一個會溝通、有責任心、能夠正確面對生活挫折的人。
在家樓下的小花園,李漾總能看到幾位老人湊在一塊拉家常,夏天搖著蒲扇,冬天戴著毛線帽,話題無非是今天燒的菜,昨晚看的電視劇。
從前的她只會匆匆走過。現在她常不自覺地駐足,感慨道,這樣的生活真好。
(應受訪者要求,陳晨、周璐、李漾為化名。)
作者後記
癌症在陳晨18歲那年不由分說地闖入她的生命。無法避免地,她比從前更多地思考生死,更容易感到悲傷。但同時,殘酷的命運也重塑了陳晨看待世界的尺度,將她雕刻成了一個更柔軟的人。這是癌症留在她生命里真正的印記。
我忘不掉陳晨初見我時說的一番話。那日,她一落座便拋出問題,「對你來說,死亡是什麼?」
她很快自問自答,「對我來說,死亡是一個人身上散發的混合著藥水和體液的味道,死亡是數不清的CT片子和病理報告單,死亡是醫生的一句嘆息,死亡是社會的歧視和家人的不理解,死亡是最後變成一個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在你的世界,死亡可能是一個抽象的、遙遠的概念,但對於我,死亡就是這麼具象,如影隨形。」
她嘆了一口氣,指著桌上的香薰蠟燭,放緩語速,「我的生命就像這隻蠟燭。我知道它會燃盡,甚至燃盡前每一刻的樣子,我都可以想像。問題在於,一個人知道死亡的形狀後,應當如何度過剩下的一生?」
這個鎮靜地談論死亡的女孩,是如何做到消解命運的殘酷,如何做到傷感但不悲怨?在之後的交談中,我找到了答案。那些經歷過的冷眼和歧視,淬鍊出了一顆更柔軟的心。
陳晨坦言,患病前,她對弱勢群體缺乏真正的同情。現在不一樣。比如,她走路時會格外留意觀察盲道,如果注意到盲道設計有問題,是斷頭路,或是發現盲道被占用,她馬上就會打12345反映。
「只有變成了弱勢群體,才能真正理解其他的弱勢群體。大家都是當前社會結構下的弱者。」陳晨說。
只是,探出頭關照世界的時刻如彗星划過夜空,更多的時候,她不得不埋頭處理自己生活中的苦痛和掙扎。
那日臨近分別時,我們一同走進地鐵,表情淡漠的面孔從我們身邊魚貫滑過。
「有時候覺得,我的生活像一潭死水。」陳晨的聲音很低。
她隨即自嘲,「你說我前兩年怎麼沒想過這種問題呢,只想著怎麼活下去了。還是太閒了,日子過得太好了。」
沉默間,兩列地鐵幾乎同時來到。我們走向反方向,她對我揮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