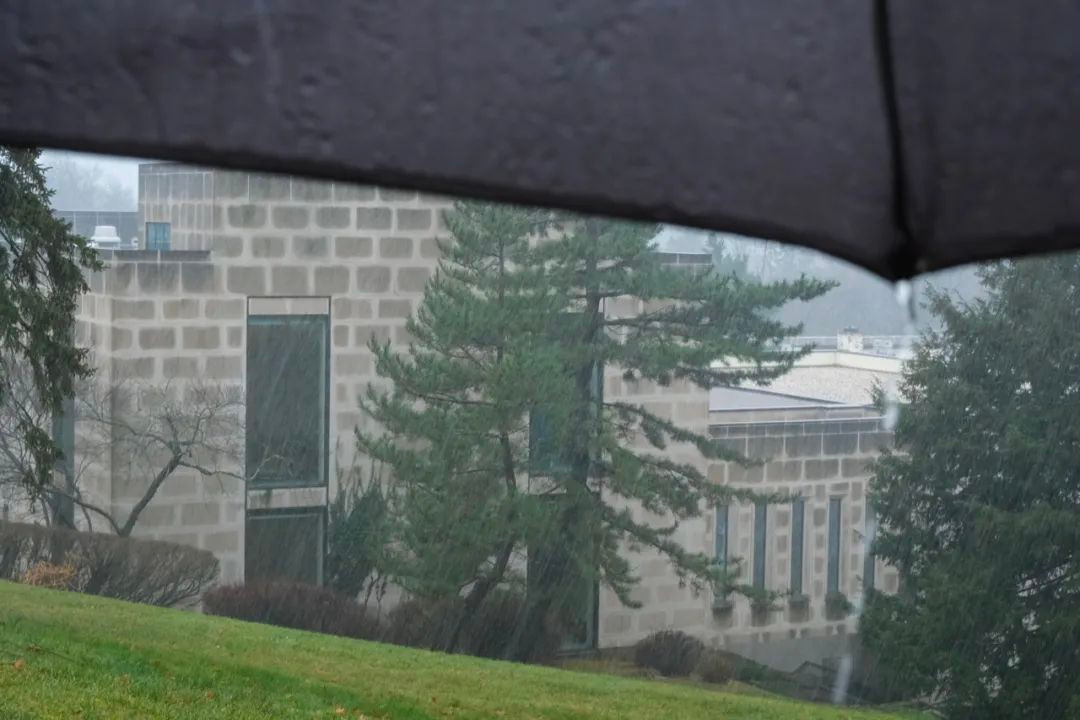
高醫生的告別儀式在紐約市北邊的芬克里夫墓園舉行。列車從曼哈頓42街的中央火車站出發,即將到達135街的時候,突然右拐,過橋離開曼哈頓,繼續一路向北。厚厚的雲霧裡,我隱約看到了135街西側那棟醫生生前居住的大樓。
春天的時候,我和一群哥大學生到那兒看望過她。那是個溫暖的春日,飛鳥在哈德遜河上翔徉,路邊的大樹長出嫩葉。拜訪時,我擷著一束向日葵過去。但到她公寓不久後,照顧她的看護阿姨對著我手中的向日葵嘆了口氣——她說,醫生不喜歡鮮切花,只喜歡盆栽花,鮮切花容易枯萎,沒有能夠紮根的土壤,也無法長久生長,徒留浪費。
果然,病床上的醫生後來也向我說起了這點,「這種花,不好。」我只有汗顏。
那時,她還在從年初一場昏迷8天的大病中恢復,每天都要做霧化,吃很多藥,聽和說都變得很困難。我們用紙筆寫字交流,聊起我曾經工作的報社,也零星談起她過去做過的不平凡的事。某個時刻,我突然心生好奇,寫字問她,「您覺得什麼工作是好的工作呢?」
我設想她會說有影響有意義云云,但她卻只寫下6個字,「安定、工資穩定。」
她把本子遞給我,盯著我看,好奇我如何看待她的回答。我笑了一下,沒有細想,也沒再往這個話題深入。但那天結束拜訪後,我反覆琢磨這一問一答,才意識到,醫生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只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已。誰不渴望安定平穩的生活呢?她不厭其煩、不懼其難地去講述那些愛滋村的故事,只是一個普通人做了遵從本心的事,一個普通人擁有了不普通的勇氣。那天她和我們說,這幾年她筆耕不輟地寫書和文章,是為了讓歷史被記住。
今天是個陰沉的雨天。為了避免紐約難以預測的交通,我提前到達墓園。四下無人,只有滿園風雨。雨水打進傘沿,墓園草坪上的小草在風裡飄來盪去,有坡度的地面上已經匯成無數小溪。天色灰濛,看不到一絲雲、一點藍。
墓園很大,坐計程車前來的人們往往會在墓園門口下車。但事實上,舉行告別儀式的小教堂離那兒還有一段距離。需要上一個小山坡,走過好幾塊墓地,下坡,再走一段平坦的路,才會來到那棟灰色的小教堂前。暴雨完全浸濕了我的褲子和鞋子,涼意刺骨。
到了12點,教堂門口停泊的車才逐漸多起來。大家眼神交匯,互相問一句,「你是來參加—–?」後面幾個字並不用說出,對方就迅速點起了頭,確認了眼神。
一位朋友來得比我晚些。她比我幸運—-她也是在墓園門口下車後才得知教堂還要走十多分鐘。這時一輛小車經過,司機搖下車窗,問她是否去參加醫生的葬禮,她點點頭,司機就招呼她上車。車沒開多久,路邊又有兩人撐著傘在風雨里走,傘被大風都吹斜了,司機又搖下車窗問,「你們是去參加高醫生的葬禮嗎?」對方說是啊,司機又招呼他們上車。於是,原本一輛空車坐滿了人。坐在朋友身旁的先生下車後還幫沒帶傘的她撐起了傘。
還有一位律師,從法拉盛過來,他在90年代就聽說過高耀潔做的事。在從墓園門口開到小教堂的坡道上,他看到一位雨中走路的女士,便邀請她坐上了自己的車。那位女士說自己不認識高醫生,從倫敦趕來,坐了七小時的飛機,時差都還沒倒過來。
這些來訪者自發的互助與關懷,和我想像的關於醫生的告別儀式有些不一樣。告別儀式的地標並不明顯,好多人走錯了位置。我以為,這裡至少會有一塊比較顯眼的牌子,印著醫生的名字,提醒我們舉辦的地點。我以為,就像中國傳統的喪葬儀式,會有許多醫生的親人在門口等候、接待。我以為一切會更有序、更隆重。但事實上,一切更像是野草般的,自發,生動,狂風暴雨中,陌生人在巨大的陵園裡走失,又接到陌生人善意的幫助。滿園風雨里,大家為同一件事而來——告別一名醫生,紀念一名醫生,一名有勇氣的、為阻止愛滋泛濫而不斷講述真實的醫生。我問了好些人,「你見過高醫生嗎?」大多數人都沒有見過醫生,只是聽聞過醫生的故事便慕名而來。

有位穿白色羽絨外套的女士,用驚喜的神色和等候的賓客介紹著一件神奇的事。她說,自己一位朋友的母親,在80年代的時候因為癌症接受過醫生的治療,一年後癌症被治好了,朋友的母親現在都還活著,朋友希望她過來表達感謝。醫生因為揭露愛滋病的泛濫而聞名,但她行醫的故事卻鮮為人知。在她人生的最後幾年,她出版了一本關於行醫往事的書,只因為她覺得,自己是個好醫生,救了很多人的命,但大家只關注防艾的部分。
在教堂門口,我聽到有人嘟囔,覺得儀式組織得不是那麼好,「門口都沒有人迎賓和指路。」於是,一位穿著黑衣黑裙的女士爽利地說了一句,那我們就代家人來迎接,人家可能在忙呢。後來,她就堅持站在教堂的金色大門口,迎接著一波又一波的客人,「謝謝」「你好」「對,就是這裡」,她自發地成為了醫生家庭的一員,負責指引,而事實上,她從未見過醫生本人。
下午一點,告別儀式準時開始了。前兩排坐著她的家人,大女兒,女婿,妹妹,孫女,還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黎教授,也是醫生的監護人。
從高醫生來到紐約的第一年開始,黎教授就幫助她處理在美國的具體事物,代她和政府、醫療保險公司做事無巨細的溝通。成為醫生房屋租賃的擔保——在紐約租房都需要擔保人。甚至包括一些更細小的事,比如帶著醫生在紐約街頭買一塊麵包。還有一次,上午9點,醫生生病住進急診室,教授10點就趕至醫院,陪伴很久,中飯都沒顧上吃。
這位陪伴了醫生十多年的教授,在告別儀式上說,在這些年裡,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國老百姓對高醫生的尊重和關心。留學生們幫醫生錄入書籍的文字,電腦壞了則幫她修,媒體人幫她編輯書稿。總有留學生想過來看他,總有中國人給她寫信,給她送禮物。他說,醫生獨自一人待在公寓,身體不舒服,語言不通,難免孤獨,這些中國人的陪伴和到訪給了她許多精神上的鼓舞。
教授是美國人,但用不算完美、帶有口音的中文完成了整段講話,一字一頓。現場很安靜,大家好像是在努力聽一段跨越國別、文化和語言的情誼。
杜聰先生和醫生相識於23年前。他經常和醫生一起,開著一部她常用的車,去些鮮為人知的愛滋村調研。那段經歷讓他看到了許多關於愛滋病的故事,促使他開啟了幫助愛滋遺孤的公益事業。在告別儀式上,杜聰說,醫生是一個有風骨的一個人物,不卑不亢,對身邊的人都非常關心,有愛心,「因為她,有很多的孩子有了長大的機會,也因為他,有很多的孩子可以讀書。二十幾年後的今天,這些孤兒有很多也結婚生孩子。她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
醫生兩鬢已蒼白的妹妹,也分享了記憶中的兩件事。
第一個故事,關於姐姐帶她看飛機。1945年夏的一天,全家聽說開封要打仗了,都躲在門洞裡。隨著飛機的聲音越來越近,醫生突然對妹妹說,「走,我帶你看飛機去。」她們一路跑到院子裡的荷花池旁。父親在身後大叫:「一個炸彈把這兩個都炸死了。」我推測醫生的妹妹講述這個故事的用意——她或許想說,她的姐姐一直是個勇氣超凡的人,就像她此後漫漫一生里所表現的那樣。
另一個故事,關於她離開故鄉前,妹妹告訴她,除了最必要的東西,其他什麼都不要帶。她說,我最重要的東西都在計算機里。這個回答嚇傻了妹妹,「我那一年69歲,叫我背一個桌機也是很困難的。」妹妹用一個小鑰匙,取出了計算機的硬碟,交給了醫生。這些資料包括了她曾經做的那些關於愛滋病的調查,對醫生來說,這是她畢生心血,是最重要的事。
最後一位在告別儀式上講話的,是醫生的女兒。受到母親的影響,她也成為了一位婦產科的醫生。她感謝了很多人。包括那位作為她監護人的教授。包括杜聰。包括那些照顧母親、為母親做可口飯菜、管理吸氧機的「看護姐妹」。包括那些來看望醫生,幫醫生發送郵件、錄入書稿的無數留學生。還有一位無名者,幫醫生支付著美國公寓的房租,但一家人至今不知道ta的姓名和身份。
溫柔的奇異恩典在告別室里響起,隨後,人們依次瞻仰醫生的遺容。經過靈柩旁,我看到了雙眼緊閉的醫生,穿著一件咖啡色的壽衣,打了粉,塗著口紅,好像在睡夢裡安眠,頭頂放著幾本她寫的書。告別室里時不時響起人們的哭泣聲。
廳堂里已擠滿了人,前來告別的人群已經蔓延到廳外的過道。準備離開時,我在門口遇到了一位西裝筆挺、匆匆趕來的年輕人。他問我,「這裡是醫生的告別儀式嗎?」我說是的,但是已經快結束了。他流露一臉遺憾。「我提前了一段時間出來,沒想到紐約地鐵在半路突然停了,這事經常發生嗎?」他不可置信地說,自己從芝加哥飛到紐約,只是為了參加這個告別式,沒想到還是沒能趕上。我安慰他,現在人們正在排隊瞻仰遺容,你還能趕上見醫生最後一面。
我從教堂出來時,太陽出來了,照亮了墓園的小山坡,照亮了一塊塊和地面平齊的灰色墓碑,照亮了剛剛完成告別儀式的那個灰色小教堂。人們在紐約冬天的風雨里完成一場告別,然後,草木上的露珠反射出光彩,灰色的事物也有了光澤。

為醫生舉行告別儀式的墓園成立於1902年,埋葬了很多在時代中留下鮮明註腳的人。
比如顧維鈞,那位在巴黎和會中說出「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的外交官,為國家爭取了平等和尊重。比如美國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他用銳利的文字揭露種族歧視以及與之搏鬥,尋找不同群體都能理解的語言,傳遞自己的聲音,積極參與到民權運動中。比如瑪麗·里特·彼爾德,一位婦女選舉權活動家和婦女歷史檔案管理員,她的努力鼓勵幾所學院和大學開始收集有關女性歷史的記錄。
在告別儀式開始前,人們坐在一個小小的祈禱室里休息和等待。一位女士說,她為了說出真相,家都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這樣的人真的是超越世俗的人。
旁人附和,是啊,普通人誰能做到和她一樣呢?
這時,一位蓄滿鬍子的男士突然說,「她是從外太空穿越過來的人,是穿越過來的人啊。」
房間裡沉默了一會兒,有人反覆咂摸「穿越」這個詞,溫暖地笑了,「是啊,說得真好」。
「其實她才是真真正正的人。說實話,做實事。」一位女士堅定有力地說,目光中有些傷感,又有些氣憤。她把神化的敘述突然往回拉了拉,仿佛在說高醫生其實只是一個普通人應該有的樣子。
這段對話一直在我腦海里迴響。一個普通人要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呢?以及,另一個和今日的天氣一樣沉重的問題,度過有意義的一生又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回程的路上,火車經過布朗克斯河,渾濁的河水裡盡躺著枯木。我想起高醫生送我們的一本她的詩集,扉頁上寫著陶淵明的一首詩,「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也想起了她那些獨居公寓、無比思鄉的孤獨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