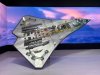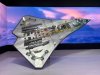抄襲者汪暉的前世今生
汪暉的抄襲,仔細讀完王彬彬的批評文章,加上對於王彬彬提到的若干文獻的仔細閱讀比對,可以看出抄襲一事立論有據,完全成立。許多人以此為依據,像王彬彬一樣指責汪暉的學風不正,固然是巴老所提倡的「說真話」,這當然是無可厚非。但是以此來透視汪暉進入學術界這若干年的思想脈絡、學術道路,或許更為有趣。筆者不才,喜好鉤沉索引,不妨就數年來所閱讀之關於汪暉之文獻,對其在學術道路上「漸入頹唐」,乃至最後「東窗事發」,作一番粗線條的勾勒,以待方家指正。
一、揚州師院生涯與汪暉的早年
一九七七年,正是改革開放呼之欲出的年代,這一年鄧小平以極大的勇氣,停止了毛選第五卷的印刷,改印高考試卷,由此開始了恢復高考的歷程。鄧小平這一舉措,無疑石破天驚,而他所力倡的恢復高考開始時期的那七七七八兩屆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社會的風雲人物,汪暉亦廁身其中,只是其面貌後來越發可疑。
汪暉考入揚州師院時正是一九七七年,其母親是揚州師院的教師,那一年汪暉十八歲。揚州師院現名揚州大學,其前身乃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實業家張謇創立的南通高等師範學院。著名學者王國維、姜亮夫都曾在這所學校任教過。校內有諸多在學界赫赫有名的學者,但是在文革時期,揚州師院如同諸多高校一樣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但是揚州師院依然群星璀璨,諸如古典文學大師任中敏、李坦、孫龍父、譚佛雛。現代文學有著名學者曾華鵬、吳周文、李關元。汪暉在這樣的條件下入學讀書,理應做出一番成績。
有人曾評價汪暉這一代學者乃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成長起來的,雖有道理,但是過分強調了時代潮流之於人物的影響。揚州雖然交通便利,但那是古代的事情,憑藉和運河相依而已。近代以來,揚州城日益閉塞,要說本科期間汪暉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無疑是牽強之論。另外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於,汪暉當時所傾心的,更多是魯迅研究和古典文學,他在揚州師院讀碩士研究生時期的導師,就是著名古典文學研究者章石承先生。章先生雖然在詞學方面造詣精湛,但是在魯迅研究方面也有許多成果。汪暉受到章先生的影響,是再明白不過的事實。但是沒想到若干年之後,汪暉居然因為研究魯迅的論文被指責抄襲,真是貽笑大方。
此處我要對汪暉在揚州師院的幾位導師做一番簡要的介紹,諸如章石承先生、曾華鵬先生。章先生的老師是著名詞學大師龍榆生先生,章先生秉承了乃師治學嚴謹的作風,而且為人極其古道熱腸,對龍榆生先生一直恪守師生禮數,不管世道艱難若何。曾華鵬先生是五十年代復旦大學畢業,他和他的同輩學長章培恆先生、范伯群先生,都是賈植芳先生的高足。其在魯迅研究和王魯彥研究上的造詣,引人矚目。其為人治學之樸實嚴謹,自不必言。賈植芳先生曾因胡風案入獄,一生坎坷,其晚年學生張業松先生如此評價賈先生:他(賈植芳)活在魯迅的脈絡上。汪暉後來從事魯迅研究,和章石承先生、曾華鵬先生的影響,密不可分。但是最後上演了抄襲這一出,真是讓人啼笑皆非。而李關元先生和章石承先生曾華鵬先生一樣,都是淡漠的學者,雖然聲名不顯,但是其治學在學界已經留下了影響。他們曾經聯合培養了諸多如今在現代文學研究界頗有名氣的學者,諸如徐德明、葛紅兵等。汪暉有如此諸多學風嚴謹的老師,到最後卻因為學風不正被人釘在抄襲的恥辱柱上,端的是有辱師門。
汪暉在九十年代的《讀書》上發表有《明暗之間》一文,記載了他與章石承先生的一段過往。一九八三年汪暉北上訪學,章先生在他臨行前聲稱有事情要交代。汪暉應約來到章先生的家裡。章先生告知汪暉先去找在鎮江的蔣逸雪先生,請他寫信給時任魯迅博物館館長的王士菁。蔣先生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師,而且資助過王先生讀書,汪暉可以通過王先生的關係查閱存放於魯迅博物館的魯迅藏書。於此之外,章先生還私下裡叮囑汪暉,有一事相托,但是千萬不要對人說起。章先生說請他去龍榆生先生的墓上祭拜,代他鞠躬致敬。後來汪暉回憶:這私事說來簡單,後來我才覺得不尋常。
龍榆生,一個多麼對於當代人來說非常陌生的名字,然而對於如今的老一輩人來說,再為熟悉不過。他是二十年代最富盛名的詞學大師,其詞學成就可與唐圭璋、夏承燾並稱。龍榆生是章石承在暨南大學讀書時的老師,私交極為密切。抗戰時期,龍榆生先生不幸落水,章先生痛心疾首,卻也無可奈何。或許正是這一政治上的歧途,導致龍榆生在學術史上幾乎被遺忘。汪暉遵囑找到了龍榆生的女公子龍順宜,龍順宜與汪暉一起去龍先生的墳上祭拜。兩人來到北京萬安公墓,找到了龍先生的墓碑。龍順宜忽然問汪暉:你們這一代人,如何看待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名動天下,但是抗戰時期選擇了與龍榆生先生一樣捨身伺虎,終致身敗名裂。汪暉那時二十三歲,按照當時流行的至今尚未翻案的「漢奸說」回答龍順宜,龍順宜長嘆一聲:老一輩的人死完了,年輕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後來汪暉憶及此事,只是覺得傷了老人的心,是不該的,但是沒有苛責前人的內疚。同樣的道理,汪暉評價龍榆生先生,也是同樣苛刻:他雖然拒絕出賣文物,但是這點個人的清白,掩不住大節有污。在那樣的歷史語境下,不可能成為獲得理解的理由。
這樣一段過往,對於透視汪暉的學術脈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儘管汪暉師從諸多名師,但是在對於文學以及文學歷史人物的理解上,顯得極為陌生。不管是周作人,亦或是龍榆生,他們的歷史抉擇,都有那個動盪年代的逼不得已,而汪暉對於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具體到內心的真切理解。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汪暉的《反抗絕望》之於魯迅的內心洞察,幾乎是寥寥無幾。這樣的著作被冠之以魯迅研究的里程碑,真令人感到遺憾。更何況還有抄襲的內容,讓人始料不及。或許正是從此開始,汪暉與他的師承輩在學術選擇上漸行漸遠,最終走火入魔。
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從文學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
一九八四年汪暉考入中國社科院,追隨唐弢先生攻讀文學史。當時社科院只有二十多個研究生,編在一個班上,汪暉擔任學習委員。當時的社科院教師群星璀璨:于光遠、李澤厚、蘇紹智、馬洪、賀麟、任繼愈、彭澤益。而這個班上的諸多學生,後來都成為中國學界的風雲人物:郭樹清、樊綱、左大培、王逸舟、黃速建、韓水法,汪暉於其中,顯得極為另類。
這一另類的原因在於,這個班上的許多學生選擇了經濟學,選擇文學哲學的為少。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聚在一起討論類似於「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大問題。經濟、政治改革是當時他們每天討論的話題。後來汪暉在九十年代以文學史研究者介入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有其在社科院的從學經歷有關。同時也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學風在汪暉身上的直觀反映。八十年代的學術氛圍,雖然激情高漲,但是學風比較粗疏,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汪暉抄襲的理由。九十年代中期,汪暉在《天涯》雜誌上發表《當代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表明了他已經徹底告別文學批評,轉向社會思想史的研究。但是這一轉型,讓汪暉成為了眾人眼中新左派的領軍人物。尤其是他主管《讀書》雜誌之後刊登美國學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更讓人對其新左派的立場深信不疑。而他對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徐友漁、朱學勤、雷頤等人的攻擊,更加顯示出他立場的左傾。
汪暉的學術轉向,原因諸多,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其學風的浮躁所致,在汪暉的師輩中,無論是章石承還是唐弢,生前都是嚴謹治學從不逾矩的本份學者,章石承著有《李清照年譜》、《陸游詩選》,功底紮實。而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早已成為學術界的經典之作。但汪暉的學術道路雖然在初期尚能在師傅輩的指引下循規蹈矩,尚能沉潛,其寫下《反抗絕望》,雖然有抄襲之處,但按照嚴家炎先生的說法,主體思想還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在九十年代以後逐漸寫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已經全然讓人不知所云。
汪暉從文學史研究轉向思想史研究,進而走火入魔,從小處看是學風不正,從大處看乃是八十年代空泛的學術風氣在九十年代的惡性循環。李澤厚曾言九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相比乃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此言概括雖然粗疏,卻也八九不離十。八十年代許多名噪一時的新理論新方法,如今看起來都是非常可笑,立論不穩。諸如社會上流行的「三論」,金觀濤夫婦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性結構等等,雖然看似有理,卻缺乏明確的學理支撐。整個八十年代真正紮實的學術研究,極為稀少。這種情況到了經歷過歷史大變局的九十年代,才有所改觀。
汪暉學術轉向的另一原因,乃是其主編《讀書》和《學人》的重要契機。在汪暉主編讀書之前,《讀書》整體是偏向人文趣味,汪暉接掌《讀書》之後,其辦刊思路乃至方針逐漸向社會科學領域轉移,但汪暉自己的學術立場,讓他開始在選稿中立場偏向極其嚴重。諸如在他接掌圖書三年之後,即二零零零年,讀書刊登了美國學者高默波美化文革的文章,引起了知識界的軒然大波。
與汪暉一樣從文學史研究轉向思想史研究的陳平原,卻沒有像汪暉那樣走火入魔,誤入歧途。雖然陳平原和汪暉一起主編《學人》叢刊,在九十年代引起了極大關注。陳平原做學問與汪暉相比,更為紮實和按部就班,絲毫沒有汪暉大躍進式的學術轉向,剛寫完文學史研究的著作,轉身寫出了四卷本嚇死人的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陳平原的另一長處,就是始終堅守學術本位,幾乎沒有參加過任何學術界的所謂左右之爭,遠離了諸多俗世紛擾。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汪暉在《學人》十年之後寫下的紀念文章中,對於《學人》走來的這「小小十年」,語氣不勝感慨。
翻開汪暉號稱代表作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雜亂無章。第一部上下卷的標題為「理與物」、「公理與反公理」,第二部上下卷的標題為 「帝國與國家」、「科學話語共同體」,其體系之混亂,思維之跳躍,讓人瞠目結舌。我仔細讀完這四卷本,仿佛吃了一頓怪異的雜燴湯,說不清楚什麼味道。只見到鋪天蓋地的學術術語和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西方學者怪異的名字。這樣的所謂思想史,嚴重混淆了思想史的界限,就筆者所涉獵而言,葛兆光、韋政通兩位學人的《中國思想史》,就比汪暉來得高明的多。而且這兩位先生的思想史,篇幅雖然不及汪暉,但是卻沒有汪暉那樣嚇死人的排場,以及所謂宏觀敘事的巨型架構。
汪暉這種思想史的寫法,說到底就是唬人。這種拿外國人嚇唬中國人的本事,五四以來,源遠流長。但是即便是五四時期的全盤西化論者,也不敢像汪暉這樣肆意誇大自己的國際學術影響。即便是胡適這樣師出名門,也只是謹慎為人為文,安守本分罷了。汪暉與五四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同在於,五四時期諸如胡適這樣的西化派,乃是以西方的思維方式方法,來觀照自己所研究的東方文化。而汪暉則是將西方理論生吞活剝,如同貼標籤一樣將西方的理論與術語貼在中國文化的研究上,因此其在《反抗絕望》中以克爾凱郭爾比附魯迅,尚有他早年閱讀魯迅的心得體會與其閱讀西方著作的心有相契,及至他寫下《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已經全然演變成一種毫無精神共鳴的學術生產。公理與名教、教育改制與心性之學,這些中西混合的怪胎,成了汪暉走火入魔的絕佳憑證。
三、從長江《讀書》獎風波到抄襲事件
二零零零年,由《讀書》雜誌承辦的長江讀書獎,由於汪暉的獲獎引起了巨大爭議。本來汪暉獲獎並不能引起太多的關注,頂多是人們在認可程度上有所分歧。事實在於,汪暉獲獎的同時還擔任著這個獎項的評委,這就讓人貽笑大方。而獲獎人之一錢理群先生也和汪暉一樣犯了同樣的錯誤。汪暉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錢理群先生是著名的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但是這一次兩人同時受到指責。在《讀書》獎風波之後,汪暉最終被拿掉了《讀書》主編,錢理群先生還發表了一些很不負責任的言論,為汪暉辯護,具體情況可參閱蕭夏林文章《兩個錢理群》。
時隔十年,汪暉抄襲案事起,錢理群先生又犯了天真的毛病,又一次為汪暉辯護。錢先生本來可以保持沉默的,因為汪暉抄襲的論文答辯委員會各位委員幾乎都是錢理群的老師輩,諸如嚴家炎先生。利害相關,總要避嫌才好,但是錢先生又一次犯了低級錯誤。王彬彬聽聞了錢理群先生的表態後大為失態,破口大罵錢理群先生無恥,並要求記者原文刊登。可能錢先生也不想再趟這趟渾水了,對王彬彬的咒罵表示寬容之後,也閉口不談。錢先生的胸襟,當然是值得敬佩的。但是屢次犯錯,則讓人遺憾。
從二零零零年的長江《讀書》獎風波到二零一零年的抄襲案,汪暉始終處在風口浪尖,但最後總是四平八穩。除了民間社會的質疑,以及知識分子的批評,鮮見體制內或是汪暉的單位對於汪暉公正的處理。截止到目前,清華大學網站上依然掛著《嚴謹治學的學者汪暉》這樣的文章,汪暉的教授照當,國務院津貼照拿,沒人來管。仿佛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事實上這些事情,都昭顯了汪暉之於公理、常識的冷漠和忽略。長江讀書獎風波中,汪暉表示他只是召集人,並沒有參加評獎,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抄襲事件中,汪暉又說希望學術界自己去澄清。這兩起事件發生的時候,汪暉都聲稱自己在美國,真是無處不巧合。這些言論歸根到底,汪暉在為自己開脫,迴避實質問題。
而我們細細來考察這兩件事情,前一次汪暉的身份是《讀書》主編,他這一明顯違反學術規則的行為,讓《讀書》蒙羞。而後一次抄襲案中,汪暉的主要身份是清華大學教授,同時還是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抄襲一事,讓清華丟臉,也讓「哈佛大學訪問學者」這一頭銜的公信力引起人們的懷疑。有人以這兩起事件為例,將其看做知識界在九十年代末左右之爭的延續。坦白而言,這種概括並不確切。長江《讀書》獎風波的實質,乃是學術界對於學術腐敗學術公正性的討論,少有涉及到具體的學術觀點。而抄襲事件,則牽涉到學術造假等嚴肅的問題。不能因為在這兩次事件中批評汪暉的徐友漁、王彬彬諸君是自由主義派的知識分子,就將他們對汪暉的批評看做左右之爭,而有人將王彬彬批評汪暉看做南京大學對清華大學的挑戰,則更是無稽之談。
坦白而言,就汪暉的學術能力而言,並不差勁,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女士一再強調這一點,但世道輪迴,旦夕不測,當年以《反抗絕望》暴得大名的汪暉,會在多年之後被王彬彬揭開抄襲的老底。本文的意旨,也在於提出自己的質疑,看一看汪暉如何從一介本分的淮揚書生,一步步被塑造成為一個學術神話,以及最終這個神話如今已經破裂。我想通過此文,刮去汪暉身上厚重的油彩,還其一個乾淨自由身。不管這種工作會不會遭人記恨,我都覺得很有意義。
責任編輯: 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0/0717/172677.html
相關新聞













 中國美院教師抄襲海外畫作曝光 民諷:這不是抄襲 是複印(圖)
中國美院教師抄襲海外畫作曝光 民諷:這不是抄襲 是複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