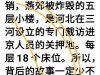一個政權是否真「為人民」,從它對民眾、特別是對「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無助待援的弱勢群體——訪民的態度上,最清楚不過地表現了出來。明朝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從最初的支持民眾反腐、懲辦截訪者,墮落到後來的保護貪官、鎮壓上訪者,一方面表現了其政權性質從「為人民」到「反人民」的轉化,另一方面又是其政權興衰變化的表徵。從這個角度看明史,總是令人不勝感慨唏噓。
重獎進京「群體上訪」的民眾
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寒,在社會上曾經倍受凌辱,對官吏的欺壓民眾具有切膚之恨。即位之後,堅決發動和依靠民眾,打擊貪官污吏。他說:「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克為務,此民之蠹也。」⑴不搞掉這些「民之蠹」,民眾繼續處於受迫害、受壓迫的地位,一場革命絕對就是白革了,還談什麼「為民」?
朱元璋的目標,是要創建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裡,「三光平,寒署時,五穀熟,人民育」,「天下無金革鬥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②,「田野辟,戶口增」③,「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④,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無官逼之憂,無盜厄之苦」。⑤
欲達此目的,搞掉官員隊伍中的「民之蠹」,是應有之義。
怎樣才能搞掉「民之蠹」呢?依靠群眾。
元末,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獨獨朱元璋取得了勝利。秘密就在於唯有他的部隊,最重群眾紀律,「擅入民居者死」⑥,「卒取民七茄,立斬」⑦,是當時唯一一支不擾民、得到群眾熱烈擁護的革命隊伍。既然靠群眾能夠打敗群雄、奪取政權,清除「民之蠹」、鞏固政權,當然也就只能依靠群眾了。大明除了制訂「重繩贓吏」⑧的法律,建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司法監察機構,以執行法律外,放手發動群眾,揭發檢舉貪官污吏,就成了不二的選擇。朱元璋說:「民間若不親發露其奸頑」,「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⑨
皇帝高高在上,當然「一時難知」誰是贓官,但是官員們生活在民眾中,他們的行事,民眾卻最了解。在朱元璋看來,民眾揭發贓官,不僅不是對大明政權「抹黑」,反而是對皇帝的幫助。——朱元璋是無所畏懼的。他堅信他的政權,心態健康,屁股乾淨,絕不「前怕龍後怕虎」。
明初,依靠群眾揭發贓官,最厲害的一手,是:一竿子插到底,激勵基層民眾,群起直接揪送那些破壞法治、刁難、殘害民眾的貪官污吏,交由政府法辦。
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朱元璋頒布《大誥》,幾十次地反覆動員,號召:「自布政司(相當省政府)至於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材,許境內諸耆宿人等、遍處鄉村市井,連名赴京狀奏」,「以憑議罪」。⑩「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閒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滑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良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幫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⑾舉凡「不務公而務私,在外髒貪,酷虐吾民」,「巧立名色,害民取材」,「欲取民財,實難言語,故行刁蹬」,「不將正犯解官,而拿解同姓名者」,「賄賂出入,致令冤者不申,枉者不理」,「起滅詞訟,教唆陷人」,諸如此類,上至布政使(省長),下到離職小吏,俱在揪送之列。
大明相信人民,毫無顧慮地,放手發動民眾,不惟不怕「群體鬧事」,反而提倡民眾「會議」、「共議」、「連名」,集體行動,「或千或百或十」⑿,「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成群結隊,浩浩蕩蕩,扭送貪官污吏進京面奏,交給朝廷懲辦。⒀
扭送贓官進京的「上訪」群眾,特重要者,由皇帝親自接見、處理。⒁只要是訪民,不僅不遭驅趕,不受懲罰,不記黑帳,不受監視,朝廷反而分別情況,給予獎賞。例如,官吏貪贓枉法,接受逃兵財物,不送交軍隊,反捉拿同名同姓良民交軍充數者,「豪傑之士、耆宿老人會議捉拿赴京,見一名賞鈔五錠。」⒂;衙門官吏、弓兵、皂隸、祇禁,「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者」,「所在鄉村吾良民豪傑者、高年者,共議擒此之徒,赴京受賞。若擒的當人一名,幹辦人一名,管幹人一名,見一名賞鈔二十錠。」⒃奸頑豪富之家勾結官府,將自家田地分寫小民名下,將賦稅轉嫁給小民,由「所在被害人戶及鄉間鯁直豪傑會議捉拿赴京」者,「將前項田土給賞被擾群民。」⒄積年「生事科擾」,「酷害於民」,「以是作非,以非作是,出入人罪,冤枉下民」的貪官污吏,或被充軍,或罰作苦工,服刑未滿,私自逃回,檢舉揭發屬實,「以本家產業給賞其首者。」⒅
常熟縣陳壽六為縣吏顧英所害,非止害他一人,且害民甚眾。陳壽六率弟與甥三人擒拿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朱元璋嘉其能,賞鈔二十錠、三人衣各二件。同時,敕都察院榜諭市村;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陳壽六者,族誅。⒆
政府發動和依靠民眾打擊貪腐勢力,態度何等堅決,氣派何等宏大!非徹底的革命家,不能有此大手筆。
許許多多截訪官員被梟首示眾
大明規定:「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⒇「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務者,雖無文引(即沒有隨身攜帶「介紹信」、「身份證」之類),同行人眾,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於三五百名,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問知面奏,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罪。」(21)所謂「邀截實封」,即中途阻撓向朝廷密封遞送「情況反映」、割斷上下聯繫、使皇帝孤立起來,那是要治罪的。阻擋群體集體進京「上訪」,與邀截向皇帝送交「告狀信件」者同罪。那麼,怎麼處罰呢?「敢有邀截阻擋者,梟。」(22)所謂「梟」,就是砍下頭顱,將首級懸掛城頭示眾。十分了得!
為攔截「上訪」民眾進京,而被「梟」的大小官員不少:
嘉定縣民郭玄二等二人,手執朱元璋頒發的《大誥》赴京,首告本縣首領弓兵楊鳳春等害民。經過淳化鎮,其巡檢(公安派出所所長)何添觀刁蹬留難,致使弓兵馬德旺索要鈔貫,馬還威脅說:如不行賄,則差人將他們送京懲處。事發,馬德旺依《大誥》規定行誅,梟令示眾;何添觀鑰足枷令。(23)
松江府知府(專員)李子安貪贓枉法,問題嚴重,擔心被人進京告發,為「防患未然」,竟將旗軍傅龍保等十二名收監。又三人走脫,欲行赴京告狀,被李子安「邀截回還,鎖禁五十餘日」。事發,凌遲示眾。(24)
開州同知(專區副專員)郭惟一貪贓害民,耆宿董思文等赴京陳告。郭惟一竟率領祇禁人等,將其邀截回州,收監在禁,監死董思文一家四口。其侄董大赴京告發。郭惟一梟令示眾。(25)
溧水縣主簿(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范允受賄,包庇罪犯。民人霍進等到縣告發,有關罪犯以鈔四百貫、紅綾二匹再次行賄,范允即又「泯滅其事」。霍進等赴京陳告,范允令人途中邀截回還。事發,梟令任所。(26)
吳江知縣(縣長)張翥、縣丞(副縣長)周從善,吳縣主簿(縣政府辦公室主任)閻文、曹縣知縣(縣長)杜用等,都曾因阻擋耆宿扭送贓官赴京等罪而被判處死刑,杜用處斬,其餘三人戴死罪暫留原職工作,以觀後效。(27)
北平貪官將贓物分存各處,其中向開州官吏羅從禮等存放17,000貫。開州州判(從七品)劉汝霖不按名追贓,卻下帖鄉村,遍處科民代賠,還給人戴大帽子:如不交納,就是不支持朝廷追贓,甚至禁錮農民,逼令納鈔。開州耆民,不忍坐視民患,赴京面奏者五人。朱元璋遣人查實,將劉汝霖梟令於市。(28)
丹徒縣丞(副縣長)李榮中等六人受賄575貫,將應當服役的1,265人免役,而將應免夫役的鋪兵、弓兵、生員、軍戶周善等數百家,一概遍鄉勾拿動擾,意在搪塞,於內又復受財作弊。被擾之家至京揭發,情況查明,梟首示眾。(29)
軍隊幹部犯此罪者,同樣嚴懲不貸。青州護衛千戶(正五品)孫旺,逼令軍人自縊身死。其餘軍人赴京申訴,他差人邀截回去,將各軍人監在牢裡,誣賴他們勾結壞人作亂,凌遲處死四人,其餘盡發雲南。事發,孫旺凌遲處死。(30)
兗州護衛指揮(正三品)蔡祥、千戶(正五品)毛和、鎮撫(六品)梁時、顧信等,百般苦軍,軍人糟法保赴京告狀,行至鳳陽浮橋,他差人趕回去,妄啟魯王,將軍人打死分屍。事發,千戶毛和等,自知罪重,脫監潛逃,指揮蔡祥凌遲處死。(30)
處州衛指揮(正三品)顧興、魏辰、屠海、雷震、盛文質、夏庸等,有軍人陸達之赴京,告張知府收糧作弊,他們與有司交結,差人趕回監問。事發,發荒僻之地金齒充軍。(30)
……
扭送貪官污吏,怒潮興起,壞人聞風喪膽。樂亭縣主簿(縣府辦公室主任)汪鐸等設計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難的,每一丁只要出絹五匹給他們,即可出脫。高年有德耆民趙罕辰等三十四人將他們綁縛赴京。行間,有的當人、說事人、管事人何濬等十人翻然悔悟,痛改前非,一同幫助,將工房吏張進等八名綁縛起行,去縣四十里。汪鐸哀求:「我十四歲讀書,好不容易才到今天。你們千萬原諒我這一次,不要壞了我的前程。」(31)從這件事,可以充分看出依靠群眾監督幹部這一措施的威力。
阻撓民眾進京「上訪」,是一種破壞朝廷與民眾的血肉聯繫、陷朝廷於孤立、失敗境地的罪行,其性質與反皇帝、反朝廷無異,幾近「十惡大罪」之二的「謀叛」罪,朱元璋豈能容忍!朱元璋是要「務得民情」的(32),有礙於此者,無論何人,都沒有好果子吃。
情況忽然逆轉,訪民遭鎮壓
正當民眾安居樂業、到處一片昇平景象、社會各方面均顯得欣欣向榮時,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大明建政後的第六十三年,江西中部新淦縣(今新干)卻突然發生了一起上訪民眾被官府鎮壓的嚴重事件,給和諧的社會畫面抹上了色彩異樣的一筆。它和整個社會無法協調,顯得那樣突出,那樣觸目驚心,以致人們在回顧有明一代的整個歷史時,不能不注意到它。
事情的經過,據《明實錄》的記載,是這樣的:
江西新淦縣丞厲中,……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催科,必非
法棰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錦綺不可勝計。民不勝毒虐,
遂集眾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眾捕之,
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康,官兵掩捕民,械送
京師,悉置於法。(33)
縣丞是縣令的助手,相當今天的副縣長。這個壞分子勾結、依靠土豪征辦賦役,手段殘狠:凡遇催科,對群眾必加棰楚。不僅如此,榨取的數量,又大大超過政府定額,為數竟達數十倍之多,從中大量貪污,攫為己有。非法所得的金、銀、錦、綺,多得不可計其數量。群眾實在受不了,起來造反,收拾了他在農村的爪牙,焚劫其家,而後走山谷躲避。當時,他們還留有餘地,給了厲中一個悔改的機會。但是厲中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派出巡檢進行追捕。群眾堅決迎戰,英勇抵抗,打殺巡檢,抓住為非作歹的貪官厲中,依例將其扭送京師,交給朝廷查辦。不料,還沒有走出江西,僅到鄱陽湖邊的南康(治今星子),就被官軍逮捕,送往北京殺頭,全部犧牲。
幾十年了,民眾扭送貪官進京交由朝廷懲辦,都是理直氣壯地,朝廷不但號召、鼓勵,還給獎勵。這一次怎麼反過來了,扭送貪官的民眾反而被全部殺頭?究竟這是判斷失誤的偶發事件,還是朝廷政策方向的根本改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事件的性質作出判斷,是容易的,就看政府後來改了沒有?如果只是偶發錯誤,政府事後一定會發現,並且予以糾正,作為冤案,對死者公開進行平反昭雪。而如果不改正,繼續照樣幹下去,而且越干越凶,那就說明政策方向從此根本改變了。
不幸的是:新淦事件發生的當代,乃至後代,直至明亡,都沒有平反昭雪,此後,形勢大變,民眾反對貪官,不唯不能受獎,而且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殺無赦。
新淦事件發生十多年後的1448年,福建農民鄧茂七因「郡邑長吏受富民賄,縱其多取田租,倍征債息,小民赴訴無所」,茂七因是扇動民眾,群起為「盜』,「劫其富民盡殺之」,政府派兵拘捕,起義民眾乃「殺巡檢及其縣官」。(34)這支因「赴訴無所」而起義的農民武裝,後來越滾越大,烏合至十餘萬眾,攻占了二十多座縣城。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為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宋彰「侵漁萬計」,用這些貪污得來的錢,向大宦官王振行賄買官,由參政晉升左布政使。到任,要撈回老本並使之增值,大刮其地皮,「小民苦為所迫」,告狀無門,群集造反,「旬日有眾萬餘,遂襲尤溪據之」。(35)
權力導致腐敗,是千真萬確的。官員手上有權,幾乎沒有不想濫用職權以謀私利的。明初,儘管朱元璋們大反特反官員腐敗,並且創造性地依靠民眾反貪,更鼓勵群眾扭送貪官,交給朝廷,予以嚴辦,大大抑制了貪腐的泛濫,即便如此,以權謀私的,仍然時有發生。就在新淦事件發生、反腐民眾遭到鎮壓的十年前,1421年,翰林侍講鄒緝就向明成祖朱棣講:「貪官污吏,遍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間有廉強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36)大張旗鼓,依靠群眾反腐,尚且如此,現在公然站在貪官污吏立場上,壓制反貪民眾,政府成了貪官污吏的支持者和庇護者,貪腐勢力必如「拉閘泄洪」,洶湧奔騰,排山倒海,勢不可擋,這是完全可以想見的。
明代中、後期,官場的腐敗確實觸目驚心。貪腐人數既極多極普遍,貪腐的程度又極深。大魚出深水。嚴嵩事敗,籍沒其家,「得銀二百五萬五千餘兩,其珍異充斥,愈於天府」,受賄所得奇珍異寶,比朝廷還多,還貴重。(37)劉瑾抄家,得金12,057,800兩、銀259,583,600兩,相當全國四十多年的財稅收入。(38)
一邊是貪官污吏大軍,一邊是廣大的民眾隊伍,兩者勢不兩立。走投無路的民眾,被貪官污吏所害,生活不下去,但有機會,必然造反。一波起義被鎮壓,不久,新的一波又起,再鎮壓下去,再起。起義-鎮壓-再起義-再鎮壓,中、後期的明代社會就是這樣度過的。在起義、鎮壓過程中,儘管有起有伏,總的說,民眾起義的地區越來越廣,聲勢越來越浩大,而統治者的力量則不斷削弱,鎮壓一次起義所需的力量越來越多,所需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困難,終於到了臨界點上,與民為敵到底的明政權最後徹底失敗,輸光了,垮台了,雙手沾滿民眾鮮血的大明末代皇帝崇禎上吊自殺,肥胖的福王在封地洛陽被憤怒的民眾宰殺,痛痛快快地,和鹿肉一起混煮,作了下酒菜,叫「福祿酒」。(39)
風風光光開始的有明一代,淒悽慘慘謝幕收場。
革命領導集團蛻變為特殊利益集團
明代是我國歷史上,漢代以後,又一個僅有的下層民眾起義取得的政權。明初幾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又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眾安居樂業的光輝時代。
同前元截然相反,我國在明代對鄰國實行「不征國」方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一個侵略成性的大帝國一變而為亞洲的和平堡壘,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既是亞洲世界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外交政治中心。(40)
前元時代,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次之,兩者屬於統治民族;漢人卑賤,南人最卑賤,兩者屬於被統治民族。明人打破了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的界限,解除了民族壓迫,各民族平等相處,組成了團結友愛的民族大家庭。
社會最先進的部分——知識分子,從蒙元時代的「臭老九」、僅高於乞丐的「九儒十丐」(41)的屈辱地位,獲得解放,一躍而登上社會的高端,「四民之中,士最為貴」(42),發揮了社會先鋒的應有作用。
在明代,奴隸不再像前元那樣,作為「生口」,標價出售,從明政權建立時起,凡「為人奴隸者,即日放還」,「復為民」。(43)「民因水患而典賣男女者,官為收贖。」(44)
諸如此類,都是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
在國際關係、民族關係、階級關係調整的同時,明初諸帝,注意生產,移民墾荒,興修水利,發展交通;輕徭薄賦,「藏富於民」(45);注重救災與社會救濟,「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社會經濟發展富有生機,民眾安居樂業。全國人口由洪武十四年(1381)不到6000萬,增加到永樂元年(1403)的6660萬,二十多年,增長了六、七百萬人。土地則由洪武十四年(1381)367萬頃,到宣德十年(1435)增長為427萬頃,半個世紀新增六十萬頃。(46)
明政權尤其破天荒地實行了向弱勢群體傾斜的社會政策,「鋤強扶弱」(47)、「右貧抑富」(48),這種政策在中國歷史上,唯有明代實行過,突出表現了這個政權初期的革命性質。朱元璋比向窮哥們許諾「苟富貴毋相忘」的劉邦強得多,心裡始終裝著貧苦人民,給老百姓確實幹了許多實事好事的。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此項過「左」激進的政策對社會的發展,也有負面的作用。但在當時,久受壓抑的底層民眾卻是熱烈擁護的。詩人歌唱道:
山市晴,山鳥鳴。
商旅行,農夫耕。
老瓦盆中冽酒盈。
呼囂隳突不聞聲。(49)
好端端一個社會,為什麼最終被破壞了?依靠民眾反貪,何等好事,為何半途而廢,而且反了過來,依靠貪官整治民眾,將大好江山葬送?
關鍵在領導集團的變化。
在革命年代,從1352年起義,到1368年大明建立,乃至1373年平定四川,基本結束戰爭,朱元璋集團是一支生氣勃勃的革命領導力量。他們高瞻遠矚的眼光,巧妙的戰略、戰術布署,堅定果斷的指揮,謀士們高超的計謀,都是一流的,無可比擬。他們所領導的部隊,軍紀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當時唯一一支愛民的軍隊,得到了人民群眾充分地支持。全體將士不屈不撓、浴血奮戰的鬥爭精神,保證了戰爭的勝利。而根據地的建設、正確的俘虜政策,對戰爭的最後勝利,也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那時,他們是萬眾矚目的。
但是,政權建立以後,情況不同了。掌握在他們手裡的權力,由於敵人的消滅無存,派不上用場了,「打天下『坐天下」,他們該享受了,權力遂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們手裡的資本,他們「安身立命」於這個政權,依靠這個政權,為己謀利,過起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
從來謀取江山的,都是把江山看做私產,朱元璋受時代的局限,自然不能免俗。所以,大明政權從建立之日起,就有兩重性:既是「為民」的工具,朱元璋們靠著它,解決民眾的生計問題;又是以皇帝為首的皇族及其「鐵桿」們謀取私利的資本和依賴。以新淦事件發生的1431年為分水嶺,明政權的兩重性,前期以「為民」為主,中、後期以「為統治者謀利」為主。
建國以後,皇族、功臣、官僚依靠政權,坐享其成。其他一切不說,單論俸祿。朝廷規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戰功最大的魏國公許達五千石,正一品一千四十四石。(50)而社會救濟政策,「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51)以口糧一年三石的標準計,皇帝的兒子(親王)不勞而獲,每年從政府所得,相當於16,666人一年的口糧,許達所得相當於1,666人一年的口糧,一品官所得相當於348人一年的口糧。
上層與下層的收入差別如此之大,在建政初期、吃閒飯的隊伍尚小時,矛盾不顯著。人們且容易把這看作是他們當年辛勞所得,是應當的,可以接受的。
問題是,不勞而獲的隊伍越滾越大。只說皇族,坐享其成的朱元璋家人,最初只有58人,對社會來說,談不上多大負擔。可是,宗室人口繁衍迅速。永樂時,便已達到127人。經百餘年的繁衍,至正德年間,宗室人口2,945人。嘉靖八年(1529),又增至8,214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為一萬餘人。兩年後,見於《玉牒》的宗室人口為19,600餘人。隆慶時,除郡主、縣主、郡君、鄉君、儀賓等女系和她們的丈夫外,男系的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及沒有名封和有罪而被革爵的庶人,共28,491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玉牒》載宗支人口為157,000餘人。再加半個世紀的發展,到明朝末年(1644),達數十萬之眾,應該說是不容懷疑的事實。(52)
千萬倍的翻滾!土地上的產量就那樣多,哪能承擔得了這般龐大的「上層建築」?正所謂「百姓稅糧有限,而宗支繁衍無窮」。
超級享受,難以為繼。永樂時,諸王祿米已不能全給,多者7,000石,少者700石。宣德以後,改行祿米折色,相當部分不給糧米,改支錢幣。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潤言:「天下之事,極弊而大可慮者,莫甚於宗藩祿廩。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三百十二萬;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借令全輸,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53)
經濟捉襟見肘,除皇帝、皇子(親王)、皇孫(郡王)三代外,自皇曾孫(將軍)及其以下,「饑寒困辱」,「多不能自存」,「常號呼道路,聚詬有司」,「守土之臣,每懼生變」。(53)代府奉國將軍聰浸連續五、六年領不到祿米,無以為食,詣闕自陳:「臣等身系封城,動作有禁,無產可鬻,無人可依,數日之中,曾不一食。老幼嗷嗷,艱難萬狀。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暴露十年而不得埋葬,有行乞市井,有行乞民間,有流徙他鄉,有餓死於道路。名雖宗室,苦甚窮民,俯地仰天,無門控訴。請下所司將積逋祿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待補,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飽。冒罪一死,亦所甘心。」(54)
一些中尉和沒有名封的宗室人等,因衣食無著,便故意輕斃人命、凌辱尊長而得罪,目的在於「發高牆以邀口糧充饑寒」。可是,鳳陽宗室監獄容量有限,宗室罪犯源源而來,守臣數告「高牆供給缺乏」。後由「有司於省城中蓋造閒宅一區,多其院落,繞以高垣,外設總門」,把有罪或有違《祖訓》的宗室人等,「移家安置其中,晝夜鋦護,五日一啟。」(55)
從前,學者們往往將明代的問題歸結為「土地兼併盛行」。事實並非如此。土地問題是重要的,但卻非關鍵。要害在糧食。糧食問題自始至終是有明一代的核心問題。皇室人員猛增千萬倍,為他們服務的官吏隊伍相應必然大大增加,保護皇室及其服務隊伍的的軍隊也不能不跟著大大增加。要保證這三支龐大隊伍的充分供應,不但要有飯吃,還要能夠過上奢侈的生活,出路只有一條:更多地壓榨農民,稅糧加征、加征、再加征。從鄧茂七「因府縣官吏收糧拘迫」,「嘯聚為非」(56),到李自成的「迎闖王,不納糧」,二百年間,農民運動無一不是圍繞生計問題展開的:農民要保命,不得不保口糧,政府要維持高效運轉,不得不從農民口中奪糧,對雙方,這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或者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面臨供應的侷促和緊張,在政府眼裡,能弄到足夠的稅糧,就是好官,颳得越多,越是良吏,官吏自己從中貪點,對民眾酷點,無礙大局。他們貪不貪,酷不酷,早就不在政府考慮的範圍之內了。
1488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的考核,標準五條:年老有疾、罷軟無為、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而無貪酷。另考查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款之外,又有升遷不協人望;大理寺丞的考查,亦無貪、酷兩條。(57)一貪一酷,曾是明初考察幹部「八目」中屬於第一、第二的最重要的兩款(58),自新淦事件後,已經被大明政權徹底廢除了。
新淦事件是明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有明一代新的歷史時期從此開始:具有兩重性的明政權,從最初六十多年間的重在服務社會,轉變為中、後期的以搜刮民眾為基本。生氣勃勃的明初「為民」的政權,「華麗轉身」而為反人民的政權。明政府改變了依靠群眾反腐的根本方向,轉而放手縱容官員貪污,並依靠貪官污吏來鎮壓群眾,不過是其政權服務重點轉移、政權性質發生變化的一個表現而已。新淦事件涉及政權同其基礎——人民群眾的關係,這是一個有關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水能載舟,亦可覆舟。新淦鎮壓,是導致明代終於滅亡的一顆種子。它與其它種子一起,無可阻擋地發芽、成長,最終葬送了大明的大好江山。
在新淦事件前,「愛民」的朝廷對於為生活所迫、聚眾為盜的民眾,是相當寬容的。從太祖朱元璋,到太宗朱棣,到宣宗朱瞻基,莫不如此。朱元璋說:「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恤,至致作亂。」(59)「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這是朱棣的看法。(60)「邊夷無故輒糾集萬餘人拒抗,或者邊將有以激之乎?」——這是朱瞻基平心靜氣的思考。(61)甚至正統二年(1437),歲飢,流民進入,荊襄難治,漢中守臣擔心:「不即誅,恐有後患。」英宗還反駁說:「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62)
是時,江西龍泉、永新「盜賊」討平後,江西參政胡昱建議在那裡設立軍事機構以御盜。朱元璋說:「民之為盜,由無良吏撫綏之,豈在兵耶?」不許。(63)就是在新淦事件前七年,1424年,五月,麗水、政和二縣「山寇」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巡按御史奏請發兵剿滅。朱棣徵求大臣楊榮的意見。楊榮說:「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相聚山谷,以求苟活耳,宜遣使招撫,當不煩兵。」照此辦理,「盜」果息。(64)
明代中、後期,情況迥異。民間但有風吹草動,神經質的朝廷立即恐慌起來,想到的措施無他:鎮壓。他們完全喪失了建政初期的自信,和由自信而來的對民眾的寬容。他們把自己擺在與民為敵的地位,草木皆兵,日夜驚恐不安,如坐火山口。越是鎮壓,自己越是下不來台。越殺人,越眼紅,越是要殺。心狠手辣,恨不得將造反民眾趕盡殺絕。他們以對民眾的屠殺「積屍盈野,流血成川」而自誇。(65)「其餘(民眾)潛石洞者,塞其門,以毒藥熏之,皆死。」(66)軍將韓雍對俘獲的瑤、僮民眾,「悉肢解刳腸胃,分掛林箐中,累累相屬。」(67)劉千斤起義失敗,「男子十歲以上者皆斬之」。(68)農民領袖趙鐩兵敗,「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死,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製鞍蹬,上每乘騎之雲。」(69)他們如此仇視農民,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非人民的敵人者何?鄧茂七等「苦富民魚肉」政府不能秉公處置,被迫起事,聲言:「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朝廷拒之不收。官軍就是要把你趕盡殺絕,豈容投降?(35)
至於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燒毀民居,搶奪民財,掠民為奴,殺民邀功,都是「以民為敵」的應有之義。「縱火焚烈房屋、禾倉一千餘間」(70),「毀碉房四千八百七十餘,牛馬、器械儲蓄以萬計。」(71)「焚廬舍一萬三千餘間,發地窖三千餘處,得稻糧三萬四千餘石」(72)「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一萬一百八十有奇」(73)甚至「搶殺良民為首級」(74),「斬賊首止八級,而所殺良民幾三千人,姦淫婦女及掠賣者無算。」(75)「所獲婦女,率指為賊屬,載數千艘去」。(76)……諸如此類傷天害理之事,記載於史籍者,多得不可數計。
他們和民眾勢不兩立,但是,生生不已的民眾怎麼會趕盡殺絕呢?最終被消滅的,當然只有他們自己,這些早已轉化為反動派、騎在民眾頭上拉屎拉尿的社會垃圾們。
朱明死亡過兩次。作為一個人民政權,它在1431年、建政的第63年,已然死去,大明變成大黑。作為一個維護皇族私產的壓迫人民的政權,它在新淦事件後,又苟延殘喘了將近二百年,於1644年終被消滅。而對民眾或親或仇的態度,則伴隨著興亡的始終。
⑴《洪武御製全書》589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②《洪武御製全書》429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③《洪武御製全書》583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④《洪武御製全書》586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⑤《全明文》第一冊6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⑥《明通鑑》107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⑦《明史》十二3806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⑧《明史》八2318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⑨《全明文》第一冊6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⑩《全明文》第一冊60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⑾《全明文》第一冊612、630、631、632、633、642、649、657、660、661、662、663、666、669、672、681、682、687、690、699、707、708、714、719、720、724、728、733、7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⑿《全明文》第一冊6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⒀《全明文》第一冊6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⒁《全明文》第一冊597、630、6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⒂《全明文》第一冊66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⒃《全明文》第一冊63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⒄《全明文》第一冊6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⒅《全明文》第一冊6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⒆《全明文》第一冊6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⒇《典故紀聞》92頁,中華書局1997年12月湖北第二次印刷
(21)《全明文》第一冊60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2)《全明文》第一冊6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3)《全明文》第一冊66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4)《全明文》第一冊6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5)《全明文》第一冊680-68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6)《全明文》第一冊681-6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7)《全明文》第一冊686-69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8)《全明文》第一冊596-5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29)《全明文》第一冊723-72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0)《全明文》第一冊7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1)《全明文》第一冊70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32)《洪武御製全書》589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33)《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24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34)《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轉引自楊國禎陳支平:《明史新編》17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
(35)《明史記事本末》1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6)《明史》十五4436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37)《明史記事本末》21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38)《明史記事本末》3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當時(1502年)全國夏秋兩季稅糧約3,000萬石(《中國歷代戶口、田地、天賦統計》33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糧四石折銀一兩(《明會要》下1012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朝廷歲入粗估折銀約為七、八百萬兩。其時,金銀比價約為1:7-1:8(黃阿明:《明代貨幣比價變動與套利經濟》,載《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3期,2010年5月)。劉瑾貪污,合銀約356,046,000兩(259,583,600+12,057,800×8=356,046.000),相當四十多年的全國財稅收入。
(39)《明史紀事本末》33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40)李洵《下學集》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41)中國歷史研究會《中國通史簡編》673頁,華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3月三版
(42)《洪武御製全書》62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43)《明實錄類纂·經濟史料類》40頁、《明史》一27頁
(44)《全明文》第一冊49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45)《明通鑑》368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46)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四次印刷
(47)張顯清:《從〈大明律〉和〈大誥〉看朱元璋的「鋤強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
(48)《明史》七1880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49)《明詩綜》卷100,轉引自《洪武御製全書》8頁
(50)《明會要》下786-790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1)《明會要》下959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2)張德信:《明朝典制》35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3)《明史》七2001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54)張德信:《明朝典制》37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5)張德信:《明朝典制》37-38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
(56)《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4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57)《萬曆野獲編》上299頁,中華書局1997年11月湖北第三次印刷
(58)《明會要》下846頁,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59)《御製洪武全書》690頁,黃山書社1995年7月
(60)《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11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1)《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20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2)《明史記事本末》1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3)《明通鑑》一348、350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4)《明通鑑》一628頁,改革出版社1994年7月
(65)《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8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6)《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20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67)《明史》一六4734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68)《明史記事本末》1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
(69)《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81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0)《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71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1)《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63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2)《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02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3)《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497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4)《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33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5)《明實錄類纂·軍事史料卷》534頁,武漢出版社1993年12月
(76)《明史》一六4962頁,中華書局1991年12月湖北第四次印刷
(原載《李蔚的博客中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