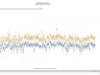《鹽鎮》終於正式上架,我想是時候告訴朋友們:我前後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和她們一起,活著。並且完成了這本書。
2021年6月25號,發完《易小荷|不想告別的告別》的文章之後,有那麼幾天我發現自己突然炙手可熱——許多朋友的慰問電話簡訊過來。紛紛問我需要什麼樣的幫助;還有熱心人牽線搭橋,讓我竟然有了一種可以絕地逢生的錯覺。後來才發現,錯覺就是錯覺。我最後的一搏,變成了更加可笑的笑話(此處省略三千字)。
於是索性就真的回到家鄉自貢,那幾個月,並沒有真正地哭一場,睡不著倒是真的。當我終於把自己安頓在自貢鄉下一間河邊的小屋時,我發現是如此的合適: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也就沒有向任何人解釋我命運跌宕的必要。推開門,目之所及,不是田地就是河水——與密不透風的高樓大廈比起來,這些讓我在落魄中體驗到新鮮的陌生感。

我當然想好了自己要做什麼,仙市鎮是我特意從備選的三個鎮裡面挑出來的。隔壁的王瞎子形容「劃一根火柴的功夫就能在鎮上轉一圈」,沒有書店、圖書館、咖啡館,自然也不會有電影院,美團、盒馬在這裡是無效軟體,當然也不會有滴滴——這幾乎就是我想找的那種既可以快速切斷過去,又可以在陌生感中收攬注意力的地方。
剛來的第一周,我需要和一隻巨大的原住民蜘蛛鬥智鬥勇。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尺寸如此驚人的蜘蛛,我甚至覺得它的體型,已經遠超陽澄湖大閘蟹。小窗看到照片說查過資料,這張臉應該是網紅蜘蛛,叫做白額高腳蛛,不會傷害人,而且還會幫著對付廚房裡的蟑螂。我每隔一個小時去看,它始終斂聲屏氣地呆在那裡,簡直就是一個安靜的美男子,只是石化了,和時間比拼著堅硬的程度。

有天早上起來在客廳裡面接了個電話,不知道怎麼迷迷糊糊地眯了一會兒,突然好像有滴水滴到胸口,然後睜眼一看,原來安靜的美男子突然掉到我身上趴著,我嚇得一激靈,從沙發上一躍而起,拼命把它甩到地上。此後有整整一個月,我都需要在屋子裡提前確定好它的方位,再據此來調整我的行動軌跡。

除了這個熟稔的「家養寵物」,天花板上還有一群神秘的動物,總在夜深人靜時分萬馬奔騰,當然有的時候它們的生理時鐘也不太準確,就會造成午飯時分開始出現騷動不安的節奏,間或傳來吱吱的聲音,和一些天花板縫裡漏下來的大顆耗子屎。
後來我想,或許這裡的生活過於安靜,以至於我對生活的觀察可以精確到所有的細枝末節。從前的日子遠去,沒有人爭相邀飯,也沒有商業談判和頻繁社交,剩下的只有,各種銀行貸款的頻頻問候。也好,我索性有段時間關掉了朋友圈,讓自己沉潛進入這無人知曉、無人聯繫的河底。
後來看書,看到有一段寫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辰光,因為「忘了門牌。他在陰暗的街燈下,來來去去地找了半個年頭,敲人家的門,詢問張德生的住家。直到夜晚二時要離開的一小時,他才放棄了他的希望,是什麼希望呢?他只希望跟一個可以說話的朋友說上一聲,我要回去下,黑夜兩點鐘的時候,我們要趕回西蘇門答臘去了。」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意識到,來之前和師友討論到「來寫一本書,看看故鄉小鎮的女性如何生活」的想法,會是一條「茫茫黑夜漫遊」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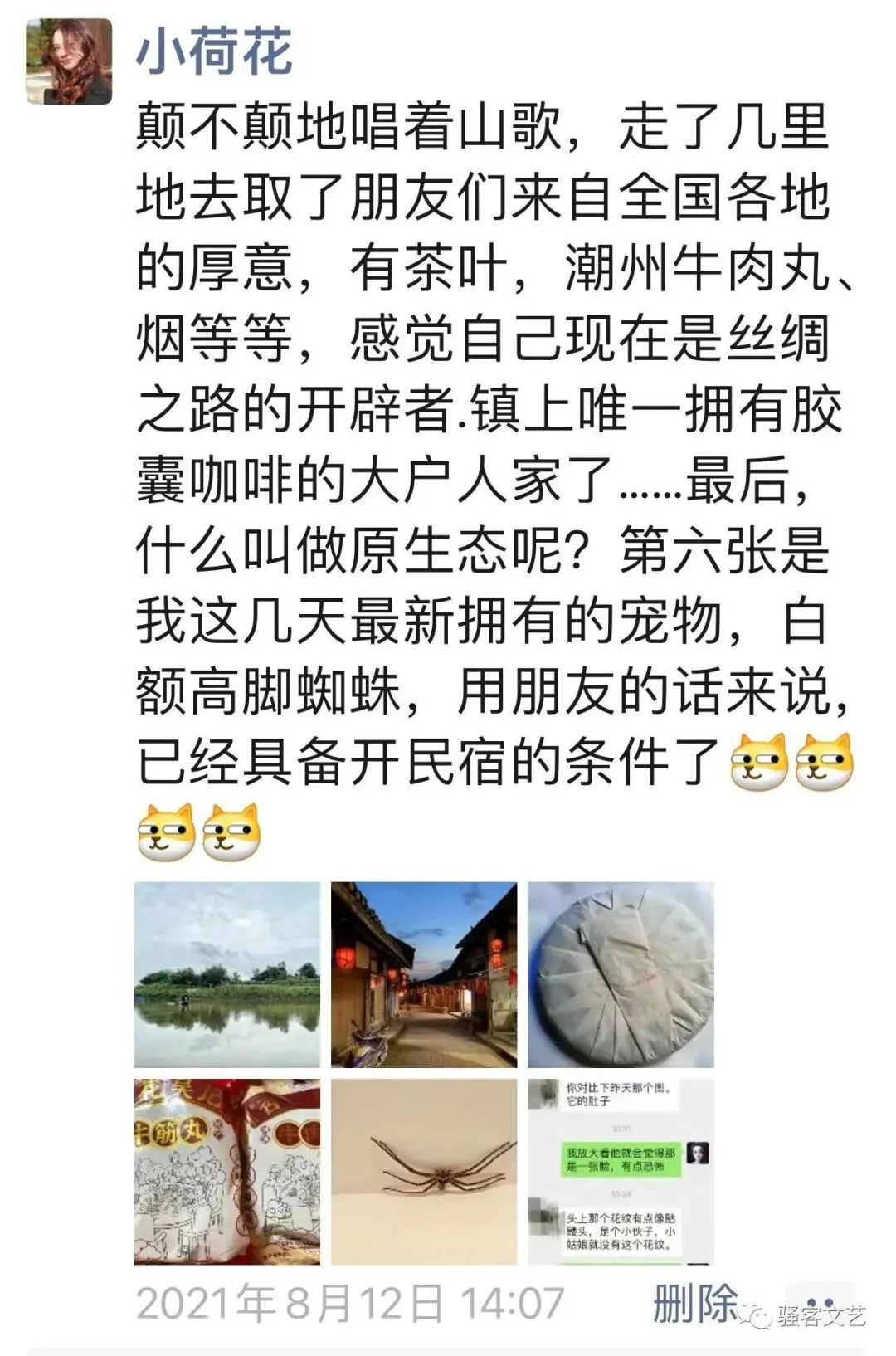
居所門口有家「張羊子羊肉店」,每次路過都能看到一兩隻山羊,大多呆呆站定在那裡,有次一隻山羊四處覓食,墊起腳尖把靠牆的掃把吃了,我覺得很有趣,忍不住上去喊它一聲,它立即看向我,咩了一聲。
第二天路過的時候,門口卻換成了一隻白色的小山羊——羊肉店門口的山羊,命運早就註定了,這還有什麼可說。我還是無端端有點難過,很後來我才知道,這仿佛是種隱喻——在這裡,生命是如此地卑微,來去無蹤。
到鎮上沒多久,一個女人自殺了,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在鄰居曾二嬸(慶梅媽媽)的茶館裡,我聽到的說法是:女人順了高鐵站的幾根鋼筋,被監控錄影拍到,高鐵站報警後,警察把她帶去問話,之後又去現場指認,第二天又把她帶去問話,回家的路上她就跳堰塘自殺了。
我請人指路,一路帶我去了那個村,離鎮上大概半小時的車程。遠遠的就能看到逝者家門口搭起的靈棚,人們擠在門口宰豬殺鴨,吃著送別的宴席。
人群里站著她兒媳婦和親家母,聽說我是作家,女人們就開始七嘴八舌地跟我說話。她們說那個女人才50歲出頭,家裡一個女兒已經嫁出去,身體不好沒有上班,一個兒子在上高二,又指指屋頭裡躺在床上的男人,「她老公身體本來就不好,現在又絕食了幾天。這個家全靠她去高鐵站打掃衛生那點工資。」男人呻喚起來,有人翻開被子,我看見他的面容和肢體,用「形容枯槁」來描述恰如其分。
她們說,女人起初以為只是撿了些許別人不要的垃圾,結果被派出所帶過去以後,男人在隔壁聽見類似於子孫後代會受影響之類的話;第二天過來傳喚,不讓男人去陪,結果到很晚也不見人回來。後來到派出所去問,派出所說早就開車給她送回來……
女人的屍體是在離下車地方將近兩百米的堰塘發現的,我去現場看,發現去那個堰塘並不順路,必須「翻山越嶺」才能抵達死路,我的腦海里拼湊出一個勤勞簡單的農村婦女,一輩子不捨得吃穿,盤大兒女,養著丈夫,突然被帶去當著眾人的面「指認犯罪現場」,又因為缺乏文化,覺得孩子的前途會被自己毀掉,於是就投了塘。
生命在這裡被碾軋到塵埃里,大部分時候沒有任何反抗。無論是人,或是貓狗。我見過一次一群孩子拿石頭砸隔壁的橘貓,它嚇得耳朵向後倒去,低著背脊尋找躲藏的地方,面對任何侵犯,除了躲避,它從來也沒想到過要去撕咬或者反抗。那些家養的蜘蛛更是有可能隨時葬身於一隻拖鞋底下……它們如果最後能活下去,也許只是因為順從了這裡的生存法則。

自殺女人的女兒沒有再回復,這件事也就不了之。
鄉村里多的是「免費的」苦難,一個男孩在垃圾站走失,他媽媽因此變得瘋瘋癲癲,二十幾年後這孩子才通過網絡找到;一個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嫁給了正常人的老公,因為農村每天都敞開大門,很久以後才發現她被人性侵,而罪犯卻是附近醫院的病人;有個會計兼老師在仙市小學給大家發完獎金,第二天之後卻人間蒸發;一個看上去健健康康的老太太,在地里摔了一跤之後再也沒有爬起來……諸如此類。所以我後來寫到:「貧窮和劫難,是家家戶戶的傳家寶」。沒人在追憶和描述的時候痛不欲生,他們不善言辭,仿佛也就不知畏懼死亡,活著就好,管它改朝換代,管它洪水滔天。
少時去美國採訪NBA,後來定居北京、輾轉上海,從巨型城市來到了小鎮,才真正意義地體會什麼叫做看天吃飯,就好像之前的生活只是一幅畫面的中景,而走進這裡之後,看得見顏色聽得到哭聲聞得到炊煙,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灶台上煙燻火燎的牆畫,展開來盡都鹽漬斑斑。

背篼是這裡的人們常用的工具,上海的超市買東西送油,這裡的超市送背篼,我立即就覺得簡單實用。
我潸然淚下的時刻有兩次:
一次是因為王大娘,我們初相識,是我特意讓她帶我一起去看仙婆——住在這裡的人,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篤信的一位仙婆,那就是他們的精神指引和唯一信仰。回來的車上,也許因為我們有了共同的經歷,她突然開始說自己的老公孫彈匠是個「爛帳」,玩過無數女人。更為震驚的是,之後沒有多久,就有鄰居告訴我孫彈匠當街打王大娘,「鎮上人人都知道。」
王大娘的這一生,出生赤貧,由於沒有生下兒子被老公嫌棄,老公一輩子出軌她一輩子忍氣吞聲,那個年代被計劃生育委員會強行流產,她記得兩隻手死死抓住床鋪的痛苦,醫生先給打上一針,引產下來之後,把死嬰給她看一眼。她閉上眼睛,感覺到一坨東西從下體出來了,伴隨著「哇」的一聲。
「當時醫生打引產針的時候應該是打到腳板,沒打到孩子的腦殼。慢慢扯出來之後,那個娃兒還是活的,差一點七個月,指甲都長全了,團臉團臉的,長得像我大女兒。孩子一邊哭,一邊拼命抓我的手臂。」
王大娘一直記得那雙小手留在手臂上的溫度,四十年後說起「那娃兒」都能清晰地記得「那娃兒是如何死的」。
說起這些往事的時候,她從來都沒有哭過。我注意到她們在講述個人苦難的往事時,眼神平靜,渾身散發出一種木頭般的呆滯,就好像水災、火災、大時代的劫難和傷痕累累的生活磨掉了一個女人敏感又細膩的感性觸鬚,她的右臉頰邊緣有條深邃的刻痕,那是被時間無情的斧頭劈開的。
她當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苦難,我問她記不記得孫彈匠打過她多少次,她說:「隨便亂說,五百多次肯定有了……」
那一瞬間,我想起《小城畸人》——「從每個人身上望下去,都如同一座深淵。」深淵可能是水災、火災、雷暴、來自他人或者不知道什麼樣的屈辱。
我認識王大娘的2021年,她62歲了。一個一輩子在小鎮生活的女人,幾乎就是鎮上的活字典。我想方設法去尋找仙市鎮的地方志,並沒有什麼結果。所謂的仙市古鎮介紹裡面,寫的全是名勝風景。
王大娘說她忍受了幾十年都是為了子女,對於未來她也沒有任何遠大的希冀,只是將來有一天百年歸老的時候,她的女兒能為她寫一篇關於她的一生。
而她一直活到老年,也就是2019年,還是因為老公被人砍殺,她衝上去救了他,才得到了這一生中他唯一給她買的禮物——一雙鞋。
還有一次則是因為陳婆婆,在這裡呆了快大半年才得以認識她。「陳婆婆」這個名字在鎮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她們都說她很會做那種生意,並因此被判過刑(監外執行)。認識之後,過了很長的時間她慢慢打開心扉,才拼湊出來她完整的一生:她歷經四嫁,卻從未領證。她用容留賣淫的錢養大了六個孩子,給每個兒子都買了房子,而她這一生,連一張屬於自己的床都沒有。
她沒有文化,只能做一些小生意:賣過胡豆,涼水、花生、茶水,最後受人指引,把茶水店變成「貓兒店」,因為她覺得「反正床鋪也困不爛。」我記得她翻開厚厚的墊絮,給我看屬於她的床,那就是幾根木板凳,她也跟我說之前小姐和嫖客們睡過的床給扔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下意識地覺得自己「不配」擁有一張真正的床。

有飯吃有床睡,能被人珍惜和重視,這不過是身為人最基本的要求,而她們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橘貓、黑貓、山羊沒什麼區別,她們只是活著,這也就是托舉她們在這塊土地上的,唯一的意義。


這裡的女人個個都勤勞善良,趕場的時候能看到她們仿佛被生活壓彎了腰,曾經想做一個鎮上女人的背影圖片展。
那天早上起來,從北走到南,從東走往西,最後停留在碼頭,看著100多米寬的釜溪河和古鎮對面的村莊,最後的擺渡人吳長生還在河上,兩隻槳相互交叉,每天早上6點一直到下午五點半,一個月20天,來回擺渡,把河對面的村民送往鎮上,把鎮上的村民送回村里。
我去過一次擺渡人的家,普通的兩層小樓,只有廚房安裝了幾片透光的亮瓦。屋子外面,被村里僅剩下的農田包圍著。
吳長生是45歲來做擺渡人的,退休之後又被航運公司回聘。冬冷夏曬,從此岸到彼岸,如此生活二十年。他肯定不知道西西弗斯,如今河上有橋,橋上有路,只是要繞很遠。「有些老的又不會開車,如果不擺渡,他們怎麼辦?」
我站在不知來處的田地里,頭一次感受到四季的分明,大自然輪轉的顏色,甚至是味道的差異。
在鎮上的一年多,我和數百人聊過,請她們吃飯,參加他們的婚宴垻垻宴,看他們做葬禮的道場,甚至和她們一起去請仙婆,盡一切的可能成為她們當中的一員,感受她們的感受,並從中「打撈」出來十二位女性的故事作為切口,90歲的陳婆婆(1932年)、63歲的王大娘(1959年)、59歲的鐘傳英(1963年)、50歲的童慧(1972年)、40歲的黃茜(1981年)、37歲的曾慶梅(1985年)、35歲的梁曉清(1985年)、35歲的陳秀娥(1987年)、26歲的詹小群(1996年)、17歲的黃欣怡(2005年)。她們的生活細節幾乎涵蓋了幾十年以來整個小鎮的歷史,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如此驚心動魄,以至於我在寫作完成之後,感覺耗盡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寫下這些竟是如此費力。

這方圓幾里之內,我已經見識到了那麼多形態各異的生命,不分高低貴賤地活著,在鹽鎮,人們擁有的,只有這條命。
夜幕降臨了,透扮家家酒戶戶敞開的大門,能看到小鎮的人圍坐在木桌前,拿起筷子,認真吃飯——那就是我這樣的人在遇到生活的重創之後,最不擅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