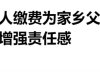這篇報導所揭示的,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的自殺內幕,而是中國部分地方產業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編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的員工在不到半年內,已發生「八連跳」系列自殺。在「六連跳」時,南方周末的實習生劉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潛伏進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記者又正面接觸大量富士康員工,多次訪問富士康高層……
但這篇報導所揭示的,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的自殺內幕,而是中國部分地方產業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在富士康觀瀾園區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即使像自殺員工盧新這樣多才藝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涂爾幹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我原來用的那台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線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 器,在扎傷人之後,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線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員工李祥慶說。
難以用統計解釋的「八連跳」
心理學家稱,富士康「八連跳」的自殺率仍低於全國平均自殺率。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盧新從富士康龍華區VIP招待所6樓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點30分。這是富士康深圳廠區三個多月內發生的第七起跳樓。在「被追殺」的恐懼里掙扎了三天後,這名外向樂觀的富士康2009級新干班工人,甚至來不及等待正從湖南趕往深圳的母親和弟弟。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樂觀、多才藝,2008年,他曾參加過湖南衛視的「快樂男聲」。
「被追殺」的幻覺產生於五一期間。即使是和盧新關係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紅領,也不知道幻覺背後的深層心理動因。5月9日上午,盧新的遺體在龍華殯儀館火化。他殘疾的父親——為了供盧新上大學,2006年父親在煤礦打工時腿被砸斷——並未到場。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掀動了這系列自殺的多米諾骨牌。「但這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說。
才過一天,劉坤即一語成讖。5月11日19點左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一線工人,24歲的河南許昌姑娘祝晨明,從租住在工廠附近的9樓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邊。據富士康通報稱,4月30日該女工已向工廠請了假,其自殺可能與情感糾紛有關。「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樣成為了自殺的藉口。」自殺學研究的創始人涂爾幹在一百年前說,「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
儘管他們的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體因牽涉死者隱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們人群構成,主要是指80後、90後。資料顯示,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裡面占到60%,大約1個億。劉坤提供的數據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90後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死亡掠過的富士康園區,生活仍在精確地繼續著。在距離盧新跳樓處不遠的大道上,人一樣高的車輪轟然碾過。銀行、咖啡館、食堂、商店對大雨中匆匆而過的青年們張著大門。在生產電腦主板的車間裡,白色工作帽下一雙雙眼睛秀麗明澈,他們像往日一樣快速在主板上插進電阻、線圈。等到17點30分下班,刷卡機依例給每個人一個紐扣大小的笑臉標記。
在過去的22年裡,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銘的領導下,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80餘萬員工。因其獨特的生產模式,2009年年底,僅富士康龍華園區,這塊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餘萬人,其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中國一個中小縣城,如城中之城。這個工業社區已很難用單純的「工廠」來定義,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行政經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稱為「郭台銘紫禁城裡的市長」。
盧新死後第二日,包括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長呂秋雲教授等國內多名心理學專家空降深圳,會診富士康。李金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內頂級心理學專家此行,是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的安排。
在專家的分析里,盧新以及稍早的、同樣跳樓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學校友劉志軍和其他四名死者(「八連跳」中田玉和饒淑琴重傷),跳進了一個統計數據里。他們稱,由於時間倉促,自殺的原因還無數明確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是遠遠低於全國的自殺率的。」2008年,中國自殺率大約是每10 萬人中有12名自殺者,而富士康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大約有2名自殺者。
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南方周末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維穩綜治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打工者排隊應徵,通過集合、形體查驗、填表、照相、考試、身份證查驗、體檢、分發八個程序後,即可成為富士康員工。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湧入。在「六連跳」後的4月13日,便有超過3500人進入。即使排上七小時的隊伍等候招工,他們中也仍有不少人談笑風生,滿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殺者中的多數,想必當年也曾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樣活著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幾個同學和校友之中。
盧新自殺的那個凌晨4點30分,李祥慶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公里外的H3成品倉庫度過夜班最難熬的一個小時。這個時候,他們通常坐在椅子上,雙手不時使勁地「乾洗」著臉,盯著前方一動不動。
李祥慶是4月12日進入富士康工作的。這是他第二次來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進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覺得「在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意思 」,出來了。大約20天後,湘潭大學機電專業的應屆生盧新進入富士康工作。盧新的大學班主任汪洋回憶,畢業前,盧新也去考過公務員,沒考上。後來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還認為這是上天眷顧他的幸運事。
從學歷和閱歷上看,盧新和李祥慶互為鏡像。前者大學本科,後者中專畢業,前者已經自殺,後者常常念叨自殺。但他們互不認識。即使認識,也應該會粗口互稱對方為「屌毛」。在廠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稱外的全部人稱代詞。「屌毛 」和「屌毛」之間很少有友誼。甚至,在馬向前死後(死於2010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認定死因為猝死),他宿舍的幾個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個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工作。」劉坤說。他認為,這是打工者不願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這樣的孤立中,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著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老鄉會」、「同學會」這樣的「非正式組織」(李金明語)在富士康幾乎是沒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壓力,便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和分擔。」李金明說。
這是一個奇怪的場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著。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藝大賽中,他憑演唱《你的樣子》獲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個新的「屌毛」來了,沒有任何歡迎儀式。等到某天下班,發現10個人一間的宿舍空了一個鋪位,才知道一個「屌毛」走了。「一個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說。
涂爾幹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或許恰是在這種孤立里,性或者愛情對於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為感情跳樓)。有女生的車間就是好車間,有女生的樓層就是好樓層。
「我真想去跳樓了。」李祥慶用剛發的勞保鞋踹著金屬柜子。剛進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機QQ上的責罵幾乎讓他哭了出來。外邊的機器還在轟隆隆地運轉,周遭的一切也都若無其事。那幾天裡,李祥慶甚至看見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侶就煩。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態強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線長)請了半天假,去車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沒想到這一切這麼快,女友原本還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點吃的給她,反倒還從她那裡拿了一點回程的路費,「太對不起她了,真的很難受,本來讓她拿走的錢她也沒拿」。
在這樣的人口密度里,談戀愛也是拮据的。「廠區里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據曾紅領回憶,盧新在去年8月進富士康以來,也尚未戀愛。儘管他多才多藝,並且也經常和曾紅領聊起愛情。
黑網咖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館」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的電腦上,這裡有不少「毛片」。在發工資之前,一些工友有時候也在這裡輕微地「解決一下問題」。但是他們說「看得難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資發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觀瀾宿舍區旁,從一個插著面破舊國旗的小路口走進去,小姐們坐在一棟舊樓下的長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價格,應該也是專為打工仔們設定的。
但不管是性還是愛情,都會撞上「錢」這堵冰冷的牆。
「沒錢沒車沒房」,「沒有錢你會愛我嗎,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李祥慶唱著不知從哪裡學來的歌曲。
他又操著湖北口音說,「媽的,老子十年之後攢夠錢了開車到她家去!開真的寶馬,反正不是倉庫的那種。」
李祥慶所說的「倉庫的那種」,指的是倉庫常見的油壓車。它們大多有毛病,狀況最好的那台,被他稱為「寶馬」,其它的,則只能算作「豐田」「吉利」和「奧拓」。
「嗜血的插針機」
紅色絕對是這裡「大凶」的顏色。把紅單發給員工,是開除,永不敘用;而把紅單貼上貨箱,這一整板的貨便須打回返工。當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受傷或死亡。
錢,是盧新和李祥慶的共同之「癢」。盧新家裡因為父親受傷和自己上學,至今還欠了十餘萬債務。曾紅領記得盧新從第一個月1800元的工資中,拿了1500寄給家裡,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塊錢。而錢對於李祥慶,則意味著他每日念叨的愛情。
是以,錢也成了他們申請加班的動力。這是一個悖論:中國的工人們主動向資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過討好線長、組長來實現這一點。
相對於其他崗位,H3倉庫里的工作輕鬆得有些無聊。現在,「寶馬」成了李祥慶練拳的木樁人。他對著油壓車的把手演練著無師自通的拳法。
F5半成品倉庫的辦公桌上,有一個用礦泉水瓶子剪成的別致花盆。盛了水,養著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兩片葉子。這讓堆滿龐大長方體深色物體的倉庫里有了一點綠色。抽屜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們抹在太陽穴上用來提神以及驅蚊。
從南門走到北門,貫穿全廠,是H3倉庫4月份新分來的員工每天的上班路線。沿路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著,除了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的序號,幾乎再沒什麼特質。榕樹、椰樹、棕櫚樹這些亞熱帶的樹木夾在樓棟間,它們的蒼翠蒙著塵灰。
即使最忙、最累的時候,他們也會表現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個閒暇,他們都會開著「寶馬」、「豐田」、「吉利」或者「奧拓」在空曠處「飆車」:站在車頭,像騎機車一樣,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全發現,會記大過,但是他們樂此不疲。
紅色絕對是這裡「大凶」的顏色。把紅單發給員工,是開除,永不敘用;而把紅單貼上貨箱,這一整板的貨便須打回返工。當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著受傷和死亡。
「我原來用的那台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線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器,在扎傷人之後,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線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李祥慶說。
類似的魔幻故事在廠區流傳。李祥慶原來在富士康觀瀾廠區是負責在塑膠板上插針的。要是有一個針眼偏了一點點,板上的孔就會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貨後被 QA(品管)發現,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時候手感不佳總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會抄起身邊的銅棒或鋼棍對著機器亂捶一氣。奇怪的是,打過以後,不管是機器還是自己,都順起來了。
4月25日晚,H3成品倉庫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機軋了一個工人的腳,幸好穿了勞保鞋,未骨折,據說自己還能走路。
但傷者惹人羨慕。「我靠,工傷,多爽,有工資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個月才回來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說。
死亡的信息,似乎從來不給這個人群帶來任何影響。「富士康又死人。」李祥慶一邊拍著大腿,一邊看著手機新聞逐字念出來。「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連跳』嗎?」
即使盧新,曾紅領回憶,當時盧也覺得自殺者離他很遠,談起「六連跳」,盧新覺得「他們很傻」,「自己不會去做這樣的傻事」。
盧新是大學新干,是坐辦公室的,但普工們面對的是高溫、噪音等崗位。儘管能拿到相應的補貼,但是新進的普工,都盼望著能分到一個安全的崗位。可這很大程度上靠運氣。運氣差了,崗位不滿意,便辭職或自離,重新招工進來,再賭一把。
在觀瀾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曾在那裡工作的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廣西佬」李加龍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錢折成的花,他說是「撿到的」。工牌邊掛著指甲鉗和一個小塑料盒,裡面是兩個工作時用的耳塞,一個辭工走的人送給他的。他在碎料的崗位上。如果沒有這兩個桔紅色的軟塑膠塞子,一個班下來,巨大的噪音,能讓人的手腳不聽使喚。
而等到剛出廠門,打火機幾乎同時作響,男工們不約而同點起煙,到這裡,他們在機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結束。
不知所措的青春
自殺者盧新在日記中說: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
即使親近如曾紅領也不知道是什麼讓樂觀、外向的盧新突然精神異常。
目前所能找到的、盧新最後的日記,發布於2009年10月26日17點35分。這篇載於「校內網」其個人主頁上的日誌,清晰記錄這個喜歡哈士奇、喜歡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對於前途的不知所措:
「放棄了最喜歡的公共職業:支持西部建設,為了錢,來到了公司,結果陰差陽錯沒進研發,來到製造,錢還算多,但在浪費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後悔……現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錯了,很迷惘……」
在盧新自己創作的歌詞裡,他回憶起兒時的歲月:「風輕輕的吹過,掠過一絲羞澀,兒時的往事黯然失色。」
當躺在倉庫的棧板上時,李祥慶也會講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裡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著吃……
在一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的眼裡,生於1985後的盧新、李祥慶這樣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備這樣的性格特徵:更傾向於個人主義,更習慣於城市的消費文化,經濟負擔較輕。與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是他們卻經歷著更加顯著的城鄉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會排斥。
或許這是困於此種際遇的一種無意識表達,中國的新生代打工者在這個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戀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歲上下的少年,相約在台州市的一處街心花園服毒,其中兩人死亡。
而在管理者看來——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來大陸,他管理過兩代打工者——第一代農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滿足,而新生代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他們這一代人,是如何從台灣農村,一步步成長為頂級的管理者。
沿著東環二路富士康龍華園區向東走去,每天都有六七個算命的蹲在路邊。一個河北口音的算命師父告訴記者,來照顧他們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們花上10塊錢,讓他們在自己手心尋找命運的脈絡,「每天都有二三十個人」。
從南大門出來,向佳潤宿舍方向走去,有一個彩票出售點。這裡總是人潮洶湧,儘管沒有傳出過誰發了橫財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點已經下班,一員工還在一直看著那掛出來的「下班,停止銷售」的牌子。
從中心花壇的噴水池往北走去,左手邊有一家書店,面積不大但分類清晰,五臟俱全。書店總是有一個女工蹲在MBA數學考試的複習書邊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學歷可以高一點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數字遠看並不清楚。但頁眉上藍字印刷的「知識改變命運」分外鮮明。
沿著出龍華區富士康南大門的路,一直往南,大約一公里,有一個小廣場。這裡出售著富士康生產的各式高檔手機。他們經常過來看,「這都是我們廠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卻總是四五百塊錢的山寨版。
從觀瀾廠區的大門出來,過天橋一直往前走,有一個商場。商場四樓,有一元錢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錢一局的撞球。這是年輕的打工者打發夜晚的地方。
從「紅太陽歌舞廳」出來,下坡,穿過兩棟住宅樓,是一個溜冰場。警察們從打工者隊伍中揪出了幾個赤膊的人(聽說身上有搖頭丸)帶走。隨後,震耳欲聾的音樂再次響起。
而現在,以及以後的日子呢?
河北的高海偉用一個撿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齡球。作為一個河北人,他說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環外,哪怕是順義,通縣。他哥就在順義買了房子,有個家。
王克柱說只有知識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給自己報了一個英語培訓班。但很快就放棄了,「沒辦法,聽都聽不懂」。
李祥慶的夢想是賺錢、發財,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著我走啊,我討飯的時候在旁邊看著,給你個饅頭。」
而自殺者盧新,他曾經希望成為一個歌手,後來希望成為一個公務員。但5月2日開始,他變得情緒異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紅領他們一起喝酒。他告訴曾紅領,他覺得「工作壓力太大了」,「睡不好」。
到5月5日晚10點,他開始顯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著自己「不夠孝順,給父母的錢太少」、「自己活不過當晚」。他開始恐懼整個世界。晚上11點多,富士康公司將盧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
5月5日上午,他甚至給母親電話說沒事,不用過來。——稍早一些時候,曾紅領他們已經將盧新的精神異常狀況告訴了他的親屬。
5月6日凌晨4點30分,正在火車上的母親和弟弟大約4小時後便會到達深圳照看他。但盧新沒有等到這一刻。在床上幾個小時的輾轉反側後,盧新從朋友的身邊爬起。他說想看看窗外的風景。那時朋友就站在他的身邊。幾秒鐘之後,他就從陽台上跳了下去。
他最好的朋友王軍想抓住他,卻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統一發放的、短袖工裝的衣袖。
(因受訪者請求,王軍為化名)
與機器相伴的青春和命運——潛伏富士康28天手記
作者: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志毅 發自深圳
■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
■他們生產著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產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著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帳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於自己的「8」。
我認識兩群年輕人。
一群是與我一樣的大學生,他們生活在象牙塔,與圖書館、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鋼鐵機器,巨大貨櫃,有無數繁雜精密生產環節的廠區里。這群人總是把他們的上級叫做「老闆」,互相之間哪怕不熟也要大聲用粗口喚作「屌毛」。
在富士康潛伏28天後,我走了出來。我一直試圖把這兩幅圖景聯繫起來。可是很難。只是這兩個地方生活著的人們確乎有著相同的年紀,相同的青春夢。
我的潛伏,起因於南方周末對富士康「六連跳」系列自殺原因的調查。編輯部很快發現,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均因年齡較大無法進入只要20歲上下年輕人的富士康工廠。相較而言,不到23歲的我,很輕鬆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潛伏,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並非因為明白了他們究竟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著。
【一】
他們活得最闊綽的一天是每月的10號,發工資的日子。這一天,自動提款機與特色餐廳里都會排起長隊,以至於提款機也會時常被提空。工資由當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費組成。
每個員工都會簽一份「自願加班切結書」,隨後你的加班時間便不再受法律規定的每月上限36小時的約束。但這並不是什麼「壞事」,相反,在許多打工仔看來,加班多的廠才是「好廠」,因為「不加班,根本掙不到錢」。對急欲賺錢的打工者們,加班更像是「會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沒有錢的日子讓他們「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勞累的工作只會讓身體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後者,甚至這種選擇的權利,也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只有老大「信任 」,關係好,或是身處關鍵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對一些人來說成了憂慮,因為花錢不掙錢的日子「很難熬」。這一天,打工仔們顧不上是什麼節,更重要的是加班費;實在不行,睡個懶覺更實在。
新開的手機店門口,銷售員洋氣地向圍觀的員工們展示著iPhone,所有人都緊緊盯著他每一個「酷炫」的操作,像看著什麼新奇。可事實上,富士康生產著包括iPhone、iPad在內的幾乎所有知名品牌數碼產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機器每個部件都來自這些工人們之手,只是他們從未想過擁有最終的成品。現在,這些成品就以略高於他們一個月工資的「驚爆價2198元」出現在眼前。這是一筆昂貴的購置,所以他們只討論著怎樣花幾百元去買山寨手機。
在與他們聊天的很多時候,我無言以對,我覺得自己幸福得太過分。他們居然羨慕那些受工傷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著笑話一面說自己的工作崗位如何有毒。他們討論自己的同事們跳樓自殺時,往往有著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語出戲謔,似乎每個人都是局外人。
我願意把他們看成一群樂觀與堅忍的人,也希望他們真的是與此無關。不過這願望怎樣想來,都免不了是一種心酸。我甚至想像自己有改變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時候說「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腳來交換5分鐘的休息時間」一樣,很天真,更沒可能。
【二】
你要問打工仔們的夢想是什麼,答案如出一轍,做生意,賺錢、發財,其它一切在這之後都會到來。在工廠的倉庫里,他們幽默地把拉貨的油壓車稱作「寶馬」。他們倒是想擁有真正的寶馬,或者至少是「寶馬」式的財富。
他們時而幻想,又不斷地親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個痛苦的畫者,無奈地不斷撕毀自己難以成形的手稿,「這樣幹下去,一輩子也別想」。他們生產著世界上最頂尖的電子產品,卻以最慢的速度進行著自己的財富積累。辦公系統的公用帳戶密碼被設成以「888」結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樣,他們喜歡這個數字,甚至篤信這個諧音。但是他們中或許鮮有人知道,是自己的雙手保住了國家的「8」,而他們每天去加班,去買彩票,甚至去買馬,卻難以找到屬於自己的「8」。
工作最賣命的王克柱總抱怨工資太低,想去外面報名學點東西卻又「聽都聽不懂」,還是放棄了。他說知識太少,就只能幹最初等的活,這是註定的。他有時候說頭很痛,有時候又瞬間精神煥發。拉貨的時候他總向前飛跑,仿佛那兩板24箱貨物根本沒有多重。每天他都會爬上兩三米高的貨箱去盤點帳目,也會鑽到夾縫裡去檢查標識單。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賣命,他並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聲:「救命!」他大約也不知道剛才自己說了什麼,我卻聽到一群真實的靈魂。他們習慣了用最大努力去改變,直到努力演變為掙扎,也沒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開生活的大繭。
廠區里一幢幢廠房整齊敦實地豎立,除開頂上用英文字母和數字組合起來的序號,便幾乎再沒什麼特質。廠房裡的機器,倉庫里的貨箱,乃至流水線上著齊整工衣的工人們,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見廠房的窗戶里探出兩張臉,一動不動,一直望著路上的墮胎。太遠,看不到表情,也聽不見聲音,那窗里僅是兩個黑點。可站在他們的位置,這路上無疑也是一大群移動的黑點,無比巨大的白色廠房背景下,他們渺小而一致。
【三】
這個工廠的工人們用雙手支配著世界上最尖端的電子產品的組裝生產,不斷刷新著令人激動的貿易紀錄,連續7年內地出口額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們操縱機器的同時,機器也操縱了他們:零部件在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環節中流過,加工成型;他們單一而純粹的青春,也在機器的特有節奏中消磨。
凌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牆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麼快,會在食堂里吃得那麼急,雖然並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部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凌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當深圳,這個曾經的邊陲小鎮一躍而成為珠三角東岸最繁華的都市之一,在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背後,我遇到的卻是一群迷惘焦慮的年輕人。《時代》雜誌在2009年把中國工人作為了年度封面人物,這本雜誌說,中國工人以「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然而所謂「堅毅」,卻是忍耐機器異化、資本侵蝕所必需的品質。這樣的「堅毅」,還是他們可承受之重嗎?當電腦、手機、汽車,每一樣商品都成了資本的產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樣代價也被資本消耗殆盡。
這個容納四十多萬人的巨型工廠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血汗工廠」。它提供食宿,規模達到一個中等城鎮,流水作業,井井有條。與同類相較之下,這裡的設備齊全而優越,待遇標準而規範。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蜂擁而至,只為找一個自己的位置,找一個也許他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實非一個工廠的內幕,這是一代工人的命運。
破解富士康員工的自殺「魔咒」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楊繼斌 實習生 劉志毅 發自深圳
參與調研的心理學家認為,富士康員工自殺多數由心理疾病造成。但亦有社會學者指出,新生代打工者實際收入遠不如父輩,又缺乏回到農村的退路,他們的焦慮無助是自殺增加的深層原因。工廠要建立員工心理關懷機制,政府更應提供對新生代打工者的制度關懷。
「魔咒」與心理疾病相關
在25歲的盧新自殺約30個小時之前,三名20歲上下的青年,相約在台州市的一處街心花園服毒。兩人死亡。
在盧新自殺五天之後,他的同事、已處在家長照顧之中的許昌姑娘祝晨明從所住的宿舍樓跳樓身亡。
在更大的視野里即可發現,死亡的魔咒並不只在詛咒著「郭台銘的紫禁城」。
為了阻擊接二連三出現的跳樓事件,富士康從四月上旬開始「花錢買信息」:任何職工只要發現身邊的同事情緒異常,便可通知心理醫師或者部門主管。若情況屬實,公司獎勵200元。
截至5月10日,這場「人民戰爭」讓富士康衛生部發現了二十餘例情緒異常者。其中已經患有較重精神疾病的,在家屬同意後,送進了深圳康寧醫院;另一些情緒異常但無需住院治療的,則由家屬陪伴回到了老家。「但我們覺得很挫敗。」劉坤說。讓富士康感覺挫敗的是5月6日凌晨4點30分的盧新跳樓事件。可是,劉坤尚未從6日的挫敗中緩過氣來,新的衝擊便又來了。
在盧新死後第二日,富士康將多名中國最好的心理學專家請到廠區,尋求強有力的心理學支持。但仍無濟於事,員工祝晨明又跳樓。之後,富士康請了五台山最有名的高僧大德,到園區為死者祈福。
在「六連跳」到「七連跳」、「八連跳」,有媒體質疑連續出現的自殺事件,是因為富士康是「血汗工廠」,高密度的死亡與其「半軍事化管理」有關。
富士康科技集團工會副主席陳宏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第六跳」發生後第二天,深圳市總工會便到富士康調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總工會公布富士康近期多位員工墜樓事件的調查結果。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稱: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業吸取教訓,建立人文關懷的管理體制。
「群體這麼大,基層的管理上肯定會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但這和自殺肯定是沒有直接關係的。」陳宏方說。
南方周末在富士康的近一個月調查發現,管理本身並無異常之處。
「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也很難與富士康的工作壓力、『血汗工廠』聯繫起來。」北師大心理學教授張西超說,「當然,我們也認為,富士康應加強對員工的心理危機干預,防止類似悲劇發生。」參與調研的心理學家均認為,這些自殺事件基本與富士康員工個人的心理疾病,特別是抑鬱症有關。
據富士康集團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介紹,實際上早在2009年7月份的孫丹勇事件後,員工的心理健康便出現在富士康(中國總部)最高管理層的問題單上。一批心理諮詢師補充到了集團里來。
現在,富士康還開通了78585(諧音「請幫我幫我」)熱線電話,給員工提供心理諮詢。與此同時,一個旨在疏解員工心理壓力的「心靈港灣工作室」也開設了,員工在這裡不僅可以接受心理輔導、通過專業儀器放鬆身心,還可以在確保隱私的前提下,在宣洩室擊打橡皮假人。
「公司管理層都願意把自己的照片,套在假人上,供員工們發泄。」劉坤說。
4月下旬,針對員工之間缺少溝通的現象,為了方便室友之間交流,富士康甚至下通知鼓勵朋友、老鄉住在一個寢室。「我們在開展心理輔導講座時,即興搞過有獎問答,誰能說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獎勵1000元。但絕大部分人答不上來。」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
劉坤告訴記者,郭台銘將在本周內專程趕赴深圳,為「員工關愛中心」掛牌。成立的日子還不到20天,悲劇再次發生了。
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慮
「許多問題,都出在上游,只是因為水流到了富士康這裡,問題集中暴露出來,所以大家以為是富士康的問題。」劉坤認為。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曾經多年研究過深圳的農民工問題。在他看來,「八連跳」並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心理問題,更是社會的問題。「只是因為富士康人口基數大。」劉開明說。
劉開明在整個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群體的歷史中,研究當前農民工高密度自殺的原因:20世紀80年代,在全民普遍低薪的歷史背景下,農民工(外來工)的工資每月高達200—600元,當時大學教授的月工資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後,得到制度庇護的城鎮在崗職工工資增長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來工工資增長則十分緩慢。隨著經濟增長的加速,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2008年,「珠三角」和「長三角」出口工廠的工人平均年收入僅是這兩個地區城鎮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的37.82%。
「考慮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所獲得的薪酬,要遠遠少於第一代打工者。」劉開明說。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早在1990年代後期,便開始關注中國的打工群體。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說,新生代打工者相對他們前輩,承受著更多的焦慮。
從2005年到2008年間,潘毅多次和同事在深圳和東莞,研究新生代打工者,她得出的結論是,相對於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家鄉回不去了。新生代農民工大多不會從事農業生產、不適應農村生活;二則,失地農民越來越多,即使想回去,家裡也沒有土地。
實際收入銳減,退路又無,新一代打工者面臨著比他們的前輩更大的生存壓力。
而涂爾幹所謂遏制自殺的最有效的障礙——集體,也並不能給中國的新生代打工者提供幫助。
「目前的社會管理制度框架,使每一個打工者處於原子狀態,他們沒有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劉開明說。
富士康行政總經理李金明以他的方式描述了工人的這種「原子」狀態:「不管是正式組織,比如工會,還是非正式組織,比如老鄉會,同學會,普通員工都找不到,所以壓力大,卻無法舒緩。」
「必須從源頭解決問題,一方面,提高打工者的收入,消除他們的集體焦慮感;建立有效的集體組織,讓他們處於一個多維度的人際關係網中。」劉開明說
富士康高層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盧新跳樓以後,郭台銘曾專門致電李金明,要求資方配合工會,加大工會的監督力度,要把工會的獨立性體現出來。富士康的行政與工會都直接同時發文,嚴格控制任何超時加班。郭台銘還請集團緊急調查,聘請海內外專家會診集團員工的心理健康。
但在李金明看來,僅憑企業的力量是不夠的。「所有的工作我們都可以做,但該怎麼來解決這個量的問題呢?」李金明說。他希望,政府在提供生產便利的同時,還能提供生活的便利,社區功能日益完善。而學者們更希望政府提供對打工者權利的制度性關懷。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劉志毅 楊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