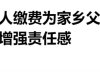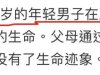年輕人抉擇:做北上廣沙丁魚 還是做家鄉鹹魚
是選擇在北上廣,被擠得像沙丁魚,還是選擇在老家當死鹹魚?逃離大城市的壓力後,他們迷失於小城市的平庸與固化。
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面,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於無根狀態的人。
這些年輕人左右為難的旅程背後,是幾乎一代普通青年艱難安放的前途與希望。
三個月後,張一軒受夠了老家那個長江邊上的地級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夠了北京,頭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樣。
他走那會兒,正好趕上「逃離北上廣」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生活壓力持續增長,白領中興起到二三線城市安家的討論。而張一軒的歸途,又趕上了「逃回北上廣」的熱潮。
單就回家這一段路,張一軒走得要比其他人順暢。父母在當地頗有聲望,沾他們的光,張一軒自然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甚至沒有參加統一的公務員招考,當地菸草局就收了他,領導很大氣,說,明年考一個試就完了,你肯定過。
一批年齡在30歲上下,混跡於北上廣的外省青年們,當初也都和張一軒一樣,以為老家意味著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愜意的幸福細節。逃離北上廣。口號叫得嘹亮,帶著爺不留此處的痛快。
重返家鄉,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終究需要一個台階,事關面子,這無異於讓他們承認,迄今為止所有出走的嘗試都失敗了,丟掉既有的圈子,他們應當放棄不切實際的努力,讓鄰里鄰居眼睜睜瞧著,這個迷途知返的人。
不過再怎麼著,面子也比蝸居的現實更廉價。搖擺之間,返程的機票或者車票就訂好了。
從某種意義上,這一張往返程的票根,是兩個城市對他們下達的「不適宜鑑定書」。北上廣以及家鄉都不適應自己了。外省青年眼裡,北京是堵的,貴的,擁擠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廣。而回到小城市,是勢利的,關係的,拼爹的,依舊是別人的。
來者與去者
張一軒吃回頭草、在北京石景山那邊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頭的工作的時候,祖籍江蘇的劉寅則醞釀著離開北京。
劉寅租住在北京東六環,每次到國貿搭計程車,黑車司機在嚷嚷,20塊,通縣走不走?他非得糾正,是去通州嗎?說的是一個地方,但他怕那個「縣」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劉寅生在江蘇一個縣城,來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過萬,兩年沒加過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長,觀望了幾年的結果是,手裡存款一路貶值,時至今日,他買不起北京五環內一套兩居室的房子。
無車無房無根,撤離的念頭連同妻子肚子裡的孩子,越來越茁壯。他變得像罹患產前憂鬱症的卡夫卡,買房、擠地鐵、喝水,甚至呼吸空氣,日常生活的一纖一毫,都讓這個80後男人疲憊不堪,「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
在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里,劉寅是北京市704.5萬外省市來京人員之一,數字仍在往上走。這近千萬人口大數里,許多像劉寅這樣勉強的中下產,抵達了人生的某個瓶頸,幸福指數開始往下走。
也有「蟻族」,大學擴招後迅速膨脹的畢業生們,他們生活在郊區的聚集群落,月收入兩千左右,可以沒有獨立的廚房和廁所,但決不能沒有網絡。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沒有實現夢想,大部分選擇離開,往往「三十而離」。據估計,北京地區至少還有十五萬「蟻族」。(數據來自學者廉思的調查《2010年中國 「蟻族」生存報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動人口到「服務」外省人的華麗轉身,而這管控的態勢,隨著1800萬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來,愈發嚴峻了。年初一連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門檻: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購令,車市限購令,「以納滿稅五年」為條件,搖號另算。
有專家呼籲年輕人不要扎堆北上廣,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個聲音在感召,「去農村吧,去基層吧,廣闊天地,大有所為」。
很多次,劉寅假設人生三種曲徑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滯留北京,繼續苦哈哈的生活,能認識更多人,更多學習機會;
其二,回歸南京准一線的市井,買車買房,吃吃喝喝,心寬體胖;
其三,回縣城找塊地,養鴨子餵豬,徹底的田園牧歌。
沒有數據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劉寅式的糾結。
山東姑娘唐果,和張一軒一樣,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廣」者。
她第一次來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業中的農村女青年唐果氣咻咻地離家出走了,夥同幾個同學,從山東濟寧一火車坐到北京,只揣了讀書時賣資料攢下的兩千塊。
首都沒有電視上演得好,天不那麼藍,公共交通地鐵擠得慌。偶爾路邊還躺著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幾個男生起鬨說蘇寧在招聘,職業規劃圓滿,前途無量,於是她去了大興區的蘇寧電器,賣電視,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遠,在豐臺區西局村里一條望不到盡頭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滿豪車的東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間比棺材強點兒,只一張床,沒廁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邊亂糟糟,在木樨園公車站等車,站牌被「廣東少婦求子」類的小廣告貼了個遍。老家房子倒是闊氣,大院裡有花有草,四五年前還有了空調電腦,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時候這個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當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學著跟北京人一樣添「堵」。要麼「堵」在路上,要麼「擠」在地鐵公共交通里,擠得元神出竅,佛祖現世。
經過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決定找個北京人嫁了。實在不行,找個男朋友,至少能做個飯,搭個伙,順便提高安保係數。籌碼:23歲,一米七的個頭,大專學歷。有人給她介紹一大興男。大興過去是北京郊縣,這些年隨著攤大餅的城市化進程列入市區,大興農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遷而生的千萬富翁俯拾皆是。見了一回面,這事兒就吹了,倒不是因為別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勁兒。
用了windows7的系統,就用不慣windows98的了
來了,又為什麼要走?或者,走了,又為什麼要回來?
張一軒1988年生,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生。畢業去向班裡約是三三開:除了簽約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的極個別,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掙三千多的月薪。張一軒屬於最後那類,在CBD一家傳媒公司上班,每個月一半的錢轉給銀行房貸,其他一切從簡,每天麥當勞肯德基(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 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噁心了。
他有點像《蝸居》裡的小貝,高大帥氣,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個北京姑娘談戀愛,一心要奮鬥,紮根北京。直到某天,經濟規律無情地左右了他的個人命運——姑娘跟一個留學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鍊。吹了。
吃噁心了麥當勞肯德基,顯然不是張一軒「逃離北上廣」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為了寫一個明星劇組如何不畏發燒拉肚子堅守片場的宣傳稿,他熬了一個白天加半個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級瞥了一眼說,還是用第二稿吧。
他決定聽爸媽的話,回家當公務員。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溫暖故鄉,父母把一切都準備妥帖了。
新工作性價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個人占了會議室那麼大的辦公室,工作內容基本是偶爾發發傳真和每天陪領導吃飯。多數時間坐著玩電腦,下班跟爹媽吃飯、看電視、睡覺。日子懶洋洋的。很快,懷著專欄作家夢的張一軒發現了一個糟糕的信號,他寫不出東西了。
一天上班,領導說,走,查煙。張一軒很好奇,學著領導,把「菸草稽查」的袖章一個個往身上戴,一臉嚴肅地列隊出門。所謂查煙,就是查雲煙、湘煙,發現一條罰一千。當地的煙商看樣子也不缺錢,人民幣一摞一摞地拿出來,畢恭畢敬。一天下來,少說幾萬到手,報紙一包就扔公車上。
這筆罰款在財政體系運作之外。不用入帳,拿了錢,哪裡貴就往哪裡去「燒錢」。查禁的煙呢,領導對張一軒說,拿回去給你爸抽。那一天,張一軒「覺得自己特像個狗腿子」。
責任編輯: 夏雨荷 來源:南方周末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11/1116/225519.html
相關新聞

 自家門上裝智能門鎖 被鄰居告了 法院這樣判
自家門上裝智能門鎖 被鄰居告了 法院這樣判 司機接單不接客 成都女子3次被「拒載」
司機接單不接客 成都女子3次被「拒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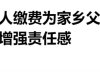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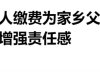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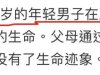







 這年輕人,總結的真好(視頻)
這年輕人,總結的真好(視頻)
 中國疫情蔓延 年輕人猝死 單位下封口令 視頻
中國疫情蔓延 年輕人猝死 單位下封口令 視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