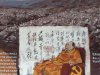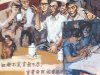(一)杜鎮遠(1889——1961),鐵道部重點批鬥的大右派
右派是有檔次的。只有達到某個檔次才有資格登上《人民日報》。
1957年8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鐵路工程技術界搜索右派,查處杜鎮遠是個反共專 家》。
本報訊:披著「鐵路專家」外衣的右派分子、鐵道部參事室參事杜鎮遠的醜惡面目,在幾次說理批判以後,已經完全暴露出來。
整風運動開始以後,杜鎮遠認為「時機」已到,一反常態,穿起西裝革履,大言不慚地吹噓自己擔任過二十年的鐵路局長,修建過好幾條鐵路,赴歐美考察過鐵路工程。污衊共產黨員「目不識丁」,說「不懂技術而當技術處長,不懂業務而當業務領導人」。杜鎮遠肆無忌憚地攻擊共產黨的團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說什麼黨對黨外人士一概不信任,黨和舊知識分子的關係是敵我矛盾。說什麼黨不得「不利用舊知識分子」是由於「黨擔當不起第二個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重任」。杜鎮遠把解放以來的八年,稱為「共產黨訓政時期」。他還狂妄到提出排斥共產黨員的要求,說「年老的、文化低的、體力弱的自請退休;有勞動力、文化低的,自請退款入學;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級較高的自動請求降級減薪。」
杜鎮遠的反黨社會主義言論,引起鐵道部廣大職工的憤怒。鐵道部工廠管理局長郎中騋、技術管理局副局長茅以新 (應該是『茅以升』之誤——李) 、設計總局副總工程師梅暘春、參事室工程師聶肇靈、技術局工程師塗允政、大橋設計事務所總工程師胡鏡銘等用許多令人信服的事實予以駁斥。梅暘春說:廣州解放後,我們只用兩個半月就修復了粵漢鐵路,而自稱「鐵路專家」的杜鎮遠呢?他在日本投降後參加修復粵漢鐵路,卻用了好幾個兩個半月;從武昌到衡陽,火車要走四天四夜。修復的英德大橋還出了毛病,斷橋,車翻,死了很多人。究竟誰不能領導科學?茅以新是杜鎮遠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激動地揭露了杜鎮遠的反動歷史。杜鎮遠擅長吹牛拍馬、鑽營奉承靠這些手段當上了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委員。杜鎮遠年青時,冒充四川省人,矇混住當時四川省當局,報送他官費入學。到1947年國民黨選偽國大代表時,因四川代表競選的人多,他又說他是湖北省秭歸縣人,當了湖北省的偽國大代表。他當杭江鐵路局長(後改為浙贛鐵路局)時,月支一千一百元的高薪,當了幾年局長,便蓋了好幾幢洋房。
1957年9月5日《人民日報》報導:《鐵道部反右派向縱深發展 原來隱蔽很深的右派分子不斷被揭發出來》。該文稱:鐵道部機關六千多人的反右派鬥爭正在以浩蕩的聲勢向縱深發展。「 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廣大群眾的認識普遍提高,絕大多數中間分子已經向左轉,特別是有些老年工程師在鬥爭中同右派分子劃清了思想界限,對群眾影響很大。如在鐵道部工作人員對右派分子杜鎮遠(參事室參事,曾任國民黨粵漢路局局長、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及偽國大代表)進行鬥爭時,技術局副局長茅以新工程師,經過幾天的反覆思考,打破了三十年老同事的情面,毅然參加鬥爭,理直氣壯地駁斥了杜鎮遠的右派言行,並揭露他的一貫反動立場。茅以新在參加論戰後,感覺到身心愉快,認識提高。基建局工程師郭浩然,材料局工程師馬家駒、工程總局工程師張逸人等都積極地參加反右派鬥爭,他們在批駁右派的時候,首先對自己的某些錯誤言論作了檢查。鐵道部副部長石志仁、設計總局總工程師林詩伯、工廠管理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郎鍾騋以及北京鐵道學院教授汪禧成等均在大會上對右派分子王北強、杜鎮遠等作了有力的批駁。 」
從這兩篇報導來看,杜鎮遠應當是鐵道部重點批鬥的大右派。《光明日報》透露了杜鎮遠的右派言論。他主張共產黨員幹部中「年老的、文化低的、體力弱的自請退休;有勞動力、文化低的,自請退款入學;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級較高的自動請求降級減薪。」因此被打成極右分子。有關杜鎮遠的右派資料,我估計在《人民鐵道報》或《人民鐵道》雜誌上能夠找到許多。那要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去找,我住在濟南,年已78,身患癌症,已經是不可能做到,只好表示一點遺憾了。
回到解放前,回到1957年,那時,在中國鐵路界,工程技術界,誰不知道杜鎮遠是一位赫然有名的重量級人物,所以需要動員茅以升等老技術專家出來口誅筆伐,以造成批倒批臭的聲勢,同時也是檢驗他們政治態度的手段,一石二鳥。
大陸易幟之後,蟄居香港養病的杜鎮遠,聽從了也是蟄居香港準備投奔中共的「雲南王」龍雲的勸說,回歸大陸,本想繼續報效國家,獻身鐵路,7年後,卻不幸墜落右網,而勸說杜鎮遠回國的龍雲,在回歸之後,同樣落難右阱。這或許是龍雲得到的報應。
二,杜鎮遠是繼「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之後的「鐵路巨擘」
杜鎮遠是個什麼人?《人民日報》以括弧注釋了杜鎮遠的四個頭銜:參事室參事,曾任國民黨粵漢路局局長、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及偽國大代表,除了第一個,都是指向政治立場反動。「參事室」是中共建立的一個高級政治看守所,讓那些沒有資格進入戰犯看守所的人有個吃飯的名目。「國民黨粵漢路局局長」的頭銜不在於「粵漢路」,而在於加上「國民黨」三個字的定語。第三個「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及偽國大代表」頭銜自然表明是個「反共專家」。這一注釋,說明這種人打右派也是命里註定的了。
在那個以政治標籤決定人的地位命運的時代,要打倒杜鎮遠實在是只需要一個指頭捏一捏,按一按。但其實,杜鎮遠非等閒之人。杜鎮遠是何許人?在「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1861——1919)之後,杜鎮遠被稱為「鐵路巨擘」、「詹天佑第二」。 這才是他成了鐵道部重點批鬥的右派的原因。
杜鎮遠湖北秭歸人。1907年6月,杜鎮遠考進了成都鐵路學堂。1910年7月,杜鎮遠進入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唐山路礦學堂,攻讀土木工程。在學期間成績優異,被遴選為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在唐山,他聽了孫中山的演講:「要中國富強起來,就需要修鐵路十萬英里,公路一百萬英里。希望大家努力向學,以身許國,承擔起歷史責任。」決心要獻身中國的鐵路建設。
1919年,被選中遠赴美國信號公司學習信號專科,第二年,他就進入康乃爾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碩士畢業並獲取學位後,杜鎮遠開始在美國德黑鐵路公司做助理工程師。1924年,交通部派杜鎮遠考察歐美各國鐵路號誌工程及材料,杜鎮遠率領考察小組,由美國歷經加拿大及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士、比利時、德國、前蘇聯等國。1926年回國,任北寧鐵路京榆號誌總段工程師。1928年,任南京建設委員會土木專門委員。
從1928年起,杜鎮遠就進入鐵路修建工作。他是繼詹天佑之後,自力更生修建中國鐵路的第二人。他曾擔任杭江、浙贛、滇湎和粵漢各鐵路局局長兼工程師,他在短短的數十年內就主持修建了3600公里長的鐵路、600公里長的公路。篳路襤褸,創業維艱。那正是抗戰臨近之前、之時、之後,中國處在日寇侵略、內亂頻仍之時,國力艱難,工業落後,資金短缺,困難重重,但他勇往直前,主持修築的多條鐵路成為中國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大動脈,貢獻大得很。
三,為滇緬鐵路嘔心瀝血不辭辛勞
本人由於寫作過滇緬鐵路工程師盛勝保(1914—1987)的傳記,到滇緬鐵路的路段採訪過,收集過相關的資料,因此對滇緬鐵路了解較多,因此以滇緬鐵路為例,說說杜鎮遠的情況。
雲南地處西南邊陲,境內都是高山巨嶺,大河深峽,交通極為閉塞,不過有一條法國人1903年修建的滇越鐵路,是一條軌距1米的窄軌鐵路,境內全長465公里,通向越南河內、海防,因此那年頭,雲南人要是到北京、上海,比較快捷的選擇,是先乘火車到海防去轉海船到上海、天津,直到抗戰初期,比如,調往雲南修建滇緬鐵路的人員,許多就是繞道河內進入雲南。有了滇越鐵路作榜樣,幾十年中,雲南人多麼盼望修建通向四鄰的鐵路啊!
1935年,時任交通部次長的曾養甫到雲南視察公路建設,深感雲南公路之少,路況之差,更不必說鐵路了。曾養甫是一位學者型的官員,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土木工程系,以後又留學美國匹茲堡大學,回國後,先後擔任廣東建設廳長、財政廳長、廣州特別市市長等要職,在國民黨政府中素以幹練著稱。1934年擔任浙江建設廳長時,發起和組織了興建我國最早的鐵路橋——錢塘江大橋,並擔任「杭(州)江(西)鐵路」 (後來延伸為「浙贛鐵路」)督辦,與著名鐵道專家杜鎮遠一起主持修建了那條東南長廊的大動脈。這年他來雲南視察時才38歲,正是精力充沛、思路敏捷的時候,他認為:雲南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自甘落後,應該充分利用有著4060公里漫長國境線的優勢,把鐵路和公路修到中緬、中印邊境,與國際交通線接通。英國人已把鐵路、公路從仰光修築到距離我國雲南邊境孟定鎮150公里的臘戍——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時,蔣介石曾三次飛臨臘戍視察地形,部署作戰事宜。
曾養甫隨即謁見雲南省主席龍雲,向他建議不但要加強公路建設,還要注重鐵路建設。當時處在抗戰一觸即發的時刻,蔣介石已有退守西南的設想。曾養甫告訴龍雲,要準備將西南建為抗戰的大後方,因此要著手籌建滇緬鐵路。
兩年後,七七抗戰爆發之後半個月,1937年7月23日,龍雲即向南京蔣介石請示,建議修建滇緬鐵路。電報云: 「南京委員長蔣鈞鑒。子密。國難當前,國防交通關係重要。承鈞座高瞻遠矚,主持於上,滇黔路已有端倪。惟由滇通緬鐵路亦屬國防要道,可否懇祈鈞座飭鐵部向英方商酌辦理,抑由滇先與緬政府商洽,視其意思如何,再為酌辦之處,祈核示遵。職龍雲叩。 漾機。印。」(雲南檔案館編號106-3-105/40)
過了一年,1938年9月7日龍雲再次請求蔣介石,修建滇緬鐵路。電報云: 「漢口委員長蔣鈞鑒:掃密。查滇緬公路現已完工,惟路線長,因雨水時有倒塌,刻正積極整理,然將來運輸力量甚微。若作主要交通, 非從速修築鐵道不可。擬請催促交通部,趕快工作,並將滇籍專門人才參用一部份於下級幹部內,以期情形熟悉,進行便利。雲近與省府同人及前勘界梁委員研究雲南出外海口,僉以為須從英緬方面設法,乃取光緒20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二十款閱之,發見其十二條所載,頗足引為出口根據。按其原文曰:『英國欲令兩國邊界商務興旺,並使雲南及約內中國新得各地之礦務一律興旺,答允中國運貨及運礦產船隻,由中國來或往中國去,任意在厄勒瓦諦江(即大金沙)行走,英國待中國之船如稅鈔暨一切事例,均與待英國一律。』等語。據此規定,則我國有在伊洛瓦底江行船通海之權,可謂最好之一出口也。茲已命外交特派員先向駐滇英領非正式提出,徵詢其意。我國現欲履行此項條約,看渠如何答覆。現職擬由騰衝修公路至八莫,因由八莫即可搭船到仰光,並擬由滇商與英商在彼合辦一輪船公司,以利航運。此關我國出海交通,至為重要,想鈞座亦所樂聞,尚祈即飭外交、交通兩部,根據條約與英使作進一步之商洽,以期早日觀成,何幸如之。謹以電聞,未諗尊意如何,乞示祗遵。職龍雲。陽。機。印。 」(雲南檔案館編號106-5-1860/5)
9月11日蔣介石復電
昆明。龍主席:陽機電悉。務密。已交外交、交通兩部核議矣。中正。真。侍參。鄂。印。
抗戰開始,急需通過緬甸運進軍用物資,因此首先修建滇緬公路。在滇緬公路接近完成的時候,於1938年4月成立了滇緬鐵路工程處。筆者在上海交通大學「林同炎展覽室」看到一本完整的《滇緬鐵路建築標準圖》,曬圖紙本,共63幅,應該是存世的孤本。我查閱了每幅圖的繪製時間,最早的一幅是1938年9月4日,全線規定的開工時間是12月25日。可見準備工作做得很早。我從雲南檔案館查到的資料,下面提到的14總段總段長陶述曾的到任時間是1938年9月。由此可見,建立機構,調配人員、制定規範等等各項準備工作,在龍雲與蔣介石的正式請示批准之前就開始了。
滇緬鐵路全長860公里,以祥雲縣為界,其東為東段390公里,其西為西段470公里。按照地形而言,崇山峻岭深峽河流大多在西段,而且這地區完全沒有公路可通,因此其艱難險阻,為測量施工帶來了巨大的困難,遠遠超過了所有以往修建的鐵路。
盛勝保所在的14總段,在今南澗縣公朗鎮,是滇緬鐵路地形最複雜的兩個地段之一。公朗鎮地勢低洼,看《南澗縣誌》,公朗鎮的縱剖圖好像處在井底,站在公朗鎮看山有壁立千仞的感覺。從公朗鎮往東北出去,40公里之間,落差有1000米,從公朗鎮往南到瀾滄江,沿公郎河,13公里之間,落差有614米,而在瀾滄江口,矗立著一座筆直筆直好像竹筍挺立的高山瓦朗山,相對高度為1523米,堪與泰山比肩。據帶路的鄉民說,山頂上有一棵直徑3米的紅木樹,隱然可見。筆者兩次到公朗鎮走訪,第二次還有縣政協主席董德海等同志陪同。經鄉民指引,在海拔2000米之上,還尋找到遺留的大段路基明槽以及大量的其它遺蹟。當年,這一段的測量工作由14總段負責。總段長陶述曾(1896—1993)因為領導有方,使線路的測量設計科學合理優越,被譽為「陶氏線」。陶述曾解放後出任湖北省水利廳長、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民革湖北省主委。
1940年3月,陶述曾的總段要調到今耿馬縣的孟定鎮——當時由孟定土司執政。從公朗鎮到孟定鎮大約有三百多公里,沒有公路,必須沿驛道步行。盛勝保率領了120人的職工隊伍,加上67匹馬和4架滑竿,走了16天。路途中,白天要架鍋做飯,夜晚往往要露宿。其間遇到的艱險困苦,一言難盡。
杜鎮遠於1938年5月被任命為滇緬鐵路工程局局長兼總工程師。他是臨危受命,義不容辭。在修建浙贛鐵路、湘桂鐵路當中,他和曾養甫、茅以升都是配合默契的搭檔,表現出他卓越的才幹和創造精神,因此,這次是被曾養甫大力推薦而來。
滇緬鐵路是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投資修建的最大工程,任務重,時間緊。杜鎮遠作為領導人,他首先需要了解全路的地形、地質、水文、氣候、村落分布、民族聚居等情況。
他在1940年5月起,帶著一批專家、技術人員,用了51天時間,從祥雲、彌渡、南澗橫渡瀾滄江進入如今臨滄地區的雲縣、臨滄、鎮康(包括如今的永德)、耿馬,直達中緬邊界的清水河口岸並去往緬甸的滾弄,對沿途的山林、河流、村寨都逐一勘察。這條路線共約600公里,正是盛勝保他們步行走過的路線。60年後,我乘坐汽車也走過(國內部分)。邊疆的五六月間整天大雨傾瀉,山林都陷於潮濕、泥濘的雨霧迷茫中,他們行走的又多數是連窄小的驛道都沒有的深山野嶺,和無橋可渡的大河小溪,有時因為山嶺太陡、樹林太深,馬匹也不能使用,過河時只能乘坐那在水浪上輕如一片葉子般的獨木舟,夜裡或露宿於山野或投宿於少數民族的竹樓上,吃不上熱飯啃點乾糧是常事。這年杜鎮遠已年過半百,長期從事艱難繁重的鐵路建設,早就患有嚴重的糖尿病、肺結核,但他像許多專家學者一樣,都是以事業為重,並不因為多病之身而有所畏縮,還是不辭勞苦地一道山嶺又一道山嶺走下去,仔細地觀察分析,與專家們商討施工中可能遇見的問題。……
那時,雲南邊陲地區,所有的道路都是土質驛道。全年氣候大致分旱季雨季,5月份進入了雨季。雲縣、耿馬一帶又是瘧疾(當地叫瘴氣)高發地區,傳染性極強,死亡率很高。當地民諺曰:要去孟定垻,先把婆娘嫁。雲縣家家有死人,有的人家死絕,真是「萬戶蕭疏鬼唱歌」。老百姓談虐色變。身強力壯被稱為「大力士」的盛勝保也沒有逃脫瘧疾。陶述曾一次病倒於途中被一位美國軍醫救了命。陶述曾的20總段100多人就死亡31人。在孟定,他招的2000名工人,死了1300餘人。杜鎮遠不顧自己的疾病,前往孟定勘察,那是需要多麼巨大的勇氣和犧牲精神!
為了籌集建設滇緬鐵路的資金,1941年,杜鎮遠還親自前往美國,會見了美國的軍事、外交、財政部門的官員,向他們陳說修建萬山叢中的滇緬鐵路,缺少資金、器材的困難。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的精神感動了美國朝野,最後羅斯福總統批准給予專項貸款1500萬元。杜鎮遠把這一筆錢在美國全部購買了築路工具與鐵路器材。
但是,滇緬鐵路在路基基本修好之後,日軍進入緬甸,鐵路只能半途而廢。
四,回歸大陸,熱情歡迎
杜鎮遠這位鐵道功臣,在「滇緬鐵路」夭折後,張群曾約請他出任四川建設廳長,他鍾情於鐵道事業,力辭不就,被調任粵漢鐵路管理局長,在抗戰勝利後,搶修重建了這條全長1300餘公里貫通華中南的大幹線,以後又擔任了「武漢長江大橋籌建委員會」的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因為多年奔走於鐵路工地積勞成疾,又看到風雨飄搖面臨崩潰的國民黨政府已難以做成什麼事,在1948年4月辭職移居香港養病;1949年春夏,一些曾為舊政權服務過的人,惶然逃往海外之時,那些對他的修建鐵路公路專長很是賞識的國民黨政府高層官員們,又想起了杜鎮遠,不斷通過各種渠道勸說他去往台灣「歸隊」,他卻引領北望關注著人民解放事業的進程,為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欣喜;回想自己從美國留學歸來後的這幾十年,費盡移山心力艱難地修築過許多條鐵路,有的是通車不久就被敵人侵占,如浙贛鐵路、湘桂鐵路,有的是還未修成就被破壞,如「滇緬鐵路」,這都是國民黨政府腐敗衰弱之故;也使他深深感到,政治是影響著工程技術人員的前途,自己雖然身懷絕技又滿腔熱情,可是生不逢時呀!如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了新中國,自己也該擇善而從了!
他這一心願,得到當時也避居香港對他的學識才幹很了解的龍雲將軍的支持,極力鼓勵他擺脫其它纏繞返回大陸,而且答應為他向中央領導人介紹。1949年12月,和共產黨已經暗通款曲長達10年的龍雲返抵北京,他與當時去車站接他的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略事寒暄後,就極力推薦杜鎮遠,說他是位難得的鐵路人才,董必武欣然表示:「建設祖國是大家的事,高級技術人才我們更是感到缺乏;杜先生願意回來,我們熱烈歡迎。」以後就由當時擔任第四野戰軍鐵道兵司令員、負責接管粵漢鐵路局的郭維城將軍,派出與杜鎮遠有舊、解放後仍然留任粵漢鐵路管理局副局長的劉傳書去香港看望杜鎮遠,洽商接他回北京的事。
杜鎮遠很是興奮,終於能如願以償了。1950年5月,他抱著為新的中國鐵道事業貢獻力量的巨大熱忱,帶著全家人返回北京。
當時的港英當局與國民黨沆瀣一氣,極力阻撓從香港回國的人士,他們聽說杜鎮遠全家將離港,以為這個當了十幾年鐵路局長的人,一定家資萬千,以「有人檢舉你攜帶了大量黃金出走」為理由,派出軍警在羅湖橋那一端把杜鎮遠扣留並對所帶行李進行搜查,但除了簡單的衣物和書籍外卻沒有一兩金子,這使他們很失望也不能再扣留,只好放行。
過了羅湖橋踏上五星紅旗飄揚的土地,杜鎮遠這飽經磨難的老知識分子,感慨萬千地流下了眼淚,總算向舊的世界告別了!
初到北京,他頗受禮遇,陳雲、薄一波以及鐵道部正副部長滕代遠、呂正操都接見了他,並安排他為鐵道部部長辦公室顧問。這雖然不是具有實際權力的職務,也正適宜他這多病之身,對新的社會還陌生的人;他也願意先加強政治學習了解革命形勢,再進一步發揮自己一技之長,但不幸的是「左」風已在悄悄漫延,他卻被鐵道部某些人看做不可信任、需要改造的舊人員。回到北京後,他除了在1951年年初隨「中蘇鐵路專家考察團」去西安至蘭州的鐵路線上視察過一次幹線塌方滑坡的情況外,幾乎沒有再參與鐵路建設的實際工作,接著在那年10月被分配到四川參加土地改革運動,讓他在運動中加強思想改造和階級鬥爭觀念,一去半年。1952年3月因在鄉下勞累過度,糖尿病加重返回北京,從此更不能工作。
五,年近古稀,右帽加冕
他1950年春回國時,早過了花甲之年,但想到戰亂已經過去,國家急待振興,未來的川滇、滇黔、滇緬等鐵路都可以讓他大顯身手,所以他的熱情很高,但他並沒有想到,他雖然積極地投身於一個嶄新的充滿活力的新社會,遇見的卻是一些對他並不了解,又恰恰能左右他的命運的人,這些人不懂業務也就難以器重他,還對他產生種種偏見。1957年他發表了一番耿耿忠心的建言,到1958年他已是耳聾眼花的69歲高齡,還被補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此他更是與鐵路無緣,只能在家閉門思過,眼耳之疾防礙他不能動筆,就每月口授請人代筆寫思想改造匯報。他抱著真誠改造自己的赤子之心,一月一篇整整寫了3年。對於一個垂暮的老人這3年是何等精貴,如果讓他進行有關鐵道建設的回顧與研究,以他的學識和豐富的經驗,要寫出多少有見解有質量的論文!
直至1961年他積鬱去世的前3個月(1961年9月)才摘去「右派」帽子,用當時的流行術語,總算沒有帶著花岡岩腦袋去見上帝。但「文革」一來臨,他雖然已去世多年,那些「造反派」還是不肯放過他,也以為他在舊中國從事鐵路建設幾十年,一定搜刮不少,兇狠地抄了他的家。但只抄出幾塊舊錶,幾件舊銀飾和2500元人民幣。這2500元還是他1961年去世後,鐵道部發給的撫恤金。他的清廉既令「造反派」失望,也令這些人難以思議。
那動亂的年月,鐵路建設並沒有完全停歇,還在時緊時松地進行,可是那時候有誰會想起杜鎮遠呢! 」
1979年12月,他去世後的18年,他的錯劃「右派」問題終於得到改正,恢復名譽,骨灰改葬於北京八寶山公墓。20世紀90年代初,原鐵道部長呂正操曾深情地撰文稱讚他: 「杜鎮遠先生是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我國鐵路的偉大建設者。」「其一生愛國報國,將畢生精力貢獻給祖國鐵路事業的博大胸懷足為後世范。」1989年他誕生100周年時,他的家鄉湖北秭歸縣隆重紀念了這位中國鐵道建設先驅,出版了紀念文集,並集資為他塑造了銅像,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特意為「杜鎮遠圖書館」題字。他故鄉的人認為,秭歸幾千年有記載的歷史,只出現過3個偉大人物,屈原、王昭君、杜鎮遠。這使這長江邊的山城人民引為驕傲也深感哀傷,怎麼他們的命運都是那樣悲慘?
六,歷史的回眸與反思
杜鎮遠回來後——恕我不用「回國」二字表述,因為這哪裡是他的「國」啊!30年前,才華卓異的作家白樺寫了一部電影文學劇本《苦戀》,隨後根據這部劇作拍攝成的電影《太陽和人》卻受到嚴厲的批判。電影寫海歸畫家凌晨光被摧殘得家破人亡的遭遇,通過畫家凌晨光女兒之口提出的『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句尖銳的問話,表達了作者對打擊鎮壓知識分子的憤慨。杜鎮遠的遭遇令我們要再次發問:「您愛我們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
中共派出與杜鎮遠有舊、解放後仍然留任粵漢鐵路管理局副局長的劉傳書去香港看望杜鎮遠,洽商接他回北京。他回到北京後受到那麼多高層領導人的歡迎和接見,陳雲、薄一波以及鐵道部正副部長滕代遠、呂正操都接見了他,並安排他為鐵道部部長辦公室顧問。顧問雖為閒職,但名目也還好聽。我想這都不是虛情假意,畢竟開國伊始,中共缺少鐵路方面的高級人才,軍運民運大量要依賴鐵路,像杜鎮遠這樣頂尖級的鐵路官員,能夠投奔共產黨,更是表明共產黨能夠收攬人心,求之不得!但是,就共產黨而言,這是一個農民造反的政治集團,在高層也有一批領導人,其科學文化水平極低、心胸極為狹隘、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從國民黨那邊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總是存在著懷疑、藐視、嫉妒的心理,在政治上不信任。那時,在革命隊伍中,對於任用國民黨的官員,有一句流行語: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所以這批農民革命幹部對於反右運動打心底里歡迎、擁護,批鬥右派正投合他們的期望。
杜鎮遠主張老幹部中「年老的、文化低的、體力弱的自請退休;有勞動力、文化低的,自請退款入學;有文化、有能力而薪級較高的自動請求降級減薪。」這正戳破了他們的肺窩。這些幹部最自負的是「咱是大老粗」,最自卑的也是這個「大老粗」。這樣的幹部在初級、中級、高級各個層次上都有。他們中文化水平最低的要進掃盲班,從識別自己的姓名開始學習。杜鎮遠的這個「右派言論」,還不會叫他們群起而攻之,置之死地而後快。
1952年部隊運用一位文化教員戚建華發明的「速成識字法」,開展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筆者那時在華東軍區後勤部工作,分配了一個業餘任務,一對一地教部長鄺任農(後來調任民航總局局長兼空軍副司令員,授中將銜)的個人炊事員。那是一位大約四十幾歲的老同志,享受營級幹部待遇,但卻是文盲。其實,現職的幹部中,各個級別的都有文盲或半文盲。在鐵道部機關和下面,這種情況也不會罕見。
杜鎮遠在滇緬鐵路任局長時,哪能容忍錄用這種人員!滇緬鐵路聚集了當時全國最優秀的鐵路技術人才,一點也不含糊,差一點也不將就。那個時候,滇緬鐵路用人在招聘和提升方面,要按章辦事,鐵面無私。曾養甫更嚴格。盛勝保在信中說起曾養甫:「他辦事是厲害的。」許多來頭比他大的人向他推薦人員,他都敢頂,毫不留情(詳見《滇緬鐵路祭》)。在當時,尤其在鐵路,曾養甫是個有口皆碑的人。他當浙江省建設廳長的時候,聘請了茅以升做錢塘江大橋工程處處長。他對茅以升說:「技術和人事歸你負責,籌款歸我負責。萬一大橋出了問題,你先跳錢塘江,我隨後跟著你跳。」
國民政府的工程技術人員職稱系列是:工程學生、工務佐理員、工務員、幫工程師、副工程師、正工程師。「師」字又寫作「司」。幫工程師相當於現在的助理工程師。盛勝保於1934年畢業於天津中法大學土木工程系,到1940年滿6年,提升為幫工程師,也不算破格。他給遠在天津的戀人邵芳寫信道:
我在到了孟定後,我的上峰——二十總段長姓陶——就呈請提升我的職位,那時經最高機關的審查,說不行。大概是因為我畢業的年限不久,我又年輕,學校的牌子不硬不成系派,我沒有後台,又不會活動。隔了一個月又第二次保舉並解釋應該升的理由,結果還是不准。第三次陶公為此辭職說:「與其不能取信於下屬,還不如不干。」局中恐失去人心,終於批准了。
滇緬鐵路的技術人員,留在大陸的人,解放後不管是否在鐵路,都是響噹噹的人才。試舉數例:
汪菊乾,工程師兼工務科長,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解放後任鐵道部副部長;
雷從民,工務科技術主任,美國康奈爾大學工程系碩士,解放後任西南鐵路分局副局長,鐵道部第一設計總院總工程師;
趙祖康,公路工程處總管理處處長,唐山交通大學畢業,解放後任上海副市長。
林同炎,滇緬鐵路橋樑課長,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碩士,後來去了美國,是享譽世界的建築大師。
薩福均,美國普渡大學畢業,解放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副部長兼西南鐵路工程局副局長,鐵道部參事主任;
程孝剛,機械總工程師兼機務處處長,解放後任交通大學教授,副校長,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茅以升,技術委員會委員,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專業碩士學位,中國著名的橋樑專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要舉例,是舉不勝舉。雲南作家彭荊風寫道:當時,由於中國軍隊在華北、華東、華中南的節節敗退,全國總長11500公里的鐵路,有9100餘公里淪於敵手,那些鐵路上的專家,在曾養甫、杜鎮遠的邀請下,紛紛奔來雲南加入了「滇緬鐵路」的修建。如張海平、汪菊潛、雷崇民、陶述曾、夏舜參、龔繼成、吳祥祺、王節堯、朱葆芬、顧彀成、張袚、李躍祥、祝秦萱、周庸華、關榮柏……幾乎全是畢業於歐美名牌大學專攻土木工程或鐵路建設;還有醫學專家張孝騫、應元岳、龐從周、孟慶華、陳又新等等;他們無論在舊中國和新中國都是科技、醫學界享譽中外的泰斗。
滇緬鐵路的技術人員,沒有留學經歷的,也幾乎全部來自北洋、北大、清華、復旦、同濟等等名牌大學的土木工程專業或鐵道專業。當時建築滇緬鐵路,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保存、鍛鍊鐵路技術人才,以備抗戰勝利後國家的復興與建設使用。1949年易幟之後,中共急於修復鐵路並建設新線,如果沒有這批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優秀的鐵路技術人才,參與其事,那會是一籌莫展。從中共來說,為了軍民運輸的需要,也比較重視鐵路,所以對於接收的國民黨鐵路方面的「舊人員」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是到了1957年,經過七八年的鍛鍊,共產黨的老幹部已經初步掌握了鐵路技術,這時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對於那些一向不信任、也看不慣「舊人員」的老幹部,特別是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幹部,正對了他們的心意。他們成了反右運動的積極分子。杜鎮遠耿耿忠心,直言快語,被打右派就成了他的宿命。
這正應了共產時代的口頭語:新舊社會兩重天。在舊社會,杜鎮遠當局長,可以任人唯才。到了新社會,他當了「顧問」「參事」,僅僅建言「大老粗」幹部要學習文化,就打了他的右派。
筆者寫作本文時,適逢蘋果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的賈伯斯逝世。中國知識界在哀悼震驚之餘,議論紛紛。網易的總欄標題是「改變世界的天才賈伯斯」。雖然中國學者紛紛質問:中國為什麼出不了賈伯斯?其實,中國也產生過一位「改變中國的天才」,他叫毛澤東。他多麼厲害啊,把中國的知識分子整得服服帖帖,俯首低眉,成為馴服工具,至今也站不直腰,抬不起頭,徹底喪失了「不淫、不移、不屈」的人格操守和精神氣質。至今共產黨對於異議人士的打壓也達到得心應手、爐火純青的水平。毛澤東改變中國知識分子可分為三部曲:第一部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第二部叫反右派運動,第三部叫文化大革命。從此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越少越光榮,張鐵生因為交了白卷而一舉成聞名全國的英雄。像杜鎮遠這樣不服「大老粗」的舊人員,打右派就成了必然的歸宿。把知識分子改造得馴馴服服、把中國社會改造得翻天覆地,難道毛澤東不配稱為改變中國的天才嗎?唯一不幸的是,按照托夫勒在《權力的轉移》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3個階段:暴力社會、財富社會和知識社會的歸類,當世界歷史的腳步,跨進知識社會的時候,毛澤東卻在中國開展反右運動,把知識分子徹底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反右運動真不愧為他的大手筆,驚天動地,亘古所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