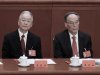他是湖南人,大約一米九的個頭,父親是地下黨,有著鮮卑族血統;他好酒,一斤原漿下去,富有磁性的清口朗誦一字不差地湧出《將進酒》或《蜀道難》;他主張吵架,鼓勵創新,提倡把事情擺在桌面上解決。四人團中,他是唯一實名微博並活躍發言者,觀點從不激進,常以通俗的比喻闡述立場。
熟知他的人,均對這條簡訊中的兩個「啊」字表示意外,因為這與他一貫的應急不太相符。他太鎮定了,也太有氣場了。也許,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我無言以對,只是簡要回覆:「這些都是鐵證,之後會低調處理。」
在財訊傳媒20多本雜誌中,《財經》顯然是老闆們最為操心的,而我似乎又是《財經》最愛折騰的。「不折騰」曾出現在中國元首的演講中,翻譯版本不一而論,如「don’t make trouble」「don’t flip flop」「don’t get sidetracked」,或「no dithering」「no major changes」,缺乏公認的信達雅譯法,以至於官方索性音譯「buzheteng」。後來中投公司監事長金立群提供了一個經典版本——「don’t rock the boat」或「no boat rocking」,直譯「別晃船」。
「《財經》就是一條船,大家要齊心,不能把船給弄沉了。」這是小京時常提到的一個比喻。每臨大事,他好比一個參加完家長會的父親,要跟孩子談心。我們的談話多數在酒桌上完成,一部分在他的辦公室。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儘量迴避這種越級。
安元鼎事件中應對警察上門的當晚,正是他坐鎮辦公室,親自將四人警號發給一名委座的近侍,事情出現根本性扭轉。這樣的政經人脈資源,確非其他內媒可以比擬。我曾安排記者譚翊飛、魯偉調查勝景山河IPO造假,紮實的報導成為這家湖南岳陽黃酒企業的上市滑鐵盧,老家托盡關係找到小京,最終,他都未開口要求我撤稿。
一次談到財訊傳媒的這些雜誌,他說:「對我來說,這是business。」但他又提醒我:「你是新聞人,你不能這麼想。」針對我舉報劉鐵男一事,他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說:「這是他的權利啊。我不支持也不反對。」同樣的表態還在他活躍的幾個高端圈子裡流轉。
在我關機的那個晚上,小京發來兩條簡訊:「明天見個面?」「中午或下午你定。」直到第二天凌晨開機,我才收到並回復。
我們的午餐選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包間,就兩人。氣氛遠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緊張,關鍵是每感緊張的時候,他能通過恰當的方式化解。很難想法,換一家機構我會遭遇什麼樣的下場。這種寬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於他們大風大雨的經歷。
誰沒年輕過呢?1989年的那個春夏之交,前途無量的他走上了街頭,換來看守所的艱難一夜。「湖南人吧,都會找一種歷史存在感。」他笑著說。那次衝動顯然讓他的人生拐了一個急彎,王所長將他介紹給了波明,自此成為聯辦的主事者之一。後來,王所長成了王省長,成了王市長,成了現在的王書記,從未忘記對這位老部下的關愛,不固定來電約酒,交流一本好書,甚至邀他復出。
這頓午餐,小京主要想了解舉報的來龍去脈,他料到王書記回國,第一時間會把他叫過去。我們還花了一點時間來梳理劉鐵男的背景,但當天沒有找到答案。末了,我忍不住在反問中加了一點私貨——
「岐山書記真是微博的潛水員?」
「他現在哪有這個時間!」
……………………………
位於東二環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廈,聯辦買下了幾層樓。在王波明雜亂簡樸辦公室的斜對面,是一間置有長形圓桌的會議室。他把一米八的身體窩進靠椅,雙腿搭在圓桌上,後背將靠椅壓到接近圓桌的水平,指間煙霧繚繞。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胡舒立說服《財經》雜誌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爐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全。被釜底抽薪的聯辦,決定為這場罕見的集體跳槽做內部說明。但對與會的《財經》記者編輯而言,聯辦強硬的書面回應及波明式會場姿態,與站在道德置高點及作為新聞標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鮮明對比。
這裡給外界的印象,有著貴族氣質,略帶國企特徵。像程益中、楊斌、王小山和我這類草根新聞人,在離開《新京報》後相繼轉投聯辦,一度難於適應。僵化的集團行政要求員工必須正裝,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褲衩視為另類,集團行政前來檢查,同事幫忙圓場:「這人是來送快遞的。」
其實,外交官之子向來自由散漫,一名下屬王安在書中描述他:「只要不是正式場合,王從不打領帶,在沙發上全無坐相,必蹺二郎腿,必一會兒就出溜下去,然後再頑強地挺上來,循環往復,樂此不疲。」他逃避紐約交易所的高薪生活,放棄中國證監會的仕途機會,舒立走後寫下唯一一篇被業界存照的署名社論:「我們不但要自覺地迴避被商業利益影響和侵蝕,更要抵制施加於我們身上的不當管制。」他討厭一切有形無形的束縛,包括女人。
1998年,胡王走到一起,準備辦一份雜誌。舒立提出了兩個條件:永遠不能干涉她的編輯部,並且提供一份200萬元的採編預算。雙方一拍即合。別看現在的《財經》是一頭現金奶牛,「可在1998年,兩三年沒廣告,我說養著。」波明回憶。
早年,雙方對「名利」有清晰的界限,新聞人除了國內一流的採編費用,坐擁享譽國際的「名」;投資者則拿走年均六七千萬的「利」。但與《財經》的時代貢獻相比,這點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從《基金黑幕》到《銀廣夏陷阱》,從《SARS何來》到《誰的魯能》……毫不誇張地說,《財經》的尺度就是中國媒體的最大尺度,亦是獨立思想與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
以銀廣夏為例,這家上市公司獲得多名領導人的視察並讚許,加之保薦人又是胞兄王東明所在的中信證券,王波明擔心報導可能導致《財經》關門,或胞兄公司重大損失,於是電話求助王岐山:「報導絕對真實,但會帶來政治上的影響。」對方答覆:「如果是真的,就出吧。」甫一報導,銀廣夏股票及其高管命運雙雙「跌停」。
從這一點上講,波明與小京均有難能可貴之處,即很少干預編輯部工作,尤其是不派題、不審讀,以真實性作為決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標準。跟小京的精彩脫口演講不同,波明需要有書面發言,否則就像失韁的戰馬。他偶爾會流露自己對新聞的理解,並回憶在唐人街給《中華日報》打工經歷,體會「無冕之王」的快感。這就好比一名老婦人不斷重複自己年輕時有多漂亮。
波明的人脈縱橫交叉,命運跌宕起伏,比如父輩同遭迫害時的同居發小如今已經登上權力之巔;兒子的母親是一位冤死國家元首之女……他的矛盾之處還在於,今天跟美國總統同台指點江山,明天又要親自面對一名宣傳處長的訓斥。
當然,也很難找到像舒立這樣的敬業者,每一則報導都在修正她對籠子尺度的計算,更重要的是,她能將聯辦所有的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以新聞專業主義發揮到極限,以至於12年之後她強大到足以與投資人叫板,索要七成的股權及「三位一體」的職位。
文人、商家與政客的混合特質,決定了這宗買賣不可能成功,最終成了決裂。
程益中曾對《紐約客》說,孫志剛事件是對警察權的部分否定,而《財經》的話題沒有影響到根本的統治體制,「因此它相對安全。我不是在批評胡舒立,但《財經》在某些方面是在為一個更具權力或一個相對更好的利益集團服務。」
承認體制權威,然後謹慎監督它改良它,這種策略決定了《財經》的過人之處,也意味著它的局限性。胡舒立以比喻回應:《財經》是一隻啄木鳥,不是為了把樹擊倒,而是為了讓它長得更直。
在胡王決裂之時的一天,法滿帶著我跟波明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長談,他說這是第一次完整講敘事情的來龍去脈。這次談話使我做出了留守《財經》的決定,切合楊海鵬對我的勸說:「中國能造飛彈的記者很多,而能提供飛彈防禦的媒體很少,聯辦無可替代。」
其實廢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為艱難。當數年後《公共裙帶》《連氏無間道》以及安元鼎、馬三家等陸續問世,我更堅信一點,程益中的話不全對——安元鼎、馬三家這類報導不會發表在以前的《財經》,這本雜誌的DNA不全是胡舒立,更有關王波明、戴小京。
在舉報劉鐵男的那個下午,未接到的巨量來電包括波明的一個,有人帶話要我去找他。我在15時56分發出一條簡訊,未見回復,於是打電話做了說明。他沒有表現出任何責備之意,只是問,證據可不可靠?這是他一如既往關心的核心要點——不怕闖禍,但怕丟人,報導的東西再敏感,只要證據夠硬,他能找到解釋的理由。
掛掉電話之前,他都沒問我的動機。當天晚上,正是《財經》年會慶功宴,據同事後來描述:波明端著酒杯在人群穿行,然後不斷地說:「太大了,這事太大了!」「怎麼還有這樣的玩法?」
有人將他們稱為「新聞玩票者」,或許更準確的表述是,他們介於體制內與局外人的邊緣,置於家國變革與擁抱世界的中線,並努力充當溝通者和翻譯者。我更感興趣的是,當他們兩鬢泛白之時,少小玩伴與早歲同僚當處軸中之日,他們是否還記得初心?能否接受批評與監督?會否固為更強大的既利集團?
一個劉鐵男,一塊驗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