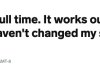2015年我畢業後,不顧父親反對,孤身一人來到成都。
那時,成都之於我,算得上是個夢想了——或者可以說,在我那時的認知里,成都才等於是生活。
來的時候是11月,有霧。出了車站,我站在街道上,看著遠處的青瓦平房和國際商業中心以一種奇異的和諧感隱在一片霧氣中,仿佛整個城市的溫柔都在一瞬間包裹住了我。
當我以扛著大包小包的姿態出現在這個城市時,也意識到一件更狼狽的事——父親一怒之下斷了我的經濟來源,而我全身上下只剩900塊了。我不清楚成都的生活成本有多高,但毫無疑問,這點錢肯定不夠安身立命。
不夠立命,那便先暫且安身罷。
幾番輾轉,我找到一家私人房屋仲介,說清了自己對租房的一些基本要求:交通方便,生活便利,壞境安靜,且最多能接受「套三」的單間。
仲介問我:「長租還是短租?」
我答:「短租,一個月。」
他又問:「心理價位在多少?」
我猶豫著答:「……不超過900吧。」
仲介用一種「你是不是沒進過城?」的眼神在我身上來回逡巡,末了,拿起一串鑰匙從椅子裡坐起身來:「行,你先跟我去看看房吧。」
我點點頭,趕緊跟著他上了電瓶車。到了地兒一看,我就傻眼了。
成都向來有「東窮西貴,南富北匪」的說法——仲介帶我去的房子在東三環外,地段很偏,交通不便,甭說地鐵站了,連個公共汽車站都不見影兒。上樓後進屋一看:不足70平的小戶型,居然被巧手的仲介活活隔出了五室一廳一衛一廚,其餘4個單間都已租了出去,只剩下最左邊的一個小臥室,大約7平,一張床一個衣櫃就占得滿滿當當,轉個身都費勁。
我去廚房看了一眼,水池裡泡了七八個油膩膩的碗碟,燃氣灶周圍的油污積起來有一指節厚,各種花椒粒、胡椒粉七零八落地散在操作台上。廁所就更別提了,剛走到門口,一股凌冽的生命氣息就撲面而來,熏得人打怵,探頭看去,泛黃的天花板上正滲著水,馬桶壁上的污漬半黃半黑,更打腦殼的是,下水口處還有一團髒紙巾,在水面上飄蕩,像是糟糕透頂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仲介轉頭問我:「你覺得房子咋樣?合適的話就趕緊租了嘛。」
我說你等我緩緩,然後木然地坐在客廳凳子上。就在我發呆的空檔,其他幾個臥室里的租客陸續出來或做飯或洗衣、上廁所,我粗略數了下——就這一會兒就出來了七八個人。
我疑心自己看到了薛丁格的房間,愣了愣,轉頭問仲介:「這個房子不是『套五』的嗎?」
「是啊。」
「這好像不止4個人。」
「是啊。」仲介不耐煩地看了看我。他這兩個「是啊」說得這般理所當然,讓我完全沒了繼續問下去的勇氣。
見我不吭聲,仲介抬手看了看表,有些急躁:「那你到底租不租嘛?」
我苦著臉跟他抱怨:「大哥,我雖然急著租房,可你這房子也忒……那啥了點兒吧,這完全是避開了我所有的租房要求啊,我就不說那廚房那廁所了,光這臥室也太小了吧,轉個身都不行,還有這室友,這『套五』的房子怎麼住這麼多人吶……」
仲介大哥一個眼神冷冷劈了過來,震得我立即止了話頭:「小姑娘,你可能剛來成都不懂行情,跟你說個老實話,我給你找的這個都算是不錯的了。你出去打聽打聽,這地段的電梯房對外出租是啥價位?你想找個人少的房子,那價格肯定也就上去了,你這又是短租又沒多少租金,咋可能租到『套三』的單間?」
這番話說得毫不客氣,我被臊了個滿臉通紅,只好問道:「好吧……那這個單間多少錢?」
「900,押一付一。」
那總共就是1800?我心裡一涼,也顧不得嫌棄這兒條件惡劣了——我這點兒錢哪有嫌東嫌西的資本,今晚能不睡大街就不錯了。我只好腆著臉跟仲介講了半天價,好說歹說,總算免了我押金,房租也只收了850。
收好了錢,仲介遞給我兩把鑰匙,囑咐我「別弄壞臥室里的東西」,然後就走了。隔壁不知幾號房傳來震耳欲聾的搖滾樂。我強迫自己忽略發霉的床墊,一邊把被褥拆出來鋪床,一邊給自己打氣:出來混的,自然得隨遇而安,要是嫌這嫌那,哪兒還有闖蕩社會的膽氣?
2
然而,我這點兒膽氣很快就泄了個乾淨。
住進出租屋的第一晚,初到異鄉的孤獨感裹著四川盆地特有的濕冷,直往我骨頭縫兒里鑽,即便我把被子和幾件大衣通通壓在身上,還是冷得打顫。迷迷糊糊睡到半夜,突然被什麼東西咬醒了,開燈一看——幾隻跳蚤正在吸我的血。
我頓時嚇得瞌睡全無,拍掉腿上的跳蚤後,身體已經不受大腦指揮一樣從床上彈射到房門邊兒,整個人恨不得都嵌進門裡去,不敢再靠近床半分。
在門邊蹲了小半晚,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開始思索一個更嚴峻的問題:現在,我全身上下只剩50塊了,該怎麼活?越想心越涼,又掏出手機,把微信、支付寶里的零錢全湊在一起,好歹多出來十幾塊錢。
就這多出的一點錢,竟讓我樂觀起來:最不濟,也能多撐兩天了。
反正廚房髒得沒法做飯,接下來,我每天早上買上4個饅頭,早上吃一個,剩下的塞包里當午餐和晚餐,這樣下來,一天的餐費也就4塊錢。
有時實在饞得慌想吃個紅豆麵包,站在麵包架前踟躕半晌,都無法下定決心。店裡的老闆總不住地往我這邊打量,眼裡的警惕和鄙夷十分赤裸,叫我想忽視也不行。我先是有些羞赧,又覺著有些難過,到後頭乾脆起了氣性——我還就不買了!直接昂頭挺胸出了商店。
但光吃饅頭也不行,我擔心自己低血糖發作,便買了袋最便宜的水果硬糖,頭暈時含上一顆,待甜滋滋的添加劑在舌尖蔓延開,我才好歹在這日子裡咂摸出點兒甜味來了。
吃了半個月的饅頭,一家一家地去醫院人事部毛遂自薦,我總算在餓死前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家不怎麼樣的民營醫院,工資每月1268塊,幸好包吃包住,至少能讓我從群租房逃離出來。
我扛著行李滿心期待地住進了醫院的「集體宿舍」,可現實又一次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宿舍總面積不超過30平,進門兩側,先是分別隔了兩個單間出來,據說是給醫院兩位女醫生住的「VIP房」。其餘的公共面積也絲毫沒有浪費,緊挨緊湊地擺了12張上下鋪,給24名護士睡。廁所在外間,兩個蹲位,一個簡易淋浴室。
整間屋子唯一的優點是坐北朝南,採光相當好——全屋8扇窗戶,卻連一面窗簾都沒有——看來這家醫院的經費確實夠緊張的。
「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可既然走到了這一步,斷然沒有退縮的道理,我只能咬著牙不去多想,住進了這間堪比香港籠屋的集體宿舍。
平日裡,我們這些護士不僅毫無隱私可言,還得隨時注意躲避窗外行人的目光,換個衣服就跟打地道戰似的;每天洗澡得穿戴整齊排上兩個小時的隊,洗完再穿戴整齊走出來;自從看到有人將一雙滿是泥垢的運動鞋扔進洗衣機、與內衣內褲攪在一起後,我就斷了好逸惡勞的念頭,開始自己動手洗衣服。有這集體宿舍的襯托,我竟然開始懷念起了在群租房裡的短暫的「幸福」生活。
這樣的日子只持續了兩個月,我就「解脫」了——倒不是我自己出來租房住了,而是醫院倒閉了,具體怎麼垮的我也不太清楚,總之,就是我失業了,又沒地方住了。
朋友們聽聞我失業的消息,都第一時間發來了「賀電」,並一致表示:醫院肯定是被我搞垮的。嬉笑過後,有朋友勸我:「這些小醫院也沒啥發展前途,而且私人醫院在夾縫裡求生存也挺不容易的,還是考個大醫院吧,大醫院不容易垮。」
我想了想,確實是這個理兒。正巧那時全省事業單位考試臨近,我便火速報名備戰,最終從近千人的考試中殺出重圍,以第四名的成績考入了一家大的公立醫院。
3
工作找到了,擺在我面前的大事還是租房。
要去上班的醫院在一環道中心,附近房價高得令人咋舌,我自然想都不敢想,只能沿著地鐵線,一站一站地去找。
那時正是三伏天,我戴著遮陽帽跑遍了地鐵沿線的各個小區,問保全、打電話,爬樓看房、討價還價,最後終於在一個老小區租到了一個「套四」的單間,面積不大,但家具齊全。
我剛按照「押一付三」交了幾千房租,那60多歲的房東老太太扭臉就反口,一邊沾著口水數錢,一邊煞有介事地跟我提出了「三不許」政策:不許用燃氣灶、不許看客廳電視、不許開臥室空調,理由是「你們這些年輕人用東西浪費得很,怕你們給我用壞了」。
我希望她能通融一下,老太太還是堅持這套說辭。我的急性子又炸了,懶得跟她掰扯,便直接說:「我不租了,錢退給我。」
這下那老太太卻不依了,捂著口袋,擺出一副我拿她沒辦法的嘴臉,就是不肯退錢。拖了兩三天,非要訛我幾百塊「人工費」,才把剩下的錢退給了我。我雖恨得牙癢,也只能當破財免災,拿了錢又重新開始找房。
後面的一周里,我沒日沒夜地在各大租房網站上篩選合適房源,可網站裡大多是虛假信息,看上一間出租屋,電話撥過去,仲介總會信誓旦旦地保證房子還在,可到了地兒,他就立馬「遺憾」地表示:「你早來一步就好了,那個房間剛剛租掉了,要不你跟我去看看附近的?」
不用想,他帶我去看的,自然都是些地段偏、硬體差、沒人租的房子。
一次,仲介帶我去一個剛翻新的老小區看房,裡面空無一物,正要轉身走人,仲介卻勸我:「正好家具剛拉來,你幫我一起組裝好了,再看看整體效果,到時候你肯定覺得大不一樣了。」
不知咋的,那一刻我竟跟被下了降頭似的,傻傻地花了半小時、費了吃奶的勁兒幫著他組裝好了一個兩米的木床和衣櫃,弄完一看——「這整體效果好像跟剛剛沒啥區別啊?」
「哎呀,你實在覺得不得行就算了嘛,我也不強求你租。」仲介擺擺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突然明白,敢情自己是被當免費勞動力使喚了。
顛沛流離了小半個月,我總算通過仲介租到了房——是個電梯小區的「套三」次臥,房子就在地鐵口附近,離醫院5站,周圍生活設施也算齊全。
房子是租到了,日子卻依然過得不舒心。搬進來後,我才發現,自己租的這個單間正斜對著隔壁住戶家的客廳窗戶。為了保證自己在這個城市暫時且唯一私人空間的私密性,我只能不再拉開窗簾,過上了吸血鬼般不見陽光的日子。
房間狹窄,終日不見光,這讓我覺得自己像是被禁錮在一個小盒子裡,一度憋得抓狂。可就在這個黑暗的屋子裡,我一住就是兩年。以至於後來談到買房,朋友問我:「你對你以後的房子有啥憧憬麼?」我總會毫不猶豫地答道:「只要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就行。」朋友們紛紛取笑我沒追求,我也只是訕笑。
由於房間小、沒空調,我也不敢買大件兒——一是放不下,二是搬家麻煩。我從附近家具店扛了台塔扇回來,在逼近40度高溫的成都,塔扇降溫的效果杯水車薪。無數個暑氣熏蒸的夜晚,我一遍遍拿過了涼水的毛巾去擦竹蓆,擦完躺上去沒兩分鐘,身下那片兒就又開始發燙了,我只能不停翻身換地兒,跟烙煎餅似的折騰半天才能入睡。
至於同居的女性室友,一開始我還懷著熱情跟她倆談天說地、請客吃飯,可她們到底只是隨聚隨散的過客,流動性太大,一來二去,我也淡了心思。白日裡的工作已透支了所有力氣,等回到這個唯一的隱私空間,實在是連半分熱情都欠奉。我逐漸發現,還是跟室友做個陌生人最簡單——不用交際,涇渭分明,彼此都落個輕鬆痛快。
等後來,租客不斷更替,我跟她們也默契地保持著冷漠,且絕對避免同時出現在一個空間裡。日子一久,我聽聲辨位的功力大增,偶爾預判出錯、跟她們撞上,也只是不動聲色地各忙各的,沒有虛偽的寒暄,更無一絲視線相接的可能。
4
我一直記著自己選擇來到成都的初心——簡單地說,這裡就是我對生活的所有夢想。可「漂」久了,卻叫我不敢十分肯定這一初心的正確性了。
一晃已經是11月,護士長給我一周連著排了四五個夜班,每天凌晨從醫院走出來時,我就立即用口罩掩住青白的臉色,昏昏沉沉地匯入人潮。整個城市都籠在灰撲撲的霧霾中,路上行人也都帶著口罩,看不清神色,只是垂著眉眼埋頭趕路,像流水線上的人形木偶。
我忽然意識到,來成都已經一年了,我還沒能捕捉到這座城市的光影、描摹出它的筋骨脈絡,卻已先被它的生存壓力絆了個趔趄。
流動的陌生鄰居、逼仄憋屈的出租房、日夜顛倒的高壓工作,跟大多數在大城市奔波的年輕人一樣,每天兩點一線,往返於出租屋和工作之間。白天在急診重症病房裡繃緊神經忙前忙後,下了班,還得拖著空蕩蕩的軀殼去擠成都的「死亡專線」——排上半小時隊,被蜂擁的人潮推入車廂,被擠得雙腳幾乎離地,在車身的震動中努力保持著「我自巋然不動」的狀態。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親近」這個城市。
很快,出租屋裡的另一件事就直接激怒了我。
最初租房時,仲介跟我拍著胸脯打過包票——「絕不會有男租客住進來」,叫我放心。可一天,等我下了夜班回到出租屋,卻見一個年輕男人正從2號房裡走了出來,一見到我,立刻揚起黝黑的臉,沖我友善地笑了笑。
我笑不出來,直挺挺地僵在原地,怒意迅速蔓延到全身。我惡狠狠地剜了他一眼,竟恨不得把所有怒意全灌進這眼神里,再齊刷刷釘進他肉里。
那男人愣住了,顯然不明白我的怒意從何而來。我沒管他,以最快速度掏出鑰匙開了房門,再關上反鎖,整個人用力往門上抵,震得脊背生疼。
我很快撥通仲介電話,劈頭蓋臉就質問他為何出爾反爾。仲介卻不甚在意地跟我打哈哈,說他也無權限制租客性別。我氣憤至極,還沒繼續和他理論,眼皮就開始發燙,豆大的淚水止不住往下掉。
這些仲介整日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早就活成了人精,我這種剛出社會的小姑娘在他面前根本不是個個兒。他三言兩語便將我打發了,很快掛了電話。再撥過去,就只有冰冷的電子女聲。
我一時心亂如麻,一想到自己要跟一個底細不明的男人住在同一屋檐下,且不說生活上有諸多不便,萬一他起了歹念,我該如何應付?我又開始夜不能寐,每天掛著一雙青黑眼圈,搜索各種女子防身術、如何發現屋內隱形攝影頭,枕下還擱了把水果刀防身,常常在腦子裡演習著所有有可能的危險狀況和一招制敵的策略。
我也曾想過搬走了之,可眼下剛交了幾個月的房租,仲介自然不願退錢,我只能硬著頭皮繼續住下去。
好在時間久了,我發現他對我也並沒有任何威脅,也就逐漸習慣了他的存在——畢竟我們平時從不打照面,從不交談,除了住在同一屋檐下,我們算得上是沒有任何交集。
後來某日我刷知乎,看到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會有女生願意跟男生合租?」再細看下面的「問題描述」,字裡行間全是對與男生合租的女生的不滿和詰問。我不知道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是出於什麼心態,但說起來,我們都不過是被生活推著走的螻蟻小民,又哪能有那麼多選擇和事事順遂。
過了幾個月,這個黑臉男人也就搬走了。
5
2017年年底,2號房住進來了一個30出頭的失業男人。在此之前,從剛畢業的小姑娘、到敲代碼的程式設計師、再到一對年輕夫妻,這個房間的租客已經來來回回換了好幾茬了。
有了之前跟男租客們合租的經歷,我對他倒也沒有格外戒備,照樣過著自己兩點一線的高壓生活。
大年初五,我從老家返回成都,到達成都已是傍晚,街上千家萬戶燈火通明,歡聲笑語隱隱傳來,好不熱鬧。我披著一身倦意回到出租屋,正掏出鑰匙準備打開臥室,卻沒找到熟悉的鎖眼,登時被驚出一身冷汗——鎖被撬了!
慌亂過後,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俯身朝鎖眼看去,裡面的鎖芯已碎了個乾淨,一半留在鎖眼裡,一半零零散散掉在門框下。我伸手把地上碎掉的金屬粒一點一點摳起來,放進掌心仔細打量,涼意瞬間從脊柱縫裡湧出,爬滿全身——我清楚地記得,我走時鎖芯是完好無損的,現在碎得這樣徹底,只能是人為。
1號房的女生還未從老家回來,除了是2號房的那個男人所為,我想不出別的可能。
聽著2號房傳來的窸窸窣窣的動靜,我心下一驚,立刻打了門衝進去,再把門緊緊關上。大腦空白了好幾分鐘,我才回過神來,趕緊四處查看有無財產損失。
令我疑惑的是,所有東西都在,並無失竊。我一時沒了主意,本想打電話報警,可一來並無失竊,二來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主觀臆斷、沒有實證,警察來了,肯定也只是做個筆錄就走人,萬一激怒了那個男人,等警察一走就對我打擊報復怎麼辦?
出去住酒店也不行,屋子裡好歹是我的全部身家,現在門鎖不上了,我一走,萬一真失竊了怎麼辦?
偏偏此時又是大年初五,聯繫了幾個朋友,都還沒返回成都。打電話給鎖匠,也都還在老家歡度春節,我最後的求助機會都沒有了。
我很快意識到,自己陷入了一個巨大困境:出不去,待不住,進退維谷。
時間一點點流逝,夜色鋪天蓋地湧進房間,將我淹沒。我按下電源開關,昏暗燈光亮起,鎢絲燈嘶嘶作響,一聲聲鋸著我的神經。我捏著水果刀坐在燈下一動不動,看著自己的影子凝在地上,像個張著嘴的黑洞。四周黑魆魆的,一片死寂,我甚至能聽到自己太陽穴處血管的搏動,只有窗外街上偶有汽車駛過,輪胎與柏油路摩擦的聲音被黑夜放大。
枯坐了大半宿,我實在熬不住了,強撐著精神,將衣櫃和桌子推過來抵住門,裹著被子蜷在桌上睡了過去。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我第一時間聯繫了仲介要求退房。
雖然租房合同也差不多到期了,但想要全額退押金卻是不可能的。仲介公司找了多個拙劣藉口,將我的押金扣得七七八八,最終象徵性地退了我23塊錢。
我急於找下一個住處,也不想跟他們多掰扯,馬上又開始在租房網站上搜尋下一處安身地了。
6
這一次我運氣挺好,當天就在西三環外找到了一處合適的住所——雖然地段略偏,房子也有些老舊,但好在是個「套二」的出租房,租客只有一個女生。一付完房租,我立刻打包了所有行李,聯繫了小貨車準備搬家。
六七個鼓鼓囊囊的行李袋裝滿我所有家當,我幫著司機將行李全部扛上車,坐上副駕。等到了小區大門,車卻被攔下了。門口保全挎著電棍,警惕地繞著小貨車看了半晌,語氣不善:「你們這搬家,得先去物業那兒開個通行條,不然不許出去。」
我掏出租房合同給保全看,又說了半天好話,他依舊不予放行。司機安撫我:「你去物業那兒開條吧,我保證不得把你東西拉起跑。」我只得下車快步往物業中心跑去——說來可笑,我還當真擔心司機將我所有家當給拉跑了。
10分鐘步程,我一路疾跑只用了3分鐘。可到了物業那兒,居然又遇到了一場無妄之災——雖然我租房兩年的所有費用都已給仲介繳清,可仲介竟已5年未繳物業費了。了解我的來意後,工作人員給業主打了電話,詢問是否放行,業主明知我的租期只有兩年,卻在電話里徑直要求我先替仲介繳清5年物業費,否則就不讓我走。
我連忙打電話給仲介,那邊卻就開始推脫責任,還說叫我自己跟業主協商。可不論我如何解釋這事和我無關,物業和電話里的業主都一口咬定——不管是誰,必須先交錢。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陸續有牽著孩子、提著菜籃的住戶走了進來,物業又立即迎了上去,滿臉春風地向住戶們介紹著最近換門禁卡、掃碼領獎品之類的活動。空蕩蕩的物業中心一時熱鬧起來,可我獨自站在大廳一旁,只覺得如同置身荒野、四面來風。無形中像是有一道壁壘,將我與他們隔離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租戶」,一邊是「業主」,涇渭分明。
我掏出手機給小貨車司機打了電話,告知他這邊的情況,可沒等一句囫圇話說全,就鼻子一酸,忍不住低聲哭了起來,一邊哭還一邊不停警告他:「不許把我東西拉跑了。」
司機大約覺得我很是莫名其妙,只說了句「那我先等著吧,你等會兒得加一百塊錢」,便掛了電話。
許是見我哭得太有礙觀瞻,工作人員終於招手將我叫了過去,然後把蓋了章的通行條交給了我。
好不容易搬完家,我才開始細細檢查起了房子:陽台欄杆上油漆剝脫,已翻出了大片的鐵鏽色;立櫃式空調的扇葉上也長滿了灰毛,送出的風都裹著濃重霉氣;房間鎖的質量欠佳,螺絲鬆動……
我買來所需物品,然後全副武裝,開始動手刷油漆、清洗空調、換鎖、疏通下水道,弄完這些,再開始整理床鋪,抬起床板,卻瞬間頭皮發麻——床下的空隙間密密麻麻全是蟑螂。
這些美洲大蠊,個個通體油亮,擅長飛行,一隻都夠讓人抓狂的,何況這一大窩?我還沒從恐懼中緩過來,幾十隻蟑螂就已飛速爬了出來,有幾隻甚至從我腳上爬了過去——那種觸感,終生難忘。
我強忍住想要截肢的欲望,立即退出房間,深吸一口氣,正式開始了除蟑大業。
到底是在地球上生存了4億年的王者生物,想要將它們這些蟑螂消滅乾淨,著實不易。我用硼酸將全屋清洗,各角落放上餌劑、再噴殺蟲劑,門縫全用泡沫墊子堵起來作為門擋,臥室門口也灑了一圈硼酸劃出安全區。即便這樣多管齊下,我還是沒能徹底清除這些惱人的蟑螂,原因無他——室友太不愛乾淨了。
多番勸說無效,我又只好做起了家庭保姆,包攬了所有倒垃圾、掃地拖地、定期除蟲的工作,最終也算卓有成效。
衛生問題解決了,新的麻煩又來了。
沒過兩個月,室友談起了戀愛,開始頻繁地將她男友帶回出租屋。有次我一開門進去,就看到他倆跟連體嬰似的抱在一塊兒動情親吻,親得忘我,如入無人之境。眼瞅著他們的嘴都拔絲兒了,我趕忙扭身開門進了自己房間。
而之後的事才真叫一言難盡。
說起來,這對脾氣火爆的情侶也挺有意思,往往凌晨兩三點萬籟俱寂時,就像狼人一到月圓之夜就要變身一樣,毫無預兆地就拉開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每回都是我睡得正酣,一聲驚天動地的獅吼就會瞬間把我震醒——這便算是他倆正式開戰了。開戰後,上來先是一陣狂風驟雨般的罵戰,罵架也不帶重樣,一般先禮貌問候對方的祖宗十八代,探討「X你大爺」、「X你娘」的倫理問題,再自由搏擊半小時,然後就是跺腳捶牆,消停沒兩分鐘,居然又發出生命大和諧的聲音。
我頭昏腦脹地聽著隔壁的動靜,實在驚訝於他倆這起承轉合毫無章法和邏輯可言。
這樣的次數多了,我也忍無可忍了。一次,又是凌晨兩三點,我看他們還不消停,便從床上爬起來,假意上廁所路過他倆房間,然後大聲咳嗽以作示警。
誰曾想,我明示暗示了個遍,他倆的聲音反而越來越大,頗有戰死方休的氣魄。我只得拖了條凳子坐到房門口,然後掏出手機開始放歌——《新聞聯播》的片頭曲,最大音量。在這莊嚴肅穆的歌聲中,隔壁這才終於漸漸偃旗息鼓。
我原以為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此結束——誰料我回了房剛一躺下,隔壁又開始哼哼唧唧起來。我心想:有種你別停,我且放個《郭德綱相聲全集》給你們助興。然而這興到底是沒助成,被他們鬧了大半宿,我腦袋昏昏沉沉實在困得慌,不知不覺就睡了過去。
自那後,隔壁的確收斂了不少,我也不再計較,半夜再被吵醒,也只當聽個有聲小說了。
7
搬了數次家,跟各種室友鬥智鬥勇,雖然一地雞毛,日子卻也都這樣磕磕絆絆過來了。
轉眼到了2018年年尾,我辭去了醫院的工作,轉行之路又困難重重,一時茫然,整日閒居出租屋內無所事事。父親打來電話,勒令我在春節之前回家——說是家裡已經替我找好了醫院,年後就得去上班。
想來人生許多大事小事最終落錘,也就都在春節前。
父親軟硬兼施,我卻遲遲不願答應,我不想重新回到被他規劃人生的日子——父親向來強勢獨斷,我從小到大的所有事皆由他做決定,容不得我置喙。
見我油鹽不進,父親頓時惱了,說話也帶了刺:「你一個人非要去成都,大城市就那麼好嗎?我們這種小城市容不下你是怎麼的?你認為你自己是拿得到成都的戶口還是買得起成都的房?未必你想在成都住一輩子的出租屋?」
我只能沉默以對。
在成都的這第三年年尾,我開始回想那些自己在這個城市掙扎生存的日子,以及決意要來成都的初心,卻始終像是有煙霧繚繞,看不分明。
我想起之前那逼仄、不見天日的出租房,想起搬家找房被坑的種種經歷,想起吃到吐的外賣、流動的陌生室友、飛漲的房租,一時竟生出「拔劍四顧心茫然」之感。我忽然才意識到,我在這個城市的所有跌跌撞撞求生存的片段,似乎拼湊不出一個可能的未來。
可又轉念一想,生活不就是這樣麼?這世上本就沒有一眼能望到底的清晰坦途,誰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罷了。哪怕這河過得跌跌撞撞,哪怕被這人間煙火熏得灰頭土臉,好歹也算是實實在在活了一遭。
「我還想待在成都試試。」我這樣回答父親。
說這話的時候,我清楚地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我的合租生涯,還遠未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