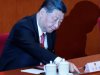資料照:在中國軍隊對抗議人群開槍後不久,北京市民把受傷者抬上平板車。(1989年6月4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民主運動以中共當局的暴力鎮壓結束,6月3日夜晚到6月4日凌晨北京城徹夜的槍聲震驚了世界,也成為了很多中國人內心永遠的傷痛。三十年過去了,當時的親歷者們對於那段過往有著怎樣的回憶與感觸?美國之音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之際採訪了多位「六四」親歷者。
八九學生運動領袖之一、曾在天安門廣場領導絕食請願的王丹回憶說,剛聽說政府開槍的時候他甚至不敢相信。
「(6月3日晚)我傳達室的電話就沒有斷過。不斷有同學在長安街找公用電話打過來說政府已經開槍了。一開始我還不相信,到後來越來越多了當然我知道這就是真的了。當天晚上我的心情都還是不敢相信,即使這樣。但是第二天都已經確證的情況下,大概有兩到三天的時間,就沒有什麼想法。因為你要知道,震驚如果太大的話,腦子會變麻木的,所以那兩天我基本上什麼都沒有想,完全處於一種麻木的狀態,太過于震驚了。」
不過,被中國政府指控為八九學運的幕後黑手而流亡美國的作家、電視政論片《河殤》總撰稿蘇曉康卻表示,對於中共開槍,他並不吃驚。
」開槍我是在一個躲藏的地方從收音機里聽到的。我一點也不吃驚,我早知道共產黨會開槍。因為鄧小平從427大遊行以後就消失了。那時候社會上盛傳他躲起來了,什麼鄧家都躲起來了。他哪裡是躲起來了,他去調軍隊去了!中國老百姓那時候那個幼稚啊!對共產黨不懂啊!我們那時候就知道,如果這個當中沒有學生和趙紫陽、知識分子不能有一個很好的合作,想辦法制止鄧小平,一定會開槍。」
曾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智囊、因支持89民運而遭到迫害並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說,在他聽到槍聲的時候,他知道,中國發生變化了。
「(6月3日)晚上11點鐘,我還在天安門廣場,後來我知道那時候已經開槍了,但是天安門廣場有幾十萬人,根本聽不到的。當時我想離開廣場,但是離不開的,因為人太多了。結果我從帳篷後面把線拆開之後離開廣場的。到家也沒有感到有開槍的問題。當時覺得很平安,第二天還可以正常地工作。但是睡覺睡到晚上一兩點鐘的時候,突然聽到槍聲大作,像放鞭炮一樣,但是聲音大得多,尖銳得多。我們跑到陽台上去看,我們的陽台就在東總布胡同,可以看到東長安街。看到很多閃光,密集的閃光。我當時就知道,開槍了,感到中國發生變化了。」
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時任《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的王軍濤回憶了他在五棵松親眼見到平民倒在戰士槍口下的一幕。
「後來我就下車走到五棵松路邊,看到一輛軍車拋錨了,軍車都是敞篷麼,戰士不斷從裡面往外打槍,老百姓就匍匐前進,弄了好幾車磚頭,』一、二、三』一塊兒站起來,嘩,那磚頭真的跟雨似的砸上去。其實復興大路那時候那個燈中間是黃的,戰士在中間看不到兩邊,兩邊能看見車中間的戰士。所以那個磚一上去,戰士就噼里啪啦往外打槍。我就看見路中間躺一個人,我想那是第一個被打死的,就在路中間躺在那。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死不瞑目,他臉看著天,頭流著血。因為那個黃光很黃,我也離得遠,我也沒法到前面去,就看著那個場面,我當時就覺得頭皮發麻。我就知道一個沉重的日子就算進入了中國歷史,中國的政治可能要有一個大倒退。」
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當年從美國回到北京參加學運。他回憶了他目睹」六部口慘案「的過程。
「1989年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我當時在美國,在美國讀數學博士,但是在運動中期,學生絕食後,我就決定回去參加運動。在戒嚴後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北京參加運動。第一次聽到槍響是6月3號晚上12點以後。當時我和一個朋友正在騎自行車從校園往天安門廣場趕。因為6月3號一天,我們都在那堵軍車啊,參加遊行,感到非常的疲乏,所以到傍晚的時候,我們回到學校去洗個澡。洗完澡以後,騎自行車想趕回廣場的時候,剛出校園的門口,大概剛過12點,聽到第一聲槍響。所以六四第一聲槍響的時候,我正在北師大的校園趕向西單的路上。騎在自行車上。當我們趕到西單的時候,部隊已經邊開槍邊向天安門廣場推進,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從前面被打死的學生還有市民抬下來。一開始我們還有幻想,可能是向天打的或者橡皮子彈,等等,還做這樣的幻想。當我們到了西單的街口,那時候槍聲一響,大家都往地上趴,再起來的時候前面就抬出幾個屍體下來,當我們看到身上的槍傷的時候,就知道這都是真的。然後我們就在長安街和往天安門廣場推進的部隊拉鋸。一會兒我們靠近他們,不開槍了,我們試圖說服他們,有時候想試圖用歌曲打動他們。但是一旦他們接到命令往前推進的時候,遇到阻力他們就會開槍。所以在那個地方,我看到了有幾十個人被打死。到了凌晨的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就到了廣場的前面,叫前三門大街,那個地方正好遇到從廣場最後撤退的大概有400人,400位學生。我們就和他們匯合,然後,又從六部口回到了長安街上。就在那個時候,我將要上長安街的時候,從天安門廣場開過來四輛坦克車,第一輛往人群扔催淚瓦斯,第二輛開機槍,第三、四輛就直接追著撤退學生的隊尾壓過去。當時我目睹了慘案,叫六部口慘案。當時四輛坦克車開過去時,是一片狼籍,大家先安靜了一下後,每個人都在驚叫,然後就去搶救被壓在地上的學生,有一些已經死去了。我們抬到平板車上,當時大概數了一下有十幾位。所以那是我看到的六四屠殺最悲慘的一幕,也就是六部口慘案。在那以後,我們又呆了一段時間後,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校園,所以我在屠殺的現場一共呆了十個小時左右。」
方政當年是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在「六部口慘案」中遭到坦克碾壓失去雙腿。他希望人們能記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亡靈。
「6月4號清晨大約6點,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3千名左右學生被戒嚴部隊驅趕出天安門廣場。方政就是其中之一:這只是其中一個畫面的場景,這個坦克停下來了,但是還有更重要的一個情景,希望大家記住,在北京西長安街六部口,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從身後在追殺襲擊了我們這些和平地撤離廣場的學生。在那裡,又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樣,受傷致殘。所以今天我作為一個六四屠殺的一個見證者,一個倖存者,一個坦克下的倖存者,在這裡,希望大家記住,記住1989年6月4號的那一幕,記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亡靈。」
時為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學教師、在天安門廣場任「外省援京團」團長的曹旭雲回憶了在天安門廣場上聽到的槍聲。
「我就在廣場上,廣場上留下了兩千多學生吧,我和學生們在一起,一直到早上三四點的時候被驅離廣場。當時驅離的時候,我被棍棒打暈了,然後頭上身上全流著血,昏迷了,被送到北京醫院,在那裡理療了兩天一夜之後恢復過來……太多了,真正的清場是早上三四點的時候,裝甲車晚上九點來鍾就開始有了,就開始有大規模的裝甲車從東往西,從西往東,都有。廣場四周全是槍聲,在天安門廣場城樓附近四周有零星的槍聲,廣場上並沒有大規模的殺人,這個是對的。但是四周,那是太多的死傷。因為我一直都在廣場,廣場上哪個地方有死亡,哪個地方有死傷,在廣播還沒有打滅之前,都有傳過來消息。有的是只知道哪個地方死了多少人,有些地方是知道死者的姓名,還有哪個學校。有些是市民,有些市民知道他的姓名,有些不知道。」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人道中國創辦人周鋒鎖回憶了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全副武裝的軍人之間的對峙,以及同學的死亡所帶給自己的震動。
「6月3號早上我本來外出的,當時我覺得自己非常累,我就想換一個想法,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一下。結果那天早上聽到有一車武器被送到學生手裡的消息,我立刻感覺到這是一個要鎮壓的信號,其實這車武器被學生送回了警局而且拿了收據,但是學生在車上展示武器的照片到處流傳。所以後來鎮壓之後,這也是被作為鎮壓的理由之一。到晚上的時候,下午我就到了人民大會堂附近,看到有軍隊試圖從裡面出來,被學生攔住,空氣中瀰漫著催淚彈的味道,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聞到催淚彈,就知道這次形勢會很緊張。就從那裡開始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月4日凌晨被驅趕走,我是最後從紀念碑南側離開的,就是第一次面對這種戰爭場面,而且戰爭的一方是全副武裝的軍隊、坦克、裝甲車、機槍,這邊就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在廣場上的學生,特別是劉曉波那些人,堅持碰到任何武器都把它砸碎,所以絕對是手無寸鐵的。但因為我在後面,就沒有趕上坦克壓人的時候,我就騎了一輛自行車,從那裡往西,回到長安街,從長安街往西走,長安街上更是一片狼籍,當時有很多被燒毀的車,路邊也有衝撞的痕跡,很多北京市民在那裡憤怒地議論紛紛。我還記得從六部口往西一點附近就有人在牆上寫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話我印象很深。從那兒走到木樨地大概是8點左右,就看到有人看到因為我身上戴了一個牌兒,當時晚上為了便於識別,寫了我的名字,清華大學學生,有人看到就說,哎,你是學生,你們清華有學生死在這裡,把我直接帶到復興醫院。復興醫院門口的自行車棚裡面,地上有四十多具屍體,大部分是白布裹著,當時看到是非常的震撼,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我們清華在那個地方,死去的同學叫鍾慶,他是精儀系86級的。當時感覺這個國家是非常可怕非常殘暴的,另一個跟我一樣的人瞬間就消失了,就覺得人的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周孝正說,那時候他們這些「老朋友」都為學生們揪著心。
「因為學生不撤啊,當時我們這些老朋友都揪著心啊,因為肯定要開槍啊,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要開槍的,但是什麼時候開?我們就揪著心。到了六三晚上、六四早晨,因為我們家住在前三門,車就進來了,坦克車、裝甲車還有軍隊,手握自動武器,就進來了。到了大概是半宿就啪啪啪,就開槍了,遠處就聽見咚咚,爆炸聲,但是我們聽見的就是啪啪啪。我的樓是靠著前三門馬路的,所以我在樓道里就看見軍隊,兩邊都是學生,或者說是老百姓,攔軍車。那哪裡攔得了,解放軍一開槍就都跑了,我看得特別清楚。悲劇終於發生了。不是中國的悲劇,人類的悲劇終於發生了,兩邊撕破臉了,學生就跑了。本來學生讓你撤你不撤,人家小平調兵去了,你們學生應該有對策啊,用現在的話,你們上井岡山啊,哪有這素質啊,一開槍全跑了。跑的跑,但是解放軍真殺人啊,大約殺了不到一千,打傷大概五千多,我估計是這個數量級。打得當然沒有血流成河,但是這也是一灘血,那也是一灘血。學生哪見過這個,打趴下了,完全超出他們的預料。開完槍後,小平也不在北京,6月9號電視台轉播,小平把軍以上幹部召集起來,他講話,他手當時都是哆嗦的,他怎麼說的,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我知道,推卸責任吶。因為這事兒不是他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後果,因為黨內有所謂右派,黨內右派說,你看,你改革開放,得了,學生出來要推翻共產黨,所以他得說這是國際大氣候,國內小氣候。現在的學生不如89啊,89年的學生都是有理想的,你現在再問學生,都是賺錢,現在就是一切向錢看.」
八九學運的學生領袖之一吾爾開希認為,三十年後反思當時的運動,「99分應該是有的」。
「八十年代是中國非常精彩的十年,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也是共產黨的口號,也是中國人民的感覺。但是這個改革開放,共產黨所願意給的只不過是能夠解除他們所陷入的經濟困境,只願意很被動的做一些經濟改革。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向中國老百姓做了大量的承諾,會讓中國走向更開放。當時學生走向街頭,就是要求政府貫徹他們自己的承諾……首先,重來是不可能的。即使這樣,也有必要來認真反思。三十年以後,反思的結果,我們當年八九年的學生,以當時那個條件,所做出來的每一個決策,都是經過非常慎重地思考的,也是在始終貫徹著理性的光輝之下做出來的,所以我們當時也許做的不到100分,但99分應該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