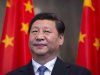張扣扣(網絡圖片)
張扣扣案庭審完畢後,我在個人微信公眾號和微博發布了我的辯護詞《一葉一沙一世界》。讓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辯護詞引發了全國層面的熱議。微信公眾號文章在閱讀量約150萬的時候,結束了自己不到三天的生命。
讚譽者稱我的辯護詞是「史詩級的」、「教科書式的」,批評者認為我的辯護詞過於煽情、缺乏說理,不及格。不論毀譽,我覺得我都有必要回應一下。
張扣扣案最先是由殷清利律師介入辯護的。大約幾個月前,殷律師第一次邀請我參與此案。但當時,我認為這個案件結局確定,沒有辯護空間,所以並未答應。直到一個多月前,殷律師再次聯繫我,告訴我另一位辯護人因各種壓力已經退出辯護,而他本人也壓力很大,希望我能介入加強一下辯護力量。
當我聽完殷律師的介紹後,我頓時決定加入辯護。目的不為別的,就為了捍衛辯護權本身。不管張扣扣是什麼人,他都有權委託律師辯護。於是,我很快便到漢中會見了張扣扣,去漢中中院複製了全案卷宗。
會見完張扣扣後,我發現我做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張扣扣絕非一個兇殘的殺人惡魔,他只是一個有著特殊童年遭遇、生活在社會底層且對這個世界充滿感情的普通人。我問他為何沒有第一時間自首,他說這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個除夕夜,他想要最後一次看看人間的煙火。
我問他有沒有想過,如果案件結果不好會怎樣。他回答說,我做出這個選擇的時候就已經知道結果了。我問,你對死亡不恐懼嗎?他說我很坦然,視死如歸。雖然我相信他肯定會有恐懼的時候,但他每次見我都有說有笑,我沒有從張扣扣的臉上看到對未來的恐懼。看守所出具的《證明》也說他「態度樂觀,樂於幫助他人」。一個超越生死,對死亡沒有恐懼的人,一定不是一般、普通的人。
接踵而至的問題是:我該怎麼去為張扣扣辯護?既然加入了辯護,我當然希望能對案件結果有所影響。我不是去為張扣扣送行的,我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夠挽救他的生命。按照法律,按照道德,按照情理,張扣扣該不該死,我都必須置之一旁。當我成為張扣扣的辯護律師的時候,我就不能再是一個普通公眾的視角。我必須完成《律師法》和《刑訴法》給我設定的職責和義務,為張扣扣爭取生機是我唯一的使命。否則,我就是失職失責甚至違法。
十幾本卷宗,我都仔細進行了研閱。這個案子的證據雖然有些許形式上的瑕疵,但足以證明起訴指控的事實。張扣扣自己穩定的供述,多名目擊證人的證言,張扣扣衣服上檢出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跡,張扣扣帶領偵查人員打撈到了作案刀具。加上作案動機明確,提前購買了刀具、提前進行了踩點觀察,此案屬於確鑿無疑的故意蓄謀殺人。故意殺死三人還接著放火燒車,稍微了解司法實踐的人,都知道僅有自首情節根本無法免死。
當時,我認為精神病鑑定也許是此案唯一的轉機。張扣扣的童年遭遇和向我描述的作案心理,讓我高度懷疑他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第二次庭前會議上,我和殷律師都堅持要對張扣扣進行精神病鑑定,但是法庭當庭駁回了我們的申請。此路不通,加之被害方家屬王家又在第一次庭前會議之後撤回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其放棄民事賠償、要求刑事嚴判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儘管如此,我還是跟張扣扣家屬多次溝通,要求他們儘快籌資、主動進行賠償。
張扣扣家屬籌措到資金後,卻無法跟法院和被害方家屬有效對接,所以才出現了正式開庭時我當庭出示了家屬籌集的四萬元現金。奈何在法院工作之下,王家還是堅決不予接受,只要求法院判處張扣扣死刑。兩家積怨至此,王家的態度完全在我意料和情理之中。
於是,所以,這個案子的辯護已經被逼到了絕路。在第二次庭前會議上,我跟殷律師達成了「一文一武、張弛結合。互有分工、互相策應」的辯護策略,並在庭前會議和正式庭審中進行了實操演繹。殷律師負責展現「力度」,我則負責輸出「溫度」。
很多人看完我的辯護詞,以為我在這個案件中就宣讀了這一篇辯護詞。他們不知道,我在庭前會議和正式庭審中就自首的主動性、精神病鑑定的必要性、96年案件對於本案的影響、作案對象的限定性等方面發表了多少辯護意見。
正式開庭審理時,合議庭首先宣讀了庭前會議報告。宣讀完畢,我立即提出了四條理由,認為合議庭不予精神鑑定的理由不能成立,當庭要求對張扣扣進行精神病鑑定。圍繞檢方出示的證明張扣扣精神正常的證據,我先後發表了三輪質證意見,並且申請恢復法庭發問。
在庭審開始的法庭發問階段,我圍繞張扣扣是被迫自首還是主動自首、行兇動機、96年事件對張扣扣的心理影響等問題,進行了長達近半個小時的發問,發問時間和發問數量遠超公訴人。公訴人還曾提出反對,認為我對96年的事件和心理問題發問過多。證據質證部分和程序部分主要以殷律師為主,我的確發言不多。
我沒有仔細查看圖文直播的內容,但僅看到的部分就出現了大量的錯漏。我的意見有的被記在了殷律師頭上,殷律師的意見有的被記在了我的頭上,還有許多的記錄不全或表述錯誤。一些人沒看過庭審直播或者看到的只是不完整的直播,就在辯護策略上對律師進行指責,這是不嚴謹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我做過七年的國家公訴人和四年多的專業刑辯律師,經手的各類刑事案件不下千件,其中不乏大案要案,我豈能不知道法庭上該如何辯護、辯護詞該怎麼寫?這份辯護詞,一開始我還是按照傳統的結構和手法去寫的。但是某個晚上,我突然意識到:非常之案,需要非常之辯,絕地求生需要不循常規。第二天一早,我決定大膽試驗,最終改成了現在這樣的版本。傳統的寫法容易,我更在行,現在這樣的寫法才更費思量。這份辯護詞是為這個特殊案件量身定製的,不代表我以前也是這麼寫辯護詞的,更不代表我今後每個案子都會這麼寫。
有法律人士自詡「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說我煽情而不說理,是譁眾取寵而不是說理辯護。甚至有人譏諷,這樣的辯護詞只為自己贏名聲,卻故意把當事人推向了絕路。誅心之論在我們的社會總是很有市場。部分原因在於誅心之論無法證偽,又迎合了人性中的陰暗面,還似乎自動將自己擺在了道德制高點。其實,喜歡誅心的人自己往往才是最陰暗的,也往往是最喜歡譁眾取寵的。沒有能力說理了,沒法引人關注了,誅心往往是唯一能改變局勢的辦法。誅心絕不是真正的批評。
我歡迎就事論事的、有建設性的批評。比如有法官撰文《作為刑事法官,我希望聽到怎樣的辯護詞》。比如還有同行撰文,稱我的辯護詞不講證據和事實、不援引法條屬於耍流氓。不過,我認為這些說法在普通案件中本是常識,但在張扣扣案件中屬於脫離實際的空泛之論。這些人做鍵盤俠的功力要遠超過真正去法庭辯護。這個案子如果只在現有證據和法條層面進行辯護,那才是真正的形式辯護。僅僅按照證據、事實和法條的所謂結構和邏輯去寫辯護詞,根本沒有任何改變結果的可能。我和殷律師雙劍合擊,或許才能集結最強辯護力量。
我做過七年公訴檢察官,豈不知道現在的刑事法官想聽什麼?但是跳出體製做律師以後,我才更加知道刑事法官還應該聽什麼。天津趙大媽氣槍案、深圳鸚鵡案、連雲港藥神案、山東於歡案,最開始的判決不都是按照該法官的邏輯做出的嗎?當時的律師不就是按照該法官想要的方式撰寫的辯護詞嗎?可結果呢?實現公眾想要的正義了嗎?
做了律師以後,我才認識到,司法判案不應該是簡單的比照法條那麼簡單。司法的合法性源於它對社會的滿足和對正義的回應,而不是簡單的、機械的做出一個判決。認定一個人是否有罪,本質上是在界定一個社會共同體所能容忍的行為底線。司法可以合法的剝奪一個人的生命,但司法的這個權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人民授予的。如果絕大多數人民覺得某個人可以不死,司法機關執意判決一個人死刑的正當性基礎何在?
有人批評我的辯護詞沒有法律分析。我只能說,這些人所謂的法律只是成文的法條,跟我心目中的「法」的定義不同。任何社會都有兩套秩序,一套是由國家法建構起來的正式秩序,另一套是由道德、風俗、習慣等逐漸形成起來的民間秩序。我在辯護詞中將之分別稱為國家法和民間法。我懇求國家法能夠適當兼顧民間法,定罪但從輕,並試圖以此為突破口為張扣扣尋求一線生機。這個辯護策略你可以不同意、可以不認可,但不要說我的辯護詞不講法。難道法理分析不是法律分析?誰能否認,天理、正義、良知才是最高層級的法?
對那些批評我太文學化和太煽情的人,我只想問一句:誰規定了辯護詞該怎麼寫?為生命辯護,為什麼不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我只不過是採用了一種強敘述、弱議論的表達方式而已,通篇辯護詞並沒有一句話是在刻意煽情。至於有人說這篇辯護詞只能對公眾講,不能對法官講,我就更不明白了。難道法官就不能有普通人的感情嗎?詩人艾青說過「我為什麼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一個沒有感情的法官,你相信他會真的熱愛法律、敬畏生命、關心正義?
寫張扣扣案辯護詞之前,我甚至都沒有想好要不要公開發布。漢中中院在微博圖文直播的時候發出了我的辯護詞概要,我才決定全文公開發布。寫完這篇回應文章,已是深夜十一點。窗外斜風細雨、寒意濃濃,應了那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