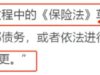恐懼與釋放
人們在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前,通常都有一段並不怎麼愉快的記憶。有些時候,這跟一段動盪的生活有關;有些時候,這源自於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還有的時候,一些人在水下太久,只是想伸出頭來透口氣。
讓張雪下定決心的是某種恐懼。自2014年從一所三本學校畢業後,她在東部沿海的一個「十三線小城市的小國企」工作了5年,如今每個月3000塊錢工資,相比5年前只上漲了500塊錢。去年公司資金鍊出了點問題,做財務的好友偷偷傳話給她,就四個字,「早找退路」,意思是她隨時有被裁員或是停工的可能。
張雪做了一個簡單的算式,「現在的家庭利潤=父母收入+我的收入-吃喝拉撒-房貸」,而「未來的家庭利潤=父母退休金(相比工作工資收入↓)+我的收入(上漲幅度不大)-吃喝拉撒-房貸-父母醫療款(年紀越大健康越差)-子女教育」。很明顯,整個家庭的「利潤」是下降的。更不用說如果沒了工作,資金來源更是問題。所以她格外看中保住自己的本金,決定用利息生活。
她也有過大額消費的時候。比如出去旅遊在某個廟裡花2000元買了串佛珠,「現在我儘量不去回憶這件事。」也有過極其想買一件東西的時候,比如在去年,她特想買一款水晶吊墜送給自己當生日禮物,但最後以「買了應該也不好搭配吧」的理由忍住了。當類似這樣自我約束的次數多了,購物的欲望就會越來越少。尤其想到未來的資金來源很可能不穩定時,恐懼讓她面對「提前消費」這樣的新觀念時尤其抗拒,信用卡、網貸變得沒有任何吸引力。對她來說,更具有吸引力的事情是,今年年底,她的存款可以到20萬了。
對比也很明顯。她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比她早工作幾年,愛好看電影,喝咖啡,現在除了5萬存款,什麼都沒有。「生了孩子之後,她們家的日子過得很拮据,不過她前段時間還是跑去看四十多塊錢一場的電影了。」相比於去電影院看電影,她認為自己未來的目標更大,這更像是一種想實現階層跨越的理想。「因為我有一個朋友特別富有,我見識過他們的那種生活,我很憧憬,所以只能現在開始努力攢錢。」
「用利息生活」小組的創始人尋我,在2013年,舉全家之力,外加還找親戚朋友借了10萬塊錢,才在當地城市為購房湊出了首付。後來的兩三年時間裡,全家人首要任務就是還錢。那幾年她開始知道錢的可貴。2013年時,她一個月的工資還沒有按揭的房貸高,如今隨著工資不斷上漲,房貸已經可以用公積金還了,但她仍然過著幾年前一樣節約的生活。之所以創立小組,尋我說,「只是偶然隨手一建,畢竟我已經過了尋找同路人的年齡了。」但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同事們都不知道她的生活方式,「用利息生活」小組或多或少成了她另一面的出口。
吳磊在發年終獎前一個月裸辭,完全是幾年來積累情緒的一種釋放。「家裡的廠房在賣掉之前,出了點糾紛,一直在打官司,如果官司輸的話,還得賠錢。」他上班的時候是心懷恐懼的,直屬領導脾氣有些差,掌握著每個季度的考核大權,幾乎每個季度都有排名末尾的同事被刷掉。所以他每次見到領導都點頭哈腰,跑腿買奶茶要衝在第一個。儘管長此以往他跟領導混熟了,但他也因此成了領導的出氣筒,有什麼抱怨的事情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他早就受夠了。
他因此一直都憧憬自由的生活,所以,當條件充分時他馬上就開始實施了。他喜歡海,辭去工作之後,決定到廈門去度假。他選了套月租7500元的酒店式公寓,直接租了一年,拉開落地窗的窗簾就能看到海,去鼓浪嶼的嵩嶼碼頭只需5分鐘的車程。
「也就9萬塊錢。」吳磊說。買了理財,交了房租,他每個月仍然有12500塊錢可以支配,是以前工資的兩倍。
那些因為各種原因決定用利息生活的人,都加入了豆瓣小組。那裡魚龍混雜,既有像張雪這樣與尋我理念相同的人,也有致力於投機事業,炒期貨、玩虛擬貨幣的,還有搞傳銷、推銷保險的。小組裡有人發帖子《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是怎樣實現財務自由的》,點開一看,是賣炒股教學課程的;也有帖子抱怨《實現財務自由的我每天特別無聊》,底下有人調侃「每天拿鑰匙到不同的房子收租嗎?」不過,無論是投機者、省錢者、騙子、還是真正的深藏不露的土豪,大家來這個群關注的都是同一件事——財富,以及活著。
自由的反面
在「用利息生活」小組裡,每個人都有省錢的秘訣。在一家網際網路公司上班的周軍會把公司發的一切員工福利掛在網上出售,三年來公司發的知名品牌的月餅券,他從未兌換過,全部七折出售。而趙樂樂從公司回家乘滴滴本來需要6塊錢,她省錢的辦法是步行40分鐘回家,她認為如果每天都能省下6塊錢,一年就能省出來一個月的生活費——不過她可能忽略了自己因此每年要花費14600分鐘在路上。
主婦孫小梅是更專業的省錢人士,她去超市買任何東西都要橫向對比,對比的方法是用價格除以重量,比如,售價21元的200毫升的洗面乳,實際上要比售價18元150毫升的洗面乳便宜。但這樣做的缺點也很明顯,用她的話說,每天都像在不停地做小學數學題。
許多人也發現,這種生活方式有可能成為一種負擔。比如,為了省錢,尋我在淘寶上買了包月的「紅包省錢卡」,每天都能領到一些紅包,紅包一般只有幾塊錢,可以抵扣網購的費用,但是幾天不用就會過期。為了不浪費紅包,她必須竭盡所能地找到便宜並且包郵的商品,然後花掉紅包。
買著買著,這成了一種負擔。「你能體會一個幾乎每天都在買筆,最後家裡有幾百支筆的人的感受嗎?」她問。
有一次周末,她心血來潮,拿出家裡筆的一小部分——兩個抽屜的中性筆——出來數,最後發現有173支,此外還有數量更多的原子筆、鉛筆、彩筆、蠟筆等各種筆。耳機線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一共買來了幾十根耳機線。她估算了一下自己使用筆的速度,在現在無紙化辦公的大環境裡,大約一支筆能用一年,這樣她買的筆就能用幾百年,可能用到她的孫子那一輩都用不完。
而就算是利息足夠多,不用刻意省錢,也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恐懼的形態是在不斷變化著的,當工作的時候,面對著失業的恐懼,而當不用擔心錢的問題,整天可以無所事事的時候,又面臨著生活沒有目標的恐懼。」
對吳磊來說,頭三個月,手機再也沒有了無休止的工作群微信,晚上看劇再也不用擔心第二天起不來床,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凌晨三四點才睡。但由於之前上班生理時鐘的緣故,他常常在早上8點鐘驚醒,像彈簧一樣彈起來覺得上班要遲到了,扭頭一看落地窗外的海浪,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我現在可是自由了」。興趣上來了,就去外面的行人徒步區上走走,或者坐船去鼓浪嶼,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就連以前從沒去過的酒吧,也在鼓浪嶼去習慣了,以至於有一天喝多了,還在酒吧里睡著了。
以前,他想像過自由的各種感覺,只是沒想過有一天自己也會覺得枯燥。鼓浪嶼去了十幾次,實在是不想再去了,海鮮吃了三個月,再聞到也有點想吐了。而且外面人太多,他寧願待在酒店裡,但整天睡覺、點外賣、看劇也很無聊,到最後,他對於時間已經沒有了概念,只知道早晚,不知道幾月幾號,也不知星期幾,需要通過觀察路上的行人來決定自己穿什麼衣服。
有那麼一個星期,他什麼也不干,呈大字躺在床上,就靠回想過往來度日。他開始意識到一個道理,「人是一種社會化的動物,脫離了社會、啥都不用擔憂的人,是不可能長期生存下去的。」
終於,房子在還有三個月到期時,他拿上行李離開,決定重新找份工作。
自由的反面,有時候並不是不自由,而是過度自由。並不是只有吳磊感受到了空虛。北京望京地區拆遷的時候,李朝元一家人分得了5套回遷房,如今算起來全家的房產已經價值3000萬,「當時我弟弟結婚,辦的婚禮酒席直接選在國家會議中心,就是整個村子的人覺得一下子富起來了,一定要有排面。」他自己也不工作,在家玩了一整年,「每天就是打牌、打牌、打牌,那一年光打牌就輸了十幾萬,就是感覺整個人都廢了。」
那是一段徹底與社會脫節的日子,「以前單位的朋友有的跟我還有聯繫,但話已經說不到一起去了……再後來我連牌也懶得打了,就覺得整個人跟條魚缸里的魚沒什麼區別,反正每天都有人來餵自己。」
另一方面,在「用利息生活」小組裡,每個人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通貨膨脹速度。對於這些相當看中自己本金的人們來說,沒有什麼比本金的縮水更令人擔憂的了。這也讓這種原本看上去自由的生活方式,籠罩了一層不自由的陰影。
在同自由和不自由進行抗爭的同時,人們其實也在同恐懼抗爭。暴富的李朝元最終也找到了自己的克服恐懼之路。他出錢將北京密雲的一座院子改造成了農家樂,從買磚、砌牆、到院子裡挖個小魚池,他都親自動手,不懂的就請裝修工來教,在那半年裡,他學到了裝修的技能,感到了久違的充實。
如今,農家樂生意不溫不火,收支勉強持平,利潤甚至比不過他用拆遷款買理財的收益的零頭,但他覺得有意思。淡季時,常常院子裡只有李朝元一個人。他每天都會給自己燒水泡茶喝——不用電爐子,用煤爐,泡個茶能磨嘰一個小時。
以前的他可能想不到,這就是他的「用利息生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