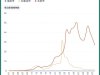昨天,壬午的一篇文章洗版後被404了。
然後,文章被404這事繼續洗版。
再然後,這篇被404了404次的文章,又第405次從其他角落重生,手手傳閱。像極了1976年的天門山詩抄,被緊密查禁,查著禁著就禁成了那個時代的象徵。
還是說回文章吧。
文章主人公是一名女醫生,某醫院某科主任。她是第一個圈出新冠病毒的醫生,也是第一個往牆外扔紙片的人。
接下來的故事,人們已經「審美疲勞」,談話、訓誡、檢討……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甚至可以悲觀地說一句,從新聞的角度來看,這篇新聞「沒有新聞」。就像在《1917》中,死亡已無法刺激士兵的神經。
這篇稿子真正令人觸動的地方在於女醫生道歉了。
是的,女醫生是救人者,她道歉了。
女醫生很早就知道實情,是第一個在病毒上畫紅圈的人。
然後因為傳紙條一事被約談。
這次約談頗有火藥味,女醫生情緒極受打擊,以致後來再有人問病毒的事,她只能閉口不言。
但當她看到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她後悔了。她後悔當初沒有再勇敢一點,沒有再多告訴一個人。
事實上,她不是在後悔,她是在道歉。是向身邊那些去世的同事、向所有去世的人們道歉。
她的一位同學跟她說對不起,因為同學把她發給他的信息發出去了,給她惹來麻煩。
但她說,她最想聽到的道歉,始終沒人開口。
這很正常。
因為,只有救人者才會道歉。只有救人者眼中才有一個個人,才會真正的為那些逝去生命道歉。
女醫生「道歉」的這一幕,讓我又想起《辛德勒的名單》。
商人辛德勒幾乎耗盡家財,從納粹的槍口下「買回」1100多條猶太人的生命。
這本是一件傳揚百世的無量功德。我確信,辛德勒內心也為自己的壯舉驕傲。
但是他沒有要求感恩戴德。
「你們當中的許多人曾來向我表達謝意。該感謝你們自己。」
他甚至自稱罪犯,自貶為剝削者,請求這1100多名猶太工人原諒。
「我是罪犯。你們將獲得自由,而我將被捕。午夜過後,我不得不逃亡。」
他帶著幾分自嘲、假裝輕鬆地對著工人發表最後演講。
午夜終至,所有猶太工人自發站在大門口為他送行。工廠經理代表工人們送上一枚金戒指——由一位老猶太人獻出的金牙鑄成。
戒指刻著一希伯來名言:「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
曾在德軍面前談笑風生面不改色的辛德勒,聽完這句話手一顫,戒指掉在地上,他連忙蹲下身撿起戒指,鄭重地戴進手指,突然痛哭流涕。
他並不驕傲。他並不以自己救了1100條生命而驕傲。他為自己無力救更多人而悔恨和道歉。
他不斷地念叨,一枚勳章可以多救2個人、一輛汽車可以多救10個人。他恨自己揮霍錢財,恨自己沒有賺更多的錢。
對於這一場戲,曾有人評論過於矯情和刻意,不符合辛德勒一向瀟灑倜儻的人設。
這並不刻意,這就是最高貴的人性,真正高貴的人。
真正的救世主,只會痛恨自己太過渺小,而不會以偉大自居。生與死不是正和負,兩者相加不會等於零。
在「內疚」這件事上,同為救人者的辛德勒與女醫生是相同的。
辛德勒內疚沒有錢可以買更多人命,而女醫生內疚沒有勇氣往牆外扔更多石頭。
他們的眼中,都有死去的那些人的影子。
辛德勒沒有忘記那個紅衣的女孩。女醫生也沒有忘記,搶救李醫生的那一夜,從她的科室借了一隻心臟起壓器。
他們的眼中,也有倖存者的筋疲力盡。
女醫生聽說有醫生同事想轉行,她自己也開始認真地考慮,是否回家當一名家庭主婦。
辛德勒的汽車緩緩駛出人群,沒有聽到歡呼聲,也沒有聽到哭聲,倖存者疲憊麻木的臉映在車玻璃里,與辛德勒的淚光彼此交融。

那1100多名猶太人,目送著辛德勒的小車消失在夜幕里,再也沒有力氣走回工廠,而是就地臥倒,等待黎明的到來。
天亮了,度過黑夜的猶太人們像屍體一樣橫七豎八躺著。
一名蘇聯士兵騎著戰馬,嘀嗒嘀嗒,緩緩走進工廠門口,對著這群「活死人」,自豪地宣布:
「你們被蘇維埃軍隊解放了。」
一片靜寂。這名士兵耳中沒有傳來想像中的歡呼。猶太人經理慢慢走近士兵,問他:
「你們去波蘭了嗎?」
「我剛從那邊過來。」士兵愉快地回答。
「那裡還有猶太人嗎?」
這位士兵張大嘴巴,一言不發。另一名猶太人又問:
「我們要去哪裡?」
這位士兵猶豫片刻後回答,建議他們不要往東,那裡仇視猶太人,「但如果我是你們,我也不會往西。」士兵強調。
換言之,對於倖存者而言,問方向性的大問題太過奢侈,最好關注當下的生存問題。所以,當猶太人問有沒有食物時,士兵指了指不遠處,說出了他此行最有價值的一句話:
「那裡不就有一個小鎮?」
戰戰兢兢的猶太人聽完這個消息,一字並排鋪開,奔向自由的小鎮。
若干天后,片中的德軍殺人惡魔阿蒙歌德被判處絞刑。行刑之前,阿蒙的遺言是:「希T勒萬歲!」
很明顯,這不是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