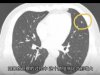我的母親相信,上帝和中國共產黨將會擊退新冠病毒。
「為武漢祈禱,為中國祈禱,」她敦促我。武漢是湖北省省會,疫情的最初暴發地。那是2月初,武漢封城已有一個多星期。母親生活在我的家鄉城市,所屬省份與湖北相鄰。與中國大部分地區一樣,這裡也採取了隔離措施。但相對來說,她是安全的;眼看著危機在中國蔓延開來時,這一點給我帶來自私的安慰:我是她唯一的孩子,生活在病毒幾乎還未觸及的地球另一端。
1月末以來,每天早上,我在芝加哥一醒來都會看到母親發來的一長串消息。郵件和簡訊會一直延續到午飯時間;有時在下午也會跳出來,這時我就知道,她又度過一個不眠之夜。
母親給我轉發中共官方媒體的報導,說政府如何快速行動抗擊病毒。她發來與朋友的對話截圖,他們討論隔離的生活,以及如何勸服不守規矩的親人待在家中。
她還會給我發來《聖經》的摘選,分享教會的禱詞。隨著室內聚會取消,母親常去的那座經國家批准的教堂將禮拜移到了線上。牧師通過萬能的中國通訊軟體微信來布道,教徒也用它來相互問候關照。
母親是一名退休小學教師。我曾經也是她的學生。在我加入共產黨的青少年組織少先隊後,她教會我唱國歌、系紅領巾。1990年代末,兒時的我一天天地坐在她的課堂上,她的課教習漢字,同時也引入歷史與思政教育。我從未懷疑,母親真心相信自己所教的內容,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也相信。
政府發放的教材如此簡單,卻包含了分別好壞及如何賦予人生意義的所有答案。黨是好的;不服從是壞的。為國家和人民服務是人生的最崇高形式。
然而,儘管 愛國(黨)教育講述了那麼多革命烈士的故事,卻從未教人如何哀悼逝者。20年前,父親突然離世後,母親開始去教堂。她在我們倆的枕頭下各放一本《聖經》,我們每次旅行時她也都帶著。我那時10歲,對於神的存在感到踟躕矛盾,但每晚還是與她一起做睡前禱告。我並沒有選擇的權利。
2009年夏天,我離開中國到美國讀研究生,之後留下來工作生活。在老家的孤單生活中,母親越來越虔誠。對上帝訴說能安撫她的渴念。
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強威權控制,取締共產黨視野之外的穆斯林少數族裔和地下教會。有時我會想,會不會有一天母親要被迫在上帝和黨之間做出選擇?她腦中是否閃過這個可能性呢?
在我母親這代人的成長歲月里,所有舶來的信仰都是異端邪說,所有傳統宗教都是迷信。當中國擺脫政治狂熱的深淵重獲新生時,共產黨學到了寶貴的一課:面對無法根除的人性慾望,不論是對物質財富的追求,還是精神安慰的需求,招安比打壓要有效得多。
個人住所里的私密宗教團體是可疑的,因為這樣的組織力量可以被用作政治目的。但城市中心的大型教堂,比如母親去的那座,則懂得如何不引起政府的反感。
母親不認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政治忠誠有任何矛盾之處。「所有的政府都為了人民好,」她說,「而每個年齡段的人都要相信點什麼。」
12月末,第一例Covid-19病例在武漢通報確診,1月初確認病毒人傳人。然而,由於懼怕社會混亂與政治負面影響,中國官員隱瞞了信息。瞞報的情況曝光後引起了劇烈震盪。很多人在網上表達憤怒,要求信息透明和問責。
在武漢封鎖早期,像「#我要言論自由」這樣的話題成為熱門——瀏覽中國社交媒體的時候,我想著,也許可以趁機上一堂課。當然,我並未抱有幻想,認為一時盛行的不滿可以演變為一場更廣泛的政治覺醒。但如果目標對象僅僅是一個人,我也許能取得一定進展,也許能幫助母親意識到她所崇拜的政府並非無可非議。
面對我列出的疫情初期官方欺瞞和應對不當的證據,母親一一做出解釋。政府並沒有隱瞞;病毒有兩個星期的潛伏期。封鎖沒有太遲;大家需要時間回自己的家鄉。封城是武漢居民所樂見的,城市裡生活一如往常。
母親對黨的俯首帖耳讓我感到難以置信。她察覺到了我的氣惱。「這不是你的錯,」她用一種柔和到近乎陌生的語氣說,「你走了太久。你被西方媒體誤導了。」
母親只讀中文,也不知道如何翻越中國的防火長城。但即便是接受同樣的信息,我們的反應依然會大相逕庭。
母親看到武漢臨時醫院施工的神速,為中國效率喝彩;我卻擔心為了趕上吹捧過度的工期而埋下安全問題。母親看到一夜之間冒出來的路邊檢查點和社區巡邏,稱讚政府工作的細緻;我則思忖國家在多大程度上借公共危機來擴大其監控權力。
軍隊力量被派往武漢支援,再次激起母親對軍隊的崇拜:她年輕時一度夢想穿上軍裝。我則以深切懷疑的態度看待所有的國家暴力工具,並相信將資源用在教育和醫療上會使人民受惠更多。
「你是否考慮過這樣的可能性:政府可以使用它的權力來實施傷害,包括針對自己的人民?」我給母親這樣寫道。
「你思考得很徹底,問的問題也很有意思,」她回答說,「上帝懲罰作惡的人。如果人民聽從上帝,他們會受到保護。」
我無法分辨,她這是在把上帝當作對國家權力的終極制約,還是暗示國家如同上帝,不容質疑。
「難道你不記得30年前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嗎?」我感覺這些話語在我的指尖灼燒,但我克制了打字的手。天安門事件的話題在中國被禁。我轉而引用納粹德國的例子,闡述國家權力不受約束的危險和普通人的共謀。
「如果有空,你可以讀讀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我提議說,「她的書有譯本,而且不難找。」
母親回復確認阿倫特的中文譯名。「如果女兒向我推薦,我一定會讀的。你是博士,而我從來沒上過大學。」

母親告訴我,她炒了一盤橘子皮。那是2月中旬。她已經兩個星期沒有離開公寓了,蔬菜也所剩無幾。
「我在網上搜了。橘子皮富含維生素!」她慶幸自己的機智:「我太聰明了。出去太危險了。」
我被負罪感包裹。我意識到自己沒有問過母親她的情況。我關注家鄉的病例統計,算著她被感染的機率。我從她每天發的消息數量和長度,來猜測她的大抵身體狀況:她花這麼多時間在線,精力一定不錯!我告訴自己,她住在一個安全的區域,周圍商店眾多,附近有親有友,再說她還有教會和互助小組。
我自視這是保持理智,並尊重她的自主權,以安撫自己的良心。我將我們每天關於疫情的交流變成了隨時隨機的哲學和政府管理課。但也許,我訴諸邏輯、數學和爭辯,是因為我不敢面對那不可避免的時間詛咒,不敢過多去想母親身體每況愈下的前景。
母親對更高權力的信念堅定不移,這讓我不安;這意味著她在順從。她相信。她重述被灌輸的話。她將憤怒和不滿置之一邊。
從我能記事起,母親一直是憤怒的。她憤怒於父母偏愛他們的兒子。她對自己的兄弟感到憤怒,因為他們被過度寵溺。在父親生前,她也生他的氣,而他過世後她則對自己不珍惜有他的日子而憤怒。她氣工作場合恃強凌弱的同事,氣班上吵鬧的學生,也氣街上多收她錢的商販。她對我發怒,隨便什麼理由,或者乾脆沒有理由。
我從來沒有屈服於她的憤怒,但儘早離開了家門。我在自己和母親的脾氣之間放置了一片海洋和兩道國門。
搬到美國不久,她就開始請求我的原諒。她稱頌上帝打開了自己的雙眼,讓她看清自己的罪行,並一再為自己以前對待我的方式道歉。「把我當作你所有不快的出氣口!」她要求我,「把所有的髒水、髒字潑向我吧!」我不認為母親相信復仇是伸張正義的方式,但在她懇求被懲罰的行為中,我看到了她的自我憎恨:她如此厭惡自己,因為她曾一再傷害的人是她最珍視的唯一的孩子。
多年來,母親一再向我表達搬來跟我一起住的心願。我告訴她,這不現實。她不會說這裡的語言,在美國也沒有朋友。我作為學者資歷尚淺,工作不穩定,工時也很長。這都不要緊,母親說:只要跟我在一起,她就滿足了。她會給我打掃做飯。她有積蓄和退休金。她不會成為負累。她只是想幫忙。她嘗試給出無條件的愛:我的一切,能為你所用的,都是你的。
我試圖向她解釋,母親可不是傭人。情感依賴是不健康的。請培養個愛好吧。請為自己而活吧。我知道,母親將我的建議視作徹底的拒絕——她得找到自己的生活,因為她的生活已經不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這大半年來,母親一反常態地熱切關注全球事務,這不是出於新發現的興趣,而是再次嘗試跟我交流並糾正我的錯誤觀念。我為英文出版物撰寫中國政治與社會相關的文章,而且常常批評中國政府的濫權。因為清楚中國政府如何向批評者和他們的親友施壓,我從未向母親提及過這些文章:反正她也無法閱讀;語言障礙和我們之間的物理距離,應該可以保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