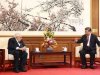邵燕祥仙逝,友人傳我一件簽名信照片,因為邵公乃是當年第一簽名者。
這次簽名事件,據說誘發了震驚世界的八九學潮,學潮又「誘發」了鄧小平的大屠殺,屠殺又「誘發」了大開國門並「起飛」,繼而造就了中共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強大,也鑄成一個超強集權,並使西方第一次覺醒「落後」,於是奮起「滅共」。此間意義極豐富,但是脈絡和演變,眼花繚亂,頗顯示中國當代史的破碎和偶然性,參與者雖不乏大名鼎鼎者,卻都是偶然跨進一扇門,有的終身改變,有的回到原位,當中自有說不盡的好故事。我引入一篇舊文,說說花絮。

一、社會名流發聲
『安徽、上海、溫州、紹興、杭州、湖南,整整40天奔波下來,攝製組人人精疲力竭,加上年關迫近,導演夏駿決定「班師回朝」。
『春節後,五集腳本的草稿已齊,我的任務是修改潤色。夏駿忙著趕拍北京的資料——沙灘紅樓、天安門、菜市口、松筠庵、湖南會館、魯迅故居……劉東已經鑽回他的宋朝。錢鋼忙著同戴晴等12名記者和一群專家學者,為拯救將會被腰斬的長江而奔走呼號。
『一日下午,大名鼎鼎的詩人北島光臨寒舍,極鄭重地遞給我一封聯名信,文字極短,大意是今年為建國40周年和五四運動70周年,為創造一個和諧的改革環境,建議全國人大對政治犯實行大赦。文後已有十幾個簽名,全是首都文化界的名流,真可謂群星薈萃。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當下讓我只覺得北島能來找我,乃是看得起我。於是不假思索地簽了字。』
上面幾個段落,文字來自我的一篇報導文學《世紀末回眸——關於一部電視片的流產記錄》,敘述我們拍攝《河殤》續集《五四》的過程,刊於1989年5月號上海《文匯》月刊,我的照片還上了封面,可是下個月北京就發生「六四」大屠殺,這本全國著名的第一流文學期刊,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封掉,再也沒有復活。
這裡可議的是:
1、三十年前,一個詩人可以聯袂名流,施壓執政者大赦政治犯;
2、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簽名敏感呼籲,非但無恐懼,且是一樁時髦;
3、當年作家詩人們,對於政治參與,年輕者有錦上添花心態,老輩者則無此需求,反而是一種社會責任;
4、每一個人,無關社會地位,仍然需要勇氣,但是都是「孤膽」,而且要承擔後果。
二、知識分子最怕「海外反動勢力」
『未料此事惹出軒然大波,讓我感到大惑不解,就跑到馬路對面社科院宿舍李澤厚先生家(他也是簽名者)向他請教,他也正在納悶,說公民向全國人大提出某項建議是憲法允許的,與司法程序風馬牛不相及嘛。況且,簽名者當中還確有幾位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建議是否採納悉聽尊便,但提建議本身何罪之有?
『那幾日空氣頗為緊張,謠傳也多了起來,說某某後悔啦,某某檢討啦,某某失去自由啦,令人有「下雪別忘穿棉襖」之感。我卻不去理會,只關在家裡改稿,反正也沒有「鬼敲門」。
『後來聽一些來訪者說又出了第二封42人簽名信,接著又出了第三封43人的信,海外也鬧得沸沸揚揚。我既沒出去走動,也沒報紙可看(報上似乎對此緘默不語,作「無聞」處理),寫稿寫累了想起此事,只覺得幾個知識分子提了點意見或建議,又沒有觸犯黨規國法,何故如此敏惑?
『中國政治舞檯曆來是爭鬥得極為殘酷,政治上的失敗者總要落到囚徒的境地,遠的不說,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陶鑄等等,哪一個不是死於非命?政見不同,黨內有之,黨外也有,倘不是人人覺得如斗不過對方就會遭難,便不會那樣「烏眼雞」似的你不饒我我不饒你。所以取消對政治問題定罪,對任何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大顯身手的人來說都大有好處,政治鬥爭也會變得溫和、文明、規矩起來。這有什麼不好呢?』
還有人記得「下雪別忘穿棉襖」這個句子嗎?
八十年代,當局應對的方式,或上門打招呼,或找人談話,但是殺手鐧,是說這個簽名信有「海外反動勢力在背後操縱」,並通過宣傳工具大造輿論,這一手非常奏效,一棒就打趴了大多數年長者的精神,他們多為「民族主義者」,留過洋,文革中吃足了「裡通外國」的罪,簽名者中有些老知識分子表示悔意,冰心說自己是不了解情況才簽了名。
時至今日,那個殺手鐧還很管用嗎?我已去國三十年,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中共在屠殺失去「執政合法性」之後,撿起「民族主義」這個破爛貨,乃是極高明的一招,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無論老少,都難過」愛國主義「這一關,而知識分子是中國的」四民之首「,統治了他們就能統治中國,種地做工的老百姓,是不知道」愛國主義「幾錢一斤的。
三、中國急不得?
『我正這裡瞎琢磨呢,夏駿忽然神色惶惶帶來一個消息一下子把我打懵了:
「剛剛接到電話,部里指示這部片子立即停下來。財務科也停止撥款了!」
「為什麼?部里怎麼指示的?」
「不清楚。都怪你們去簽那個名?"
『你們?——我恍然想起,參與這片子的顧問李澤厚、龐朴、金觀濤劉青峰夫婦都簽了名,撰搞人中劉東、王焱和我也簽了名。噫唏!大伙兒簽名時大概都沒想到還有這部片子牽掛著呢。
『是不是這個緣故,我還不敢斷定。《河殤》之後想再搞一部類似的片子,我總懷疑我們有些異想天開,得隴望蜀了,但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半載心血、滿紙宏論、無數畫面連同那上萬里路的風塵,眼見要付之東流。我這才覺得很對不住夏駿和他的攝影師們。這些小伙子春節後抬著機器滿北京跑,直到兜里只剩下一塊七角錢才停機,連晚飯都不知到哪裡去混一頓……。
『不幾日見劉東,我對他說:「夥計,你不總說中國急不得,需要一劑治本的緩藥嗎?現在可好,咱這緩藥還沒熬成,一著急全砸鍋了!」
胖子漲紅了臉,憨笑不語。』
那封簽名信,我到三十年後,才因為邵燕祥的逝去,而得以重見。北島也多年未聞音訊,聽說他只能住在香港,可以進大陸去開會,但不准居留下來。共產黨很記仇,他們大概至今不原諒北島那次領銜、徵集簽名。
到此我才想起,當年北島光臨寒舍,身後還跟了一人,小個子,也是詩人,不久又跟我在巴黎邂逅,還一起在索邦大學學法語,誰知他後來瘋了,流浪失蹤二十年,前不久才終於回了故鄉。他就是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