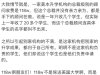2021年8月5日,中國探險協會發布聲明稱,該協會近期組織的青少年騰格里沙漠探險項目發生意外,一名16歲北京學生不幸身亡。
這起悲劇中的周邊信息引人注意:這名學生參加探險,原本是為了出國留學。中國探險協會官網的一篇文章稱,該活動有助於「提升文書的亮點,讓招生官記住獨一無二的你」。一名同班同學在媒體採訪中稱,「大多數人參加這個活動,就是為了出國留學加分,並不是喜歡戶外運動。」
2021年6月,深圳某留學機構發布了一則廣告,宣稱學員付費1.58萬元,就能參加一項「女工賦權項目」。該項目將在紡織廠、電子廠等地開展為期一周的調研,相應地,學員將獲得一篇被視為「學術成果」的調研報告、一封導師推薦信、一張項目結業證書。
這則廣告引發巨大爭議——青年人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商業化包裝運作以及申請大學的功利心驅動下,該項目將對女工群體的人文關懷,異化為給履歷鍍金的工具。
這兩項活動都與留學仲介市場中的商業概念「背景提升」有關。在國外精英大學,尤其是美國本科的申請中,除了托福、SAT、ACT等標化考試成績,學生還需要提交個人陳述等文書、在網申系統中填寫10項課外活動。一些不可量化的——更關乎「學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指標——也被納入考察,比如社區參與、對少數群體的關懷、領導力,以及是否一個「好的公民」。
准留學生們的「人設」,成為可以被包裝和打造的生意。仲介機構通過提供付費科研、實習、公益等活動,提升學生在申請階段的「軟實習」。在競爭激烈的賽道上,為了讓簡歷脫穎而出,不至於淹沒在雪花般海量的申請材料中,一些申請者報名參加看上去「高大上」的活動,以此讓考官眼前一亮——比如去北極科考、到尼泊爾為窮人造房子。而在西方受推崇的議題則更能抓人眼球,比如為少數民族婦女賦權、為社會邊緣群體發聲等。那些僅靠身邊有限資源腳踏實地申請的人,則逐漸捲入留學申請消費化的不安和隱憂中。
「升學助力」
18歲的王波是西南某二線城市一所民辦學校國際部的高中畢業生。她扎馬尾、戴框架眼鏡,坦蕩地露出額頭。
自高一入學起,王波時常被裹挾在一種焦慮的氛圍中。她所在的學校,是一所集活動、考培、留學申請於一體的國際學校。王波是從國內教育體系升上來的學生,國外大學的申請制對她來說是全然陌生的體系。「做活動」的重要性,常被校長、老師掛在嘴邊,「沒有好的文書、活動經歷,光靠學習成績是申不上好大學的」。
陳彬傑是成都一家留學服務機構的負責人,從業已超過十年。他認為目前市面上的背景提升項目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由留學機構根據學生自身的興趣、經歷,規劃出可以長期參與的課外實踐活動;一類由專做背景提升的第三方機構「外包」。還有一類是與國際學校或公私立學校的國際部合作,簽約成功後學校將獲得佣金,「一般來講,返傭點在20%-30%不等」。
陳彬傑注意到,2013-2014年開始,越來越多學生想去國外本科讀名校。2016-2018年是去美國讀本科「井噴式」的三年。國內留學市場的供方也從最初幫學生做留學服務和指導的機構,發展出越來越多第三方背景提昇平台、科研平台。
讓王波印象最深的是,當時學校經常開分享會,「類似普高的早會」,並邀請家長參加。在學校禮堂,老師會細數常春藤名校的光輝歷史,反覆強調低分高錄的極端案例——比如一位學生成績並不出彩,但依靠保護海龜的經歷和文書包裝,最終被海外名校錄取。這讓王波產生了錯覺:「它會在潛意識讓你覺得,就算我學習不努力,只要活動做得特別好,一樣可以進這麼好的學校。」
學校為每一位學生配備了一名活動導師,在家長也在的專屬微信群中,導師經常推薦一些背景提升活動。「含金量」是最愛使用的詞彙——「它要麼是把含金量具體化,說這個項目能讓你產出一篇高質量,並且能夠保證發表的文章,或者就把含金量三個字打在那裡,也不作解釋,但就說我們這個活動能給你提供非常大的升學助力。」王波對記者說。
許多定位高端的項目極具誘惑力。陳彬傑以科研為例,平台通常會以每小時500美元酬勞邀請海外名校的退休教授或是兼職教授,帶準備申請的學生做科研項目。「如果想學醫,他們就研究一些本科大三、大四學生才會研究的話題,比如神經科學、生物酶、帕金森疾病。」
王波的一位同班同學告訴記者,最讓她感到壓力的是和校長的面談。那時,校長和四五位老師會親自坐在她和家長對面,反覆強調:美國本科申請需要填10個課外活動,如果手上數目不多,「就會輸在起跑線上」。
「他們會給你施加壓力,讓你非常擔心。我不知道自己假期做什麼的話,先試一試學校提供的項目,就以這種心態參加了。」王波對記者說。
曾擔任過哲學夏令營導師的海外傳播學博士生劉舸看見某公眾號推送了一則廣告宣傳「科研項目」,號稱會有「神仙級別教授陣容」來輔導學生,學生可以與「世界上最頂尖的學者們一起做科研」。課程結束後,還有機會「以學生自己的名字」在國際學術期刊上面發表論文。該項目報名費高達四五萬元,而論文發表則需要另交幾百美元。
他查閱了該機構過往的發表成果,發現這些學科五花八門的文章都發表在了同一本英文期刊上,過刊上作者全是中國的高中生和本科生。「國外招生官也不是大傻瓜,這種套路想必他們也非常清楚」。
陳彬傑認為,許多打著名校教授頭銜的高端科研項目甚至讓高中生以第一作者發文,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雖然不排除有學生有這樣的能力,但批量化生產後,「尤其當它成了一個可高度複製、較低篩選門檻的市場化產品,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我們所有人都在向國外招生官傳遞一個信息,你們本科生都做不到的時候,我們高中生就可以做到,而且還是跟你們國家的頂尖名校一起做項目」。
「台前的表演」
2019年1月,王波到成都一寺廟參加學校根據她感興趣的心理學推薦的一項有關「僧侶幸福感」的調研報告。這次調研時長不到一周,收費接近兩萬元。王波不屬於富裕家庭的孩子,覺得價格貴,導師告訴她:「市場上差不多都是這個價格,不用驚訝。」
王波的媽媽屬於服務型勞模母親——只要為了孩子好,辛苦一點都願意。當時學校有意無意暗示,其他學生已經報名交費,王波知道以母親的性格,肯定不願女兒受委屈。「她可能會扣一點家裡的生活費,或者問親戚朋友借點,讓我能享受到跟其他人一樣的機會和條件。」
回想那次寺廟的調研活動,王波覺得「不值」。她向記者介紹了日程安排:第一天抵達成都;第二天一位北師大心理學系在職的老師給參與者傳授基礎調研知識;第三天、第四天,採訪;最後一天,產出一篇「類似小作文的東西」,整個調研就此結束。
王波高三時自學過心理學,她認為要掌握專業的社會調研方法,至少得上5-10節課。但在寺廟的「調研」更多是在路上攔住一位行色匆匆的僧侶,跟著他一路小跑,追問:「你覺得幸福感是什麼?」對方通常一臉懵,敷衍地答一句。她最終以「從僧侶的處世態度之中學會了什麼」為感想,寫作了一篇「遊記式散文」。
王波的同學則參加了一個到貴州的山村小學熬紅糖的項目。活動打著「非遺保護」名頭,帶領學生「傳承古法紅糖技藝」,收費一萬多元。同學回來後反饋:「就是把我關到山溝溝里,被蚊子咬了三天,學一下紅糖製作,最後拿了一瓶紅糖回來。」
「這有點類似於台前的表演,實際上深入的問題沒有被解決。學生也受苦,還沒有產生任何實際效益,只是拿了一張證書。關注紅糖技藝是好的,但不是一群學生來學怎麼做。」王波對記者說。
唯一把紅糖項目認真做下來的是一位後期選擇商科的學生。他為當地村民的紅糖尋找銷路,在朋友圈售賣,籌集的資金最終捐給了貴州山區學校。「但大部分人就是去熬了一下紅糖,把紅糖拿回家。」
來自雲南昆明某中學國際部的畢業生胡嘉桐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她對多元文化教育感興趣,曾花費近四萬元參加過一個尼泊爾遊學項目。按照活動手冊介紹,他們將去當地學校調研、採訪,了解異國學制、課程模式,還有5天時間自主設計課程教書。在她的想像中,這是一次深度了解尼泊爾教育體制的調研機會。「但十多天的行程里,至少有九天都在拍照,在加德滿都的景區打卡」。到了學校後,受制於語言,參與者只能簡單地參觀課堂,和當地學生隨便聊了一下就走了。這段費用高昂的經歷並沒有讓她產生任何感想,最終也沒有寫進申請文書中。
王波記得,學校曾組織學生參加過一次某銀行的「精英實踐實習項目」。當時銀行定製了一個得分表,得分達到90及以上的人,將得到由行長親自簽名的實習通知書。「你通過自己的努力只能達到60分左右,後面的得分需要定期存款,或者購買理財投資產品才能得到。當時有學生家長真的存了巨額進去。」
班裡一位做活動最積極的同學甚至到了病態的程度,「她學習成績不好,把希望押在了做活動上。」她喜歡打探周圍的同學都做了哪些活動,也會焦慮地找活動導師推薦。她曾找到一位山區貧困學生,每個月資助對方,還親自去當地,請人拍下捐款的珍貴瞬間,「她把錢交到對方手上,兩個人都在笑,發到公眾號上作為證據,她確實做了這件事。」
「如果項目設計得非常好,把它執行出來,孩子就能學到很多。但是如果項目設計得沒有那麼好,或者以結果為導向,就很容易發生孩子也不知道怎麼做,完成任務一切就結束了。」北京某留學諮詢機構創始人Theo對記者說。
在Theo看來,付費購買並不是引發背景提升行業亂象爭議的核心,重要的是,學生是否真的熱愛,以及真的做了事。比如有一位學生很關注視障人士,因為父母都是眼科醫生,外公有眼疾。後來在各種機構的幫助下,他做出了一款幫助視障人群的App,有視障患者反饋確實有幫助。「這種熱情是真實的、天然的,不是被改造的,也不是表演的。但做App不是他的想法,是他得到幫助之後的想法。」
「是不是發自內心願意做」
王波和胡嘉桐參加的這一類「華而不實」的背景提升活動,正是國內部分留學機構藉助信息差製造的商業噱頭。
「從國外大學來講,特別是針對美國的申請,它只需要一部分申請材料幫助招生官了解,學生除了學習以外,怎麼分配和安排自己的時間,最有熱情的領域是什麼,在探索過程中解決了哪些問題,如何突出學生的領導力、團隊合作精神或者社會責任感。」陳彬傑對記者說。
但留學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後,越來越多人想分蛋糕,這個過程中衍生出一些以短平快為商業模式的機構。「比如他們會利用第三方國家非常棘手的問題,不管是衛生、環境、貧困還是教育,給學生制定一周到十天不等的公益項目。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我覺得算是旅遊,因為不管你是幫助尼泊爾遭受到家暴的婦女,還是去非洲幫助動物保護,一個高中生他能做什麼?這更像是課外為時不多的體驗和遊戲,或者是幫助建立認知的過程。」陳彬傑對記者說。一旦有參與的學生成功被名校錄取,就會成為機構大書特書的對象。「這是打了一個信息差,因為學生能否成功錄取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機構以這種方式製造市場的假象。」
王波所在的西南二線城市,信息相對一線城市更加閉塞。「信息不對等是有時效的,比如北上廣這樣的老牌留學輸出地,至少輸出了十年以上的學生,他們周圍輻射到的人可能會更多。越小的地方,它的信息不透明度就越高,我們也不知道哪裡能獲得信息。」
陳彬傑的一位朋友做過藤校面試官,對方分享過一個故事。面試時,有學生說自己去尼泊爾建了一所學校,自己召集了當地老師,給學生上課。面試官聽了立刻覺得不對勁,追問下去,發現這名學生講不出任何細節。他面試了好幾個學生,說的都是大同小異的經歷。「從他的角度就會覺得,這一群學生全是不可信的」,陳彬傑覺得,這屬於「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前普林斯頓大學校友面試官雪麑曾於2007年-2014年在中國香港地區和華北地區負責校友面試。她面試過一位名叫Brian的理科小學霸,來自北京某頂尖公立學校,笑容很有感染力。雪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胸有成竹的樣子和非常到位的面部及肢體語言很明顯是在鏡子前反覆練習過的,不過,他發揮得很自然,不會給人假惺惺的感覺。唯一的缺陷是語速太快,仿佛是在奮力地完成一項任務,而不是在用心和我溝通。」
Brian提到他曾帶領高年級學生去一個自閉症治療中心和孩子們互動,從聯繫治療中心到申請學校支持,到招募志願者。雪麑希望聽到更多他和孩子們相處的點點滴滴,Brian對答如流,講起他們一起畫畫、聽音樂的經歷,並侃侃而談自閉症在當下社會是缺乏關注的心理疾病。
聽到他對自閉症的關注,雪麑希望他談談對這個病的了解,國內有哪些治療手段。Brian明顯愣了一下,他思考了半分鐘左右開始語無倫次,試圖搪塞過去。雪麑認為他如果真的關心自閉症問題,不會不花時間深入了解。她沒有立刻打斷,而是靜靜看著他,怎麼給自己圓場。
疫情以前,陳彬傑每年都會參加國外名校針對升學導師的交流會。他問過一些招生官,怎麼看待中國學生花錢提升學術科研背景,「他們也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商業機構把學術化產品做成了產業鏈,他自己學校至少80%以上的教授都接到過類似邀約,當兼職教授帶學生發表論文。但招生官是分得出來的,你有沒有真的花心思去做這件事,你的學術能力有沒有達到你的科研成果呈現出來的學術水平,通過你的文書、你的談吐,能檢驗出來。」
雪麑認為,最重要的是學生是否傳遞出了真實的聲音——「招生官不care你這個經歷是花錢買的,還是你爭取來的。他更care的是孩子是不是發自內心願意做,而且有成長、學習和反思。它不是被包裝上去的。你問他幾句話,他回答不上來深刻的東西,就知道這應該是他功利地為了一個包裝而去做的。」
家庭軟實力競爭
十年前,划船、賽艇在國內還屬於小眾運動,為了讓招生官眼前一亮,有學生會說自己喜歡賽艇。「你去聊,發現他最多就划過一次,那算什麼興趣愛好,正常的practice都不算。」一個孩子說自己養了很多馬。雪麑向記者回憶,「她覺得這是說出來就很棒的一件事。因為可能同學沒有,那時候比較少見,或者父母給她灌輸一些錯誤的信息,養馬就代表上流社會。」
Theo告訴記者,一名學生家長想給孩子報名參加北極科考項目,「他覺得別人都去非洲,我們去北極,牛逼!」當時該北極科考項目在全球每年只招15人,家長覺得這是一個含金量極高的項目。「但如果我是招生官,看到這個活動的第一反應,應該是畫一個問號。這麼短的時間,不管他花費15萬還是1.5萬,我都沒有看到孩子的連貫度和發展的領導力,他在高中之前並未對這個有興趣,申請的專業跟北極科考關係不大,也找不到他為什麼突然之間就想去做這件事的理由,就跑去北極了。」
近些年,一些更「聰明」的父母正努力學習在西方主流社會更為討巧的話語。劍橋大學博士生王婧宜曾聽做新媒體的朋友提起,一位老闆希望花錢請人做一部LGBT題材的紀錄片,因為他的兒子要申請國外的影視專業,「他認為這樣大學肯定能收」。
王婧宜認為,學生與家長的矛盾在於,如果一個孩子想去深圳的工廠進行一到兩周的實地調研,大部分家長並不會答應。但是當這件事情被仲介包裝,有一個漂亮的PPT、名校博士生帶領,還要交昂貴的費用、獲得一封推薦信,家長就會覺得這是好事。這種話語挪用與社會科學學科設立的宗旨本身是相悖的。「社會學就是在批判資本操縱的本質以及結構里的不公平。」
「學校有這個規則,就默認我要用盡各種手段達到它,這樣我才能去上好學校。乍一聽好像合理,可能在高考體系下是沒有問題的,但在海外高校有這種所謂軟實力,個人陳述、軟簡歷,就非常容易摻雜不平等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王婧宜說。
雪麑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式思維誤區。因為長期受應試教育影響,面臨一些非量化考核時,中國家長更在意結果,比如拿到一張證書、學術大牛的推薦信,證明參加過活動,由此導致一些形式主義的現象,以及各種稀奇古怪的小眾偏門活動湧現——那些新奇的、小眾的,別人不會做的活動才能顯得特別——「但其實學校並不在意你做的是什麼。你可以去研究水、研究桌子,更重要的是研究過程中你的學習和反思,你挖得有多深。」
一個孩子對雪麑說,他想去日本學習磨刀,「我說可以啊,北京胡同里也有做糖人的,都是工匠。你可以做一些研究北京民間藝術家的項目,這個孩子順理成章就有一些活動想參加了。這是最正確的規劃。但可惜現在很多家長和家庭跳過了這個過程,直接想買一個結果。但是你去南極,你跟任何其他去南極的人有什麼區別呢,最後還是一模一樣的。」
雪麑如今也在做留學諮詢。她發現很多時候孩子是容易溝通的,難搞的是家長,有時甚至不僅要和父母,還要和爺爺奶奶溝通。「歸根到底,一個孩子未來的走向,其實是整個家庭,甚至是幾代人的縮寫。」
她發現很多有藤校夢的媽媽,能力都很強,但在家中沒有地位,也沒有自己的事業,為了家庭放棄了自己的夢想。「這樣的媽媽是比較恐怖的,因為她把自己的人生價值建立在孩子是否能進藤校上。例如老公給她下的指標,我們家得出一個藤校的,因為我們這個上市公司只配得上藤校的孩子。對於媽媽來講,這就成為她的使命了,她在這個家族是否有用,她整個價值就建立在是否能夠培養出一個優秀藤校孩子的基礎上,這本身就是錯誤的。」
雪麑記得有一位媽媽長得很漂亮,「有富太太的范兒」。年輕時她本可以成為電視台主持人,後來嫁入豪門,生了孩子。她外表光鮮亮麗,但內心是空虛的。「因為身邊的所有朋友都是競爭對手,要跟他們的孩子比。她一切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一些家長的「藤校夢」則是為了彌補自己當年的缺失,「他們不是為了孩子,是為了自己」。比如孩子特別想學藝術,本可以申請一些設計類專業,也容易找工作,「家長說不行,必須要學商,第一學商懂得管理公司,第二就是這個商學院排名更高」。
家長對於申請結果的執著,一部分出於對不確定性的焦慮。「還是因為信息閉塞,以及對招生方法不理解。」雪麑向家長強調利用身邊資源,許多家長表示懷疑:「不可能吧,這麼簡單?」
留學顧問徐阿龍覺得這更像是一種「無法退出的機制」。「這孩子可能就是很普通,但外面也要包裝得非常漂亮、非常華麗。大家都認為這種方式能讓我的孩子在申請上有優勢,如果一個劣幣的孩子在包裝,那扎紮實實在做事的人虧不虧?很多家長都知道腳踏實地的重要性,但在實操過程中,就變成不能讓我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