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查已經進入我們的血液中
騰訊文化:您寫作大概三十年了,在您眼裡文學是怎樣的一種存在?
閻連科:我最初的寫作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逃離土地、要成家。但是真正到了後半生,自己就說不清文學是什麼樣的存在。到這時文學可能真的進入到血液中、生活中,我就是要這樣活著,(於是)就這樣寫下去了。
騰訊文化:提到您的書經常會跟"禁"這個詞聯繫起來,禁與不禁,這中間有邊界嗎?
閻連科:我認為「禁」不是褒義詞,也不是貶義詞。但是我一再強調:一個作家被禁,並不等於他是好作家;一本書被禁也並不等於這本書是好書,不禁也不等於是壞書。一部小說的好與壞要靠小說本身來說明。
我今天的寫作已經不再把握任何邊界,只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和想像能完全飛揚起來。我經常說:別人不解放自己,自己首先要把自己解放出來,沒有任何禁錮、沒有邊界地寫作。這個寫作既包括內容,也包括形式,更多的可能是在藝術上。一個作家不要去審查自己,因為會有很多人幫你審查。
騰訊文化:但是很多人在取材上會不由自主地作出取捨。
閻連科:我一直特別相信一點,中國作家從延安文藝座談會、1949年之後,我們每一個作家血液中都有一個本能的自我審查。就像我們閱讀的課本一樣,從一年級讀書,課本其實是被很多人審查過的,審查已經進入我們的血液中間了,所以這個邊界其實是本能的。
當然,有時自己可能不會發現它的存在,我也是通過寫《丁莊夢》才忽然發現它是自己經過自我審查的一次寫作。這部書不管好與壞,仍然被禁掉了。經過自我審查之後寫出的這樣一部作品,仍然沒有讓廣大讀者進一步閱讀。我已經到了這個年齡,(既然)有人幫我審查,那我就自己解放自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騰訊文化:但是實際上比如說拿《丁莊夢》來說裡面反映的現實可能是您以前作品裡面尺度最大的一部?
閻連科:《丁莊夢》是我最溫情的一次寫作,特別是對人的愛和理解、日常人性的挖掘。這本書被禁掉可能是題材的原因。我想這完全是多此一舉,因為愛滋病問題全世界都已經知道了。
有人說,如果這部小說是別人寫的也許就沒問題,但因為是我寫的,可能就會得到一種特殊的關照。《丁莊夢》給讀者帶來了更多現實意義的思考,但它並不像《受活》《日光流年》那麼有難度。更散文化、更傳統,在小說藝術形式探索上還有欠缺。
我認為這部小說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是值得去禁的,它是一部充分表達主旋律和正能量的小說,人物、故事都充滿了溫暖。禁它的人是一時腦袋糊塗,早晚會醒過來。
騰訊文化:您一直提倡的「神實主義」,在《丁莊夢》裡表現得也並不是太多。
閻連科:「神實主義」這個概念是在寫了《丁莊夢》《風雅頌》之後出現的,但最清晰的出現是在《四書》中,是因為《四書》的那些情節和細節。但是,「神實主義」在這中間有了非常清晰的概念,有了對自己小說的更正,我也希望通過對它的表達給自己的寫作推開一扇新窗。
別的作家都在講荒誕的、魔幻的、現代的、後現代的、黑色幽默的(東西),但你會覺得這些都不準確。我經常說,今天的評論家是相當偷懶的,他們不太去思考用一種新的理論去表達新的小說,總是用舊理論去談新事情。所以,在《四書》之後,我寫了《發現小說》這樣一本書來討論現實主義、二十世紀文學,也提出了「神實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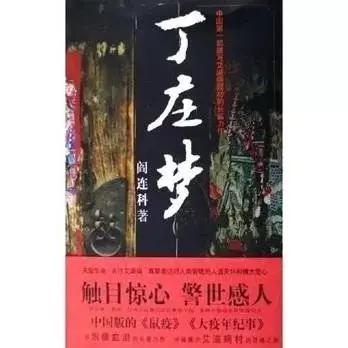
真善美是主旋律假惡丑同樣是
騰訊文化:您怎麼看待人性,特別是幾千年傳統的農耕社會生長出來的人性?
閻連科:第一,人性和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是分不開的。比如,我的青少年時期在非常偏遠的農村,那時會覺得人性充滿溫暖和美好,但是隨著年齡越來越大,經過的事情越來越多,你會發現人情越來越複雜,會看到更多黑暗面。我想這與我的經歷和年齡有關,所以在寫作中也會更清晰地表現人性的複雜性,解剖人性最陰暗的一面。我想這不是表達你對生活的美或不美,而是你認識到人和世界就是這樣。
第二,我們不要簡單地用真善美和假惡丑去理解小說,真善美是主旋律,假惡丑同樣也是主旋律,因為我們把假惡丑呈現給讀者,見證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那也讓人性變得更美好,讓我們更警惕一些東西,它同樣也是一個正能量的作品,我們要正確理解正能量的寬泛性,不能簡單理解為某一點。
騰訊文化:比如《炸裂志》裡這類群體,每當他們走向一個未知的新生活時,對過去基本沒有任何眷戀,並且以前農耕社會留下來的傳統也沒有積澱。比如,您寫到,突然有一天村長想到哭墳的習俗已經忘了很久了。您是怎麼對他們這種表現做判斷的?
閻連科:在我全部的寫作中,《炸裂志》是一部最直接關注中國三十幾年現實的作品。關於農耕文化、改革開放、城鎮化,乃至於中國夢等很多問題在其中都有很大信息量。
今天的社會現實情況是:當我們邁開步子,把改革作為發展,所謂進一步城鎮化和進入現代化時,許多東西都在被迅速地拋棄。比如哭墳的情節,小說最後他們才想起來重新去(哭墳)。
今天的社會在發展的同時,也在迅速拋棄過去。我們恨不得以一夜之間的速度奔向西方的文明,拋掉兩三千年的文明。不管我們怎麼強調國學和傳統,但事實上文明正在被拋棄。
比如,我們到處看到立交橋,但是立交橋墩子下的古文明其實都被拋棄。《炸裂志》非常清晰地表達了這一點。
騰訊文化:您剛才說到的迅速拋棄,知識階層身上也有,王蒙把它總結為弒父弒兄的行為,就是後人不斷地否定前人。
閻連科:我想這是一個全方位的、共同的、有預謀的拋棄,從城市到鄉村,從南方到北方,從知識分子到農民。除了建築問題,還有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的過度崇拜(問題)。我們今天所有的理論都來自於西方理論,而非中國原有的或古典的理論。西方從理論到實踐正在取代我們今天的現實社會,誰都無法阻擋它的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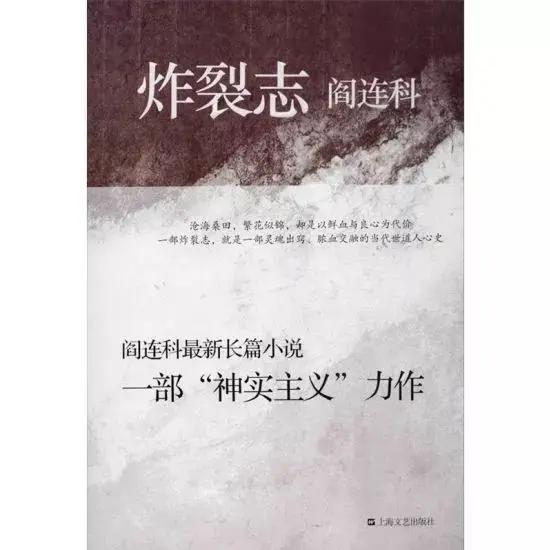
寫《炸裂志》時沒有想到潛規則問題
騰訊文化:小說里的主人公的姓氏安排有什麼寓意?比如姓孔的(孔明亮)帶著全村青壯年去當賊致富,姓朱的(朱穎)帶著全村女人出去賣淫致富,姓程的又依賴于姓孔的。
閻連科:小說畢竟是小說,沒有明確意義,並沒有想得那麼遠。比如,我家在河南嵩縣,家門口就是程頤、程顥,寫《兩程故里》是因為我小時候就在兩程故里讀書。
小說是要講究趣味性的,要給讀者留下更多東西。我讓他姓孔、姓朱,沒什麼明確目的,但是會給讀者帶來更深遠、更複雜的思考。有時寫作的人只要給讀者一滴水,讀者就能從這滴水上看出大海,這滴水必須交給讀者。
就寫作來說,我僅僅是希望交給讀者一個望遠鏡,至於讀者望到哪裡是另一件事。寫作者一定要留給讀者詮釋的空間,否則小說沒有可讀性。今天的讀者是極其智慧、極其會讀小說的,你要留下很多讓他創造的可能性。
騰訊文化:您在小說里給孔明亮的升遷設計了一套官場邏輯,您怎麼看待傳統社會裡權力運行的潛規則?
閻連科:其實我寫的時候沒有想到潛規則的問題。我不可能像《國畫》《羊的門》之類的小說寫得那麼細膩深刻,我的強項其實是放棄那種最真實的東西,而完全用想像抵達另外一種真實。
關於這套線索,我全部的努力就是要講一個好看、豐富、有意義的故事。這個有意義是指讀者在閱讀中,甚至在讀後回想時,會忽然發現故事含有多層意思。
在我的全部寫作中,《炸裂志》是第一次聽到有很多人說:閻老師,我是一口氣把這個小說看完的。它在我整個寫作中確實是最好看的一次,同時它的現實性和探索性也仍然存在。
在這個小說中,我的想像力有可能超過了《受活》《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在《受活》之後的寫作都在原地踏步,但是寫到《四書》《炸裂志》,我想或多或少是有進步的。最明顯的就是小說中的想像更加狂野、飛揚,當然這種想像是非常接地氣的想像。
騰訊文化:在您眼裡什麼是一部好小說,是賣得多,還是寫得好?
閻連科:我想每一部偉大的小說都存在問題。如果一部長篇小說完美無缺,那麼它不會有多大價值。一部小說存在問題根本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有多大的不可替代的創造性。創造性同時也會伴隨巨大的爭論和缺陷。
對我來說,只要你的寫作創造出了別的作者不具備的小說元素,那就是好小說。當然,一個作家每天都在創造,可能一生都沒有創造出一部具有創造性的小說。
小說更多是停留在小說本身,是故事、人物、情節、細節,反映出作家的文學觀和世界觀,給人類帶來思考。小說有沒有價值在於你給這些讀者和批評家留下了多少詮釋空間。你留下的空間越大,作品的意義就越深遠、越深刻、越複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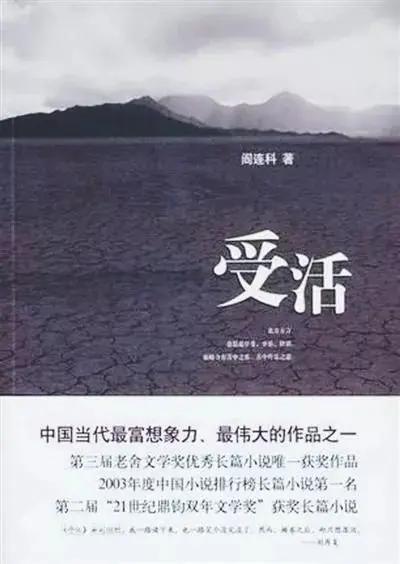
今天每個人內心都極其分裂
騰訊文化:很多西方漢學家都在說中國文化的深層次結構,叫做超穩定。對於您筆下農村文化的超穩定結構,您怎麼認為?
閻連科:西方人在談到超穩定的時候,可能指的是這樣一個社會結構。比如,他們會認為你們有多少人下崗,或者有多高的房價,社會就會崩潰。但這些數字在中國都失去了效應,所以他們認為這是個超穩定的社會。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能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現實。西方所謂的超穩定是從西方經濟學、政治學、科學的數據來對應中國文化,認為是超穩定,其實並不是這樣。
今天的社會最不穩定的是所有的人心,每個人的內心都極其分裂,人性的崩潰已經到了邊緣。這可能是我們最敏感的神經,不被西方人把握,只有我們內心知道。
就像《炸裂志》寫的人心的分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分裂,各個階層的分裂,城鄉的分裂,貧富的分裂,這種分裂已經到了一種神經接近於崩潰的狀態。
但是,中國是一個久遠的、有傳統的社會,有可能某一件事情就把我們統一起來。比如奧運會、釣魚島,就會把很多分裂的情況統一起來。所以一邊是分裂,一邊是有可能挽救緩慢分裂的各種辦法。
我們中國人心最分裂,但也往往容易被某一個事件所吸引,從而進入某一個專注點,這一進入就是五年、十年。我想我們的超穩定可能在這。當有一天我們的人心沒有被統一到一個事上時,那社會就真的崩潰了。
騰訊文化:就拿《炸裂志》裡申請超級大都市的情節來說,他們雖然凝聚到了一塊,但最後的結局是悲劇。您剛才也提到了奧運和釣魚dao。奧運之後,北京的空氣越來越差,70-80%的場館今天都荒廢了;釣魚dao事件,全國上下同心凝力,但事實上很多城市是在打砸搶。把這些投射到書里,超穩定結束之後,是不是都得悲劇收場?
閻連科:文學和生活不能徹底對應。《炸裂志》充滿想像,它的真實感是小說某種精神上的真實感。比如,這個城市最後成為超級大都市之後,一個有野心的人帶著一個城市三千萬的人們朝著西方去。
這是個極其荒誕的情節,但它恰恰表達了剛才我們談到的某一事件和情節,能夠把中國的人心帶到某一個方向。這是不是悲劇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達了今天中國人的心被某一個來自於陰謀的事件所帶領,對應的恰恰是今天中國人內心所有的焦慮和不安。
這部小說的奇妙之處就在於精神上的真實。雖然小說里的很多情節和細節在生活中無法發生,但是我們不會懷疑它不存在。
騰訊文化:您在寫作時,對民族主義狂熱或者是民粹主義有沒有關注?
閻連科:我想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都來自於中國幾十年習慣的革命和運動。在全世界範圍內,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一百年來都處於革命和運動中,即便是搞經濟也是一場運動。這使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迅速地發動起來,被帶到某個地方去,比如大躍進、反右、文ge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