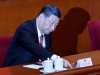1997年2月5日,新疆伊犁發生的使用軍隊鎮壓民眾抗議事件。伊犁市的維吾爾人組織了一次非暴力抗議示威,呼籲停止對維吾爾人的宗教壓迫和種族歧視;示威被血腥鎮壓,之後,大批參與示威的維吾爾人被中共當局抓捕。
1997年2月5日那一天,我正好在烏魯木齊。1997年的穆斯林開齋節是在2月7日,漢人的春節好像也是2月7日。
到2月5日為止,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大家都在為過節做準備。當然,作為穆斯林,大多數的維吾爾人都正在封齋,耐心地等待開齋節。每一個維吾爾人家的女主人也都開始準備饊子、甜點,開始給兒女準備節日的新衣服和禮物。
2月5日那天,我們一位老同學請客,幾個要好的大連工學院畢業老同學帶著家眷,晚上8點按時來到了一位同學在南門的家。但一位在公安廳上班的同學沒有來,房主人說,他答應一定來,可能耽擱了,要大家等一會兒。
等了半個多小時,快9點了,公安廳上班同學還是沒有出現,大家決定先吃飯。飯也吃完了,他還是不見身影。大約10點多,公安廳上班的同學來了。出乎大家預料,平時西裝革履的他,卻穿著警服來了,而且一臉沉重。
寒暄過後,他坐了一會兒,似乎掂量了一下,然後對我們說:「伊犁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不知道也不能說太多,事兒很大。載有北京領導的飛機已飛達伊犁,新疆軍區已經調部隊進入伊犁,兵團也已動員。我們都被要求日夜輪流值班,隨時待命。為安全,我建議大家今天還是早點各回各家。」看他凝重的神色,我確信事情很大。當然,不用說,大家都明白出的大事必然和維吾爾人有關。
聚會的熱情驟然消失,緊張和憂慮籠罩。我們大都在伊犁有親人,出動軍隊、動員兵團意味著又一場對手無寸鐵的維吾爾人的屠殺。
我們匆匆告別房主人來到街上,那天下著大雪,我和另一位同學站到路邊擋計程車。一輛又一兩,出租者司機減速探出頭看一下我們,然後就加速離開。快半個小時,我們決定讓女士和孩子擋計程車,一輛車停下來了,我和同學幾乎是從路邊衝到車前,快速拉開車門和家人鑽進了車裡,告訴司機我們要去的地方。漢人司機看看我們說:「今天我本來不拉維吾爾人,看你們像是受過教育的維吾爾人,我就拉一下你們吧。」
我有點不高興,「為什麼不拉維吾爾人?我們一樣付你錢。」
「你不知道嗎,伊犁的維吾爾人暴動了。伊犁一部分被你們的人占領了,聽說烏魯木齊機場附近也出現了武裝的維吾爾人,要打過來了,維吾爾人又要殺漢滅回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伊犁的一部分被維吾爾人占領,被手無寸鐵的維吾爾人占領,可能嗎?烏魯木齊飛機場出現武裝維吾爾人,哪來的武器?可能嗎?我不想和司機爭論,也不想猜測傳言。
本來我計劃那一個寒假都呆在烏魯木齊,和朋友們一起度過,但突然一切都變了,紅色恐怖的氣氛開始替代節日的氣氛。烏魯木齊也開始到處是軍警,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氣氛緊張得令人窒息,報紙、廣播、電視到處都是有關「分裂分子」在伊犁打砸搶的報導。我決定回家,帶著孩子和家人回到了石河子。
到了石河子,似乎學校就在等著我們,學校通知全體老師返校參加學習。表面看,我們是在學習江澤民和王樂泉發表的無數個重要講話,但很快我們就搞清楚了,這實際上是針對我們十來個維吾爾老師。我們被迫人人表態,義憤填膺地批判「分裂分子」。這,本來就令我心情鬱悶,感覺特別窩囊,憋了一肚子的氣沒處發泄。
一天下午,又是學習黨中央文件。台上書記在念江澤民的又一個重要講話,什麼「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分裂主義」等等。我身邊一位姓陳的老師大概也是寂寞了,嬉皮笑臉對我說:「伊利夏提老師,聽到了嗎?危險是來自你們這些分離主義分子。」我一下子找到了發泄的機會,大聲說道:「毛澤東不是說過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獨立!』怎麼維吾爾人就不能反抗一下嗎?」整個會場大家都轉過頭看著我,那位陳老師低著頭不敢看我。
書記看著我說:「怎麼了伊利夏提老師,這是在開會,注意會場紀律。」我搶白到:「陳老師說分裂分子是我們維吾爾人,維吾爾人怎麼了?這是維吾爾自治區!我們的權利被剝奪,還不能說話了嗎?我不參加會議了,再見!」我越說越來勁,越說越激動。
說著走著,我氣呼呼地走出了會場。來到操場,我遙望藍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儘管有一種一吐為快的感覺,但也不無擔心。我沒有注意到校辦主任是什麼時候來到我身邊的,他拍拍我的肩膀稍帶威脅地說:「伊利夏提老師,陳老師不過是在和你開玩笑。你要注意,不要在會場鬧事,你的職稱評比會受到影響的,要考慮後果啊。對了,書記要我告訴你,他要你明天早上先到他辦公室去一趟。」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書記辦公室。書記是一位老右派,上海人,他是從老師轉到教務處當主任,再突然升為書記的,我們很熟。書記辦公室門開著,我一出現,書記示意要我走進去。他先讓我坐下,然後站起來把門關上了。
他看看我,一臉嚴肅地說道:「伊利夏提老師,我很尊重你,但你得管住自己,昨天你的做法非常不好,破壞了會議進程。你是破壞政治學習,知道有多嚴重嗎?你必須寫檢查,陳老師也要寫檢查。」
他繼續說道:「我本來也要找你談話的,有老師也有學生反應,你在教室給學生講無關課堂內容太多,談民族問題太多,有政治問題。以後請你只講相關課程,不談民族問題,相信黨中央政策。你應該知道,你的中級職稱一直評議不過關,就是因為你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希望你三思而行,改變態度。」
我聽出書記話裡有話。我們教研室有一位姓趙的黨員老師,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從北京被發配到奇台縣,住在維吾爾人村莊,學會了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改開」平反後,來我們學校擔任漢語老師,給我擔任班主任的民族班教漢語。她幾次以聽課名義,在我給學生講地方史時出現在教室里,聽到了我用維吾爾語嘲弄中國編造維吾爾歷史的話語。當時,我就看出她很不滿意,而且她也曾當著學生面和我爭論,我都是一陣冷嘲熱諷懟回去。
那時,我所在教研室主任是另一位上海老右派,對共產黨嗤之以鼻。他曾有一天下班把我留下,關上辦公室的門警告我:小心趙老師!他告訴我,在教工黨員會議上,趙老師指責我民族情緒非常嚴重,經常給學生灌輸分裂主義思想等等,是個思想不合格,不適合當老師的人,更不應該允許我給民族學生上課。
我猜到了,趙老師把狀告到了書記這兒。當然,也不排除有其他老師或學生。
我沒有和書記爭辯,只是點頭表示在聽。等他講完,我問他是否可以離開?他似乎非常不滿意,直視著我說道:「伊利夏提老師,我這是以校黨委的名義警告你,你必須端正態度,虛心接受批評,學習黨的政策,提高認識。否則,後果自負!」
那一年,我的中級職稱又沒有評上,工資也沒有漲。優秀老師、先進工作者,我想都沒有想過。看著別人拿職稱、漲工資、評先進,儘管我儘量裝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但知道家裡親人也都覺得我活得窩囊。那些進步人士,則是覺得我不知好歹,不知感恩黨國。
那年暑假,我回了一趟伊犁。2·5屠殺過後的伊犁一片蕭殺,恐怖籠罩城市。維吾爾人人心惶惶,不知道那天晚上警察會衝進誰家,抓走誰家的孩子;走在街上,也是驚恐的眼睛看著持槍的警察,擔心一不小心會被開槍射殺。
我長大的村子,年輕人也都大部分被抓走了,我上維吾爾小學時的同學有幾個被判了重刑;我的一個表弟被酷刑折磨,幾乎成了廢人;遠親有兩個被槍殺。我呆不住了,十天左右我就返回了石河子。
1997年的2月5日,改變了很多維吾爾人,尤其是那些體制內的維吾爾人,包括本人。第一次,中國政府以所謂「打砸搶」名義對維吾爾人的屠殺就發生在我身邊,我認識的人、我的親人、朋友被抓捕、判刑,被槍殺。
1997年的2月5日是維吾爾人近代歷史上,又一個還在流血的傷疤。到底,中國軍隊、兵團打死了多少維吾爾人?抓捕了多少維吾爾年輕人?沒有人知道。但伊犁的維吾爾人幾乎每家,都有年輕人被抓走或被失蹤。至今,還有很多伊犁的維吾爾人在等待那些被判重刑的兒女們能夠回家,還有很多維吾爾父母在等待2月5日那天失蹤的兒女。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