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因輕信吃過什麼虧。
有關甲午戰爭的經緯幾乎已經被人寫爛了。不過,對於甲午的回顧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馬關條約》簽完,中日兩國並沒有如人們想當然的那般,立刻結仇。相反,中日俄三個大國之間的外交風雲,其實才為二十世紀前半葉中華民族苦難史埋下了更直接的誘因。我們今天來說說這段常常被忽略,但卻有至關重要的「甲午後傳」。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這個人的賣國賊形象,說不冤其實也冤。甭管是《馬關條約》還是後來的《辛丑條約》,都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明火執仗就是要搶你的,不簽其實也沒辦法。不過,真要說李鴻章決策失誤,主動「賣國」,倒是也有一次,只不過今天中國人反而不怎麼提,那就是緊接著《馬關條約》之後的《中俄密約》。
事情要從甲午戰敗,《馬關條約》簽訂開始說起。按照這份城下之盟所言,中國要賠給日本兩億兩白銀和台灣,還要把遼東半島也割給它。考慮到這片地方緊挨著清朝祖上的「龍興之地」,大清的決策者們很是肉疼。正糾結間,北方傳來了一個我們聽來很是「正義」的聲音,讓日本怎麼吃的怎麼把遼東給吐出來。
這個聲音,沙俄聯合法德兩國發出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俄國此時出來打抱不平,倒不是因為正義感發作,而是覺得日本割占遼東阻礙了它下一盤大棋。事實上,正當中日兩國在遠東掐的正歡,沙皇也在他的宮殿裡對著地圖比比劃劃,想要在遠東建立所謂的「黃色俄羅斯」——說白了,沙俄當時想自己把整個中國東北一口吞下。突然聽說日本人要搶先把遼東割走,吃慣了獨食的沙皇表示不爽,於是立刻義正嚴詞的警告日本人立刻放開中國東北——換他來。
不過,沙皇的這番「苦心」,中日兩國當時卻都沒有很深的體會,日本那廂只覺得自己很受傷,覺得自己維新多年,明明學來了君主立憲、近代化軍事,乃至西裝革履、留上了八字鬍,卻仍然是被歐洲列強當外人看。從此留下了心理陰影,「臥薪嘗膽」成了響徹當時整個日本列島的口號,日本人扯起「為黃種人爭取地位」的虎皮做大棋,憋在家裡一門心思大搞擴軍擴軍。
與之相對應的,清廷這邊卻樂壞了,清廷原以為洋人都沒有好心眼,突然見著這麼個肯給中國打抱不平的,當然驚若天人。
所以,在甲午戰爭以後,清廷的外交政策做出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由原來的「一體拒外」變為「有聯有拒」,而「聯」的對象,首先就是沙俄。1896年,清廷派出李鴻章出訪沙俄,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並密令他檢討「聯俄拒日」的可能性。
其實,以李鴻章之能,冷靜思考估計能看出沙俄「無事獻殷勤」背後安的什麼心。不過,甲午一戰大清賠光老底兒,此時實在拿不出手什麼東西來制衡日本,李鴻章這會兒也陷入了焦躁當中。
更何況,李鴻章一到莫斯科,估計很快就被捧的找不到北了——沙俄給了李鴻章空前的超規格待遇,紅地毯、儀仗隊和十九響禮炮聲,根據美國記者當時的報導:在參與典禮的各國來賓中,數李鴻章所受到的歡迎是最為熱烈的,其排場僅次於加冕典禮的主角沙皇夫婦。

這麼高的待遇,真是給足了李中堂和大清的面子。沒辦法,咱中國人就吃這一套,偏巧,沙皇陛下又向來善搞這一手。
在雙方熱烈而友好的氣氛,李鴻章和尼古拉二世很快簽訂了《禦敵互助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兩國共同防禦的目標明確指向日本:「如果日本侵占俄國遠東或中國、朝鮮領土,中俄兩國應以全部海、陸軍互相援助。」而為了滿足共同防禦的需要,清政府同意沙俄修築「東清鐵路」(也就是中東路)。

請注意,最後一點特別重要,因為藉助這條丁字形的鐵路線,沙俄可以將自己的觸角深入中國東北這片他們覬覦已久的膏腴之地。而這種做法,更挑起了其他列強入我堂奧的野心。
但據說簽了《中俄密約》之後,李鴻章反而很是滿意,他的密友兼幕僚黃遵憲在得知這份密約之後,憂心忡忡的提醒他沙俄一定沒安好心,要早做防範,但李卻自信的對黃說:「二十年無事,總可得也。」
不料密約的墨跡未乾,李中堂就被打臉了。
老來失計親豺虎
彼得大帝曾經有言,俄羅斯只有兩個朋友,海軍和陸軍。那麼按照這個邏輯,想成為其「第三個朋友」的民族往往會被賣的很慘。而這一判斷,在上個世紀初不幸被清朝應驗——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引來了八國聯軍侵華。
侵華八國之中,最積極、最興奮的就屬剛剛跟中國簽約締盟的沙俄,俄皇把幾年前剛剛許下的盟約拋到腦後,立刻通過陸軍大臣向俄軍下令:「中國已經到了衰亡、崩潰的邊緣,俄羅斯應當利用這一時機,攫取儘可能大的一塊。」

夢想「黃色俄羅斯」的尼古拉二世。

所謂「儘可能大的一塊」可真夠大——它包括整個中國東北。
趁著中國內亂,也藉助還在營建中的中東路,十五萬俄軍打著鎮壓義和團、保護「東清鐵路」的旗號,兵分七路,浩浩蕩蕩的殺奔中國。而借著中東路的便利,用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沙俄就占領了東北全境,且這一來就在東北安下窩了,一待就是五年,還節外生枝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七項撤軍新條件。明擺著是要吞併東三省。
交友不慎的李鴻章在絕望中被俄羅斯人逼死了,把黃遵憲氣的夠嗆,在送他的輓聯里刻薄的諷刺這位老友,說:「老來失計親豺虎,卻道支撐二十年」。
在黃遵憲和當時的很多精英們看來,李鴻章一生其他的過失也許都可推脫「時運不濟,不得已而為之」。唯獨「聯俄拒日」這招棋,是其主動而為的,大大的臭棋。

然而諷刺歸諷刺,面對沙俄陳兵十五萬於東北現實,自知打不過的清政府此時實在沒有什麼好辦法了——趕也趕不走,忍又忍不下。
交友不慎造成的創傷,似乎只能以新的交友來彌補,急火攻心的清廷這是不得不又一個外交急轉舵,轉而「聯日拒俄」。
其實,與中俄之間的「親善」僅僅停留在外交層面不同,當時中日之間,反而倒真有點「親善」的民間基礎——
甲午戰爭打完之後,中國的民間思潮從最開始對日本的仇視,迅速轉向對日本短時間內富國強兵的崇拜。
而日本方面,在認識到武力吞併中國沒希望後,轉而希望以中國的老師自居,開始炒作「日清提攜,復興黃種文明」的概念。事實上,從1898年開始,日本政府就開始自掏腰包請中國學生留日,至少最初,授課態度確實還算誠懇,連當時歐美密不外傳的軍事學科,日本都對大清國學生進行了教授(這導致後來不少抗日名將都有留日經歷)。

留日時穿和服的魯迅先生
在東學中漸之風的感召下,中國整個精英階層迅速走向親日。1898年至1907年這段時間,被稱為中日關係的「黃金十年」,兩國關係甚至好到中國人把自己的語言都模仿日文改造了——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漢語中,有大量詞彙(比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的「打倒」和「帝國主義」),其實轉自日文對西洋概念的翻譯。
更有甚者,維新變法中,康有為等人還提出要效法戰國蘇秦佩六國相印的故事,聘請伊藤博文來中國擔任「客卿」。「日本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中國人誠摯的願望。
而在中日打得火熱的背後,所有持此主張的人又都有一個潛台詞:現在威脅我們國家存亡的主要敵人是沙俄,跟日本結盟是我們唯一選擇。
於是就像當年李鴻章聯俄抗日時一樣,中國當時的精英們在短短几年後的聯日抗俄中也完全拋下了「一片心」。完全傾心結交。
有民間思潮做底兒,清廷的外交轉向登時間在國內一呼百應。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全國各地「請聯日以拒強俄」的請戰摺子紛至沓來,張之洞、盛宣懷、岑春煊、端方等大員紛紛表態支持此提案。
其中最激進的張之洞,還提出過一個今天看來十分「腦洞大開」的建議,他上奏說中國人的勇敢是沒問題的、也不缺兵員,只是我們現在尚未訓練好熟悉現代戰爭的軍官體系,所以真要打,則應「日本之將校,率我之兵,庶幾可與俄人一戰。」——張中堂不僅要中日組成聯軍跟沙俄血拼,還要讓日本軍官領導中國士兵上陣(也不知道他是打算讓中國士兵學日語,還是日本將官學漢語)。這個提議真的實行了,之後的歷史也不知會如何寫張之洞這個人。

到頭來,反倒是日本人擔心清朝參與對俄作戰會引發外交不利,出於自身的利益力勸清朝保持中立。
1904年,日本對沙俄宣戰,日俄戰爭爆發,而清廷表面宣布中立,暗中則傾向日方。而看到日本為了「亞細亞前途」敢於單挑強俄,中國人民更感動了: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鑑湖女俠秋瑾揮筆寫下了「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名句,盛讚日軍英勇無畏。在日本留學的陳天華更是組織「拒俄義勇軍」,要到東北去幫日本人拼命,還好,被中日政府合力給攔下了。
所以今天讀歷史,你會感覺很奇怪,對日俄戰爭這一仗,我們教科書中的官方叫法都是日在前,俄在後,其實以實力而論,這一仗應該叫「俄日戰爭」才對(就像同期的英布戰爭),其實這個叫法最初確定,就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親日情緒達到頂峰,順著日本人「日露戰爭」的叫法,我們也就這麼「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的叫上了。

日寇禍華的肇因
也許在整個中日關係史上,日俄戰爭都是中日關係最好的一段時光。然而,這段中日間濃情蜜意的日子幾乎剛過了春分,立刻就冬至了——我們中國人把日本人的參戰動機想像的太美好,而日本人在戰後的漫天要價,卻又太赤裸裸了。
與很多國人後來的指責不同,日本打日俄戰爭,主要目的還真不是為了取代沙俄稱霸中國東北,而是怕沙俄進一步染指朝鮮。所以日本最初跟沙俄提出的是「以滿易韓」,你瓜分中國東北,我占據朝鮮半島,咱倆都當好」模範帝國主義,井水不犯河水,這不挺好的嗎?
這個要求,日本覺得自己已經很克制擴張野心了——畢竟中國東北多麼膏腴,朝鮮半島那嘎達除了冷麵泡菜有個啥?出血大拍賣啊屬於是。
但俄羅斯這個帝國吧,作為世界列強之一,它在思維上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漏洞——心裡沒數,不懂得見好就收。總不會和不甘於與其他列強在合適的程度上達成妥協。過度的野心讓其霸道,而霸道的要求又每每讓其眾叛親離。
面對日本提出的其實對沙俄很有利的妥協案(後來日本人又讓步,說要以三八線為界,詳見《三八線,為什麼是「38°線」》),沙俄的態度基本是這樣的:你們這些黃皮猴子,怎麼配和我們高貴的第三羅馬談條件?還什麼「以滿易韓」,甭廢話。滿韓都是我的!

就這樣,求與沙俄「親善」而不得的日本,這才想起「提攜」一下「同文同種」的清朝。
換句話說,這個朋友本來就不是真心的,可是清朝當時自上而下,卻真的「全拋一片心」。
果然,隨著日俄戰爭的展開,日本的心思起了變化——由於日俄戰爭中軍事技術的演進(機關槍、重炮霰彈、塹壕、鐵絲網),以及日軍極端落伍的戰爭思想,這場戰爭日本打的太慘了,日俄戰爭日本號稱是「戰死十萬,凍死十萬」,總傷亡達到二十萬人以上,兵源幾乎打空了。有的村莊家家戴孝,戶戶披麻,完全是一場慘勝。
與之相比,俄羅斯人雖然最終輸掉了戰爭、整支太平洋艦隊報銷,但其上報的陸軍死亡總數卻不到三千人(俄軍把士兵當灰色牲口,這個傷亡統計一直都很迷),甭管真假,沒有太傷筋動骨可能是真的。
更讓日本感到不滿的是,在戰後簽訂的《普茨茅斯和約》中,日本除了獲得俄方割讓的殖民地和在華利益,沒有獲得任何賠款。沙皇尼古拉二世咬緊牙關就是不賠款。
這讓勒緊褲腰帶,在家吃了多年苦的日本人民很是不爽。《和約》簽訂消息傳回日本後,不滿政府「喪權辱國」的日本人民立刻在東京日比谷公園搞了場「群體性事件」,以燒外國使館的方式發泄不滿。
死了那麼多人,花了那麼多錢,卻沒撈到足夠多的好處。日本決定堤外損失堤內補,打起了中國東北的主意——按照日本人的一廂情願,整個東北是日本「幫」著中國保下來的,「心懷感恩」的中國應該對日本的予取予求全盤答應。
但這個帳,中國方面無論如何是不會認的,尤其當時主理外交事務的,是北洋大臣袁世凱。此公在朝鮮早跟日本打過交道,當下決心要做鐵公雞。主權問題,能爭一分是一分。
於是雙方就開始了從清朝打到民國的「滿洲問題」外交扯皮戰。
雙方爭論的具體焦點,聚焦在日本從沙俄繼承了的所謂南滿權益上——中方堅持認為日本即便繼承沙俄租借的大連、旅順、南滿鐵路等權益,也只能繼承「租借中餘下的年限」。然而,這些租借的年限大多所剩不到15年,日方掐指一算,覺得根本不夠「回本」,堅持要求中方延長。中方則當然不干。
在談判過程中,日本媒體天天濃墨重彩的渲染中國人「不懂感恩」(在日本文化中,這是十分嚴厲的指責)、而所謂「滿蒙權益」又是日本怎樣「犧牲數十萬帝國軍人」換來的。拜這些宣傳所賜,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印象迅速惡化。
與之相對,中國人也從之前的「親日狂熱」中冷卻了下來,從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中國人為日本「代表黃種人取得勝利」而如痴如狂,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短短十餘年之中,中國精英們對日本的觀感,又經歷了一次從頂峰到谷底的過山車。
1906年,中日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條約確認了中國對東三省享有主權,而大連、旅順等租借也應在15年期滿後歸還中國。
公道的講,對於積貧積弱的中國來說,能迫使日本簽訂這樣一份條約,也算是一場亡羊補牢式的「外交勝利」了,主理此事的袁世凱等人得到了清廷的嘉獎。但這個「勝利」,其實也僅僅是戰術上。從整體戰略上看,中國在這十年中丟失了台灣,又在東北結了禍緣,其實是大虧的。
在這場會議結束後,日本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說的一句話很能代表日本人當時的想法:「此次我抱有絕大希望而來,故會議時竭力讓步……不料袁宮保(袁世凱)如此斤斤計較,徒費光陰,獨不見大局。」
代表日本的小村心懷怨懟的走了。而中日的這次不歡而散,最終成為了兩國此後半個世紀為仇作對的起點,數十年後,日本將用悍然侵略的手段,試圖攫取他們在談判桌上沒有拿來的「滿蒙權益」。
寫到這裡,你大約能理解為什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對侵華為何如此執迷而瘋狂了,幾十年起,這場災禍的種子就已經被種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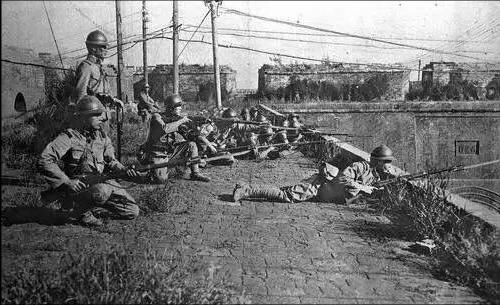
不可或缺的戰略級外交思維
從1896年的甲午戰爭,到1906年的中日締約,短短十年中,從「聯俄拒日」到「聯日拒俄」,外交政策經歷了過山車一般的巨變,但這樣看似靈活的閃轉騰挪非但沒有爭取到主動,反而整個20世紀前半葉的苦難史種下了肇因。這背後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至德收京回紇馬,宣和浮海女真盟。」必須承認,中華民族雖然勤勞、智慧、樸實,但在歷史上,我們並不是一個很有「外商(外交智商)」的民族。由於地理環境的原因,我們早早完成了「征服所有已知土地」的大一統。列國紛爭時代的早早結束,讓我們在面對歐陸那種「多元外交」時所必須的博弈智慧開始退化。
在戰國時代,我們尚有蘇秦張儀那種縱橫捭闔的戰略級外交大師,漢唐時代就只剩下了班超、王玄策那種「借威服遠」的戰術級外交家了。
到了南北宋,「約金攻遼」、「約蒙攻金」最後把自己活活玩死的外交蠢招就開始一再上演。如果說同時代的羅馬余脈拜占庭是在以其外交術給自己續命,那麼宋朝的外交就是一道催命符。

到了近代,我們從善用外交的英國人那裡學會了兩句很「叢林法則」的話:一,「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並奉之為圭臬。
但我們對這兩句話的理解其實從沒有深邃過。你看晚清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之間的這段外交術,表面上看,似乎一直在踐行這兩句話,可是一番博弈的結果,卻是盟友最後一個沒交上,禍患卻惹了一大堆。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深入了解英國歷史,你會發現,英國的外交政策,是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軸的:既「光榮孤立」和由其發展出的「大陸均勢」、「不列顛治下的和平」,從英法百年戰爭結束以後數百年至今,英國人萬變不離其宗,一直讓它的外交圍繞這個主軸轉動。

美國人後來承襲了這種思維模式,為自己的國家量身定製的「門羅主義」「離岸平衡」「美利堅治下的和平」等外交思想。

這種層級的外交思想,我們不妨稱之為「戰略級外交思維」
請注意,這些「戰略級外交思維」有一個共性:它並不定義或鎖死自己應該與什麼國家結盟——所謂「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其實是為戰略級思維服務的:敵友是可以變動的,但也絕對不是亂變的,並不是所有「敵人的敵人」都天然是朋友,必須圍繞這個國家的戰略軸心轉動。
有這些戰略級的思想作為主軸,再去思考外交上的「敵友問題」,這些國家的外交就不會出過於重大的紕漏。而與之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的外交思維,始終停留在晚清那樣的「找朋友」迷思當中,沉迷於到底「聯俄拒日」還是「聯日拒俄」的戰術二元選擇中,沒有自己的「主軸」。那麼這個國家的行動,就很容易被急於拉攏的那一方所綁架,圍繞這個「朋友」的外交主軸來轉動,最終一再重演被對方賣了,還替其數錢的悲劇。
幸運的是,正如我在《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要不要分的那麼清?》一文所敘述的,在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定了符合我們國情的外交戰略主軸——「無敵國外交」。正是在這種外交戰略的保駕護航下,我們迎來了人民幸福生活、經濟發展、國家崛起的黃金時代。

遺憾的是,從留言看,雖然我在那篇文章中解釋了那麼多到底什麼叫「無敵國外交」,很多普通人好像仍無法理解這種高深而英明的外交策略,這可以理解,就像顧維鈞所言,外交對大多數人來說本就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最可怕的是做庸俗化理解。
那我們不妨就把故事講的淺一點——從晚清那十年的交友不慎史當中,你至少應該弄明白一點:
敵人的敵人,未必真的就是朋友,也可能是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