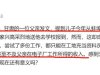大學生,集體度過了一個「社會面消失」的春天。
「非必要」的活動在這個春天被大面積暫停,它們是洗澡、出門、線下上課,還有實習、考試、面試、實驗……
不止這個春天,有人入學3年,一直被困在時斷時續的網課里,好多同學的長相都快忘了;有人的實驗、實習被迫終止,能不能順利畢業都成了難題;有人無法入職簽好的工作,有人為了出國讀書,跑了大半個中國「追逐考場」;有人被封在了寢室,重點心願成了吃飯、出門、努力讓自己保持心理健康……
「沒有去探索嘗試的途徑,對於整個大學生活都很失望。」一個女孩說。
我們時常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大學生在呼救,於是尋找了全國各地近20位大學生。
這個春天的「最嚴封寢令」里,有個上海女孩寫了4.6萬字的封寢日記;在被疫情影響的校園裡生活三年,有個男孩問「沒有疫情的大學生活是什麼樣?」;在面對1076萬的嚴峻就業形勢和各公司減招,有個畢業生說「我要不回老家吧?我們剛入世時就不得不開始考慮退路,很無奈。」
給一切蒙上不確定陰影的疫情,正重塑著大學生們的世界觀。
這遠非一座城市裡大學生的困境,而是一代人的大學生活。
當時代的混沌與大學的多元發生碰撞時,揮斥方遒的課堂、細密敏感的思維、浪漫想像的空間將如何被疫情重塑?新冠三年裡,這一代人的大學發生了哪些改變?
封校、封寢、返鄉
2022年4月底,長春。全城大學的「足不出寢」方案,已實行了50多天。
一所大學的宿舍樓里,走廊的樓梯口,兩名學生志願者坐著。
他們裝束一致,穿防護服戴口罩,眼睛注視著電子屏幕中網課的內容,時不時瞟幾眼走廊,空蕩蕩的,便又安心地把目光放在了屏幕上。他們也是被集中管理的在校生,一邊執行學校的封寢條例,一邊負責幫老師組織其他的同學。
從3月10日左右開始,長春市的大學就陸續下發通知,要求學生們「足不出寢」。
寢室門不可以隨便打開。走廊里的視頻監控開著,偶爾會有駐宿舍的輔導員到樓道里巡視。除了拿飯、放垃圾、上廁所、做核酸,學生要嚴格遵守「封寢」規定,以最大限度阻隔奧密克戎病毒的傳播。
吉林大學的大四學生姚創,從未想過會這樣度過大學的最後一段時間。
雖然從去年開始,長春每次出現疫情時,學校都會封閉一段時間,但也不過是封閉校區,大家還能在校園內活動。
到了這個學期,封校變成了封寢,氣氛徹底緊張起來。兩個月來,姚創除了室友,見到最多的人就是這些在走廊里的「大白」志願者。
東北的大學裡,多是公共洗漱廁所。每天的洗漱時間,姚創和其他同學都戴好口罩,在志願者們的協調下,每6人一組,進入原本供18個人共同使用的洗漱區,剩下的同學在門口遠距離排隊。
「封閉久了,飲食、生活都很單調,許多人承受不住這種單調如一的節奏,看不到任何期待。」姚創說。
除了日復一日的單調,洗澡很快成了第一個難題。
吉林大學生陳沛只能到夜幕降臨,用一條被單把陽台的窗戶封上,打幾盆熱水,快速把身上打濕,用搓澡巾搓一遍,連沐浴露都不敢用。三月的東北朔風刺骨,她5分鐘結束一次清潔。
4月初,無法洗澡的長春大學生陸續到微博上發聲、求助。但即便如此,近2個月來,大家洗澡的次數普遍都不超過2次。
4月中旬開始,上海的大學校園也隨著城市的靜態管理,開始陸續封寢。
大四的李文俊,幾乎把姚創一個月前開始過的日子,全部重過了一遍——畢業實驗無法推進,生活更千瘡百孔,洗澡要澡票、去超市靠搶號、理髮、炸雞漢堡都要預約。
學校面對1萬多封寢學生,每天開放的570個超市名額,李文俊孜孜不倦地參與搶號。如果搶到號,就是全員出動超市「打劫」,搬3個大號行李箱,帶著這些貨物滿載而歸,李文俊感嘆道,「又可以過一段好日子了!」
畢業論文已經不抱希望了,封寢耽誤了畢業實驗的進展,論文幾次易稿,最後變成了寫綜述。「原本實驗要做到4月才能收尾,後來封寢後,都實現不了。」李文俊說,現在自己每天搬運外國文獻,每天翻譯幾篇文獻,然後進行理解再書寫。
封寢的時間,比想像的要更久。
到5月初,長春持續了近2個月的封寢後,各大學開始發布了大學生「應返盡返」的返鄉通知,但各方在執行層面,幾乎是以恐嚇的方式來勸返大學生。
一位準備返鄉的大學生告訴我們,社區說「你不要回來,回來就是14+7集中隔離,上萬元隔離費」;學校說「你最好不要留下,即便情況好了也是長期封樓,餐食可能無著落,宿舍還要做環境消殺」。
而那些被同意接收的「幸運兒」,則面臨著盲盒般的隔離環境、高昂的返家費用、複雜的中轉線路……但相比之下政策臨時加碼帶來的不確定性更令人受挫。有人住進「7+7」隔離酒店後被告知要多隔離7天,有人聯繫好了社區的接駁車被攔下原地隔離,有人聽到好消息的第一反應不是歡欣鼓舞而是反覆質疑「保真嗎?是官方文件嗎?明天不會改嗎?」
在夢想和牽掛之間,大學生們從一種謹小慎微的生活,又過渡到了另一種謹小慎微的生活。
孤島之上
2020後的大學生活和此前40年的完全不一樣。
學校突然放假、提前返鄉,幾個學期網課,依賴網際網路跟同學聯繫,線下的見面越來越少,還有消失的畢業儀式。
高珂從2021年到上海讀大學,被困在時斷時續的網課里,讀了將近一個學年,還尚未正式地邀請父母朋友來參觀「她的大學」,也沒能走出圍牆去別的大學多看看。
和同學去看電影、音樂節、演出、旅遊……這些在她的大學生活里通通沒有痕跡,她對大學失望、對這場疫情痛恨。
在封校前的一堂大課上,高珂碰到過一位很想認識的同學。「剛開始沒好意思要聯繫方式,再開這門課已經是線上課了,這成了一場無疾而終的相遇。」
她懷念線下課,她喜歡那種「人與人互動、踏實的感覺」。
比高珂高兩級的余偉,這半年來的表現是夢魘不斷。
余偉又做夢了,這一次他夢到自己在家裡,喊父母起床。室友叫醒他時,他睜開眼看到宿舍那幾平方的天花板,失望再一次襲來。
他是一名痴迷於神經生物的大四學生,以前奇幻的夢境總是會冒出來:掉進地心或是在火星的外太空旅行,但封校後,總是反反覆覆夢魘,余偉夢到在監牢一樣被束縛的環境或是被人陷害,夢到重讀高中,夢到家裡發生變故。
余偉猜測,或許是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情緒的出口都太窄。
對父母,報喜不報憂;對千里之外的朋友,怕增加負擔、怕不能感同身受,畢竟在隔離期間溫飽無憂已是一件莫大的幸事,飯菜單調一點、頭髮長長一點、學習計劃被打亂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用老師的話說「克服一下就好了」;那心理輔導呢,輔導是由院裡的老師兼職。余偉有時想:在同樣封閉的日子,老師的狀況並不會比學生好多少,他們只是拿著一份薪水做必須要完成的工作。
包括余偉在內,很多同學都放棄了各種情緒的出口,任著生活肆意顛倒。
封閉的日子裡,打撲克、搓麻將,以往的沉浸感和專注感消解在即時娛樂的陰影之下,他們稱這為「合理的擺爛」,找不到意義感。
陳沛剛剛大二,正常的日子裡,她早睡早起,按時去教室上早課,下午去圖書館看看書或準備自己的專業課。上半年宿舍四個人被關在一起,她每天將近八點起床,早飯也不吃了,下午一起睡大覺,晚上不困,追起綜藝和電視劇來,除了課上學習到的知識,幾乎沒有自主學習的時間。
看累了就閉眼躺床上想事情,周圍傳來室友打遊戲、打電話、追綜藝的聲音,陳沛盤算著怎麼將學習計劃重新提上日程,而不是天天混吃等死。後來,一切難以改變,她索性關閉以往細密敏感的反思通道,她說「我只想自己好好的」。
規律的校園生活遙遠而奢侈。
「非必要不返校」的北京研二學生木木,她被困在老家。木木每天四點入睡,八點醒,躺在床上,木木翻來覆去地想:「今天、昨天、前天的時間到底去哪兒了?」
原本返校實習的計劃,被輔導員告知「不是特別必要的」。論文被擱置了,讀不進去書,寫不出來編碼。除吃飯、睡覺、運動外,整日無事可做。她期待兩周一次的線上黨團活動,因為要發言,這勉強算得上一件正事。
樓下是快樂的幼兒園小朋友在玩耍,遠處是快樂的阿姨們在跳廣場舞,父母在正常工作上班,只有木木自己,房門一關,像被世界遺忘了。手機是唯一與世界交流的渠道,有時候推薦的內容已經開始重複了,木木還在機械性地重複刷視頻的動作。
轉折的「自救」,是與外界建立聯繫開始的。
木木去考了駕照,在練車場,她和學員和教練拉家常,去熱鬧的夜市與廣場,與所有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講話。她本不是一個外向開朗的人,但覺得「這只是在尋找一些真實感,證明我還活著」。
在復旦的小魚,今年大三。封寢期間,小魚寫了4.6萬字的隔離日記《上海56天》,她記錄新聞、疫情進展、市民互助的見聞、網課心得、同學間互動,她把56天都記錄下來。
小魚原本希望,上海的朋友們看到共同的經歷,能得到一些寬慰;更希望通過記錄尋找每天的時間坐標,不讓自己成為封閉的孤島。但日記能帶來的力量,越來越弱。
「每天在經歷肉體困境的時候,就很難去專心想更長遠的事。比如我未來要做什麼職業、有什麼規劃。」小魚告訴我們,「如果你問我未來,可能我需要回到家人身邊,住幾天。到那個時候再聊一聊未來,討論才是客觀的,有意義的。」
封校不僅是生活半徑縮減,上課場合搬到了線上這麼簡單,大學裡,也不只有學分和文憑。
大學構築的社會體,關乎一個人如何尋找志同道合朋友,如何去探索知識邊界,如何抵達自己的人生理想。
而新冠蔓延的這三年,重塑著這一代人對於大學的認知。
畢業生的憂慮
疫情反覆,最焦慮的是即將離開大學校園的畢業生。
數據顯示,今年國內畢業生人數首破千萬。出國、讀研、工作,所有下一步的選擇,都不可避免地重重遇阻。
過去一年,為了自己的留學計劃,王永像牧民追逐水草般,在不同的城市間為了考場而遷徙。變化莫測的疫情,讓這場遷徙變得困難重重。
去年8月,王永在學校所在地武漢,預約了GMAT(經企管理研究生入學考試),但考試最終因疫情取消,她匆忙前往長沙,一戰失敗;二戰蘇州,隨後蘇州也爆發了疫情,無奈之下她選擇到上海實習,上海的考位穩定開放,她本希望一邊實習一邊考試。
當二月考完後她坐在上海街頭放聲大哭,感慨這一切太不容易了。而後,卻被困在了上海。
疫情之下,很多畢業生的實習、考試、面試被學校定義為「非必要的」,某種程度也改寫了眾多畢業生的人生軌跡。
研二林夏的寢室里,所有人的計劃都被迫打亂。很多人找工作,只能線上面試,很受影響。
林夏聽同學說,3月初,長春有疫情,有人報考了浙江省的公務員選調生考試,但因為疫情不能到現場參加面試,面試並沒有因此推遲,也沒有安排線上面試,就被直接pass掉了。「你不來了,這種機會就沒有了。」
有人去不了實習,只能選擇延期畢業,為了保留一個應屆生的身份,也為了一年1200元極低的租房成本;還有人即將簽約成為老師,卻因無法參加線下的終面,而被卡住……這些都並非孤例。
作為畢業生,姚創現在關心的,還不是未來,而是還沒畢業的他,怎麼就像已經被學校拋棄了?
為什麼出門考教資要自費隔離?為什麼學校疫情信息不公開透明?為什麼選調因疫情不能到場會被取消資格?為什麼低風險區不能返校?學生們紛紛在問,但質疑的聲音得不到回復。
「就像是說家長決策一切,連知情權都不讓知道,沒有離校但是歸屬感就蕩然無存了。」姚創說。
大學的邊界,突然真的成了一個圍城。想要出去的、想要進來的,都不能自己選擇。
原計劃3月底入職網際網路公司的王碩,被困在了學校。他一邊看著網際網路裁員狂潮、上海疫情、2億人自由就業、經濟下行等外部世界的急速變化;一邊在學校里在打遊戲和做核酸之間,過循環的生活。
王碩也曾嘗試主動儲備一些入職技能,但靜止的生活總能讓焦慮有縫可鑽,實在悶不住了,他約朋友到校園逛逛,但話題總不經意又回歸到令人無力的「大環境」和「裁員」。
在去年秋招,王碩還覺得自己未來一片美好,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到現在,王碩開始仔細盤算後路:試用期不過就被裁是最壞的情況,但要是能工作滿一年,被裁至少還有補償,工作時間越長,找下家也會更順利。因此,他盼望著能公司讓他多「苟」一段時間,掙個首付,然後去二線或回老家,進個小廠,過起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有孩子也好,沒孩子也行」。
時代的旋渦下,象牙塔里曾教給這些學生多少理想化的「原則」,在急速變化的形勢下,變成了他們的不解和困惑。
不少學校開始了5至8月的「百日就業衝刺」,更有高校院系在公共平台熱烈邀請用人單位來院招聘,積極推介自家畢業生資源。
但在雙減裁員、房地產暴雷、旅遊業停擺的諸多現實面前,這些手段都顯得杯水車薪,城鎮調查失業率已連續走高。國家統計局5月16日所發布的數據顯示,相較於全人群6.1%的失業率,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高達18.2%,是前者的三倍。
應屆生工作經驗少、起薪高,即便上崗也面臨著最先被裁員的風險。
還有一些畢業生剛簽完三方協議便被公司毀約,在脈脈職言上,他們在名單中將失信的公司一一列出進行控訴,可這無法改變他們將錯過春招和秋招機會的事實,一旦喪失了應屆生身份的保護殼,等待他們的,將是與社招大軍所進行的殘酷競爭。
保守一代
給一切蒙上不確定陰影的疫情,也悄然重塑著大學生們的世界觀。
年輕人熾熱的試錯念頭遠去,明哲保身求穩定,成了年輕一代的優先考量。
「畢業之後要不要回老家呢?」還有兩年才碩士畢業的小李,在這兩年時封時開的校園、時常出現的網課課堂上,無法控制地思考這個問題。
離家近、第一時間可以趕回父母身邊、即使隔離期間也能工作,不用怕失業等等因素,都成了小李所列出的優點。
王碩說,他現在更關注工作的穩定,其次才是價值。
他甚至有點後悔當初沒參加選調生的選拔,後悔沒去找一個輕鬆穩定的工作,他感到遺憾,「也不是學歷歧視,只是像我們這樣的人也要擔心工作的穩定性,剛入世時就不得不開始考慮退路,也挺無語的。」
向上的空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向下有保障。
每一次封城,每一個裁員或欠薪的消息,無形中都在加劇這股潮流。
更多大學生開始盤算著堅固的東西,用它們抵抗時代的不確定性,大家笨拙地學著屯物資、學著占有,害怕被困住,開始和同輩討論起公務員還是不是鐵飯碗,即使那曾被認為是最「退而求其次」的選項。
「把握窗口期」成了普遍的心態。每天關注學校論壇里的感染和新增,抓緊一切的時間去洗衣服、去洗澡、去呼吸新鮮的空氣,去把握哪怕只有十分鐘的自由,及時行樂的古訓,最終以一種令人心酸的方式對學生們顯現。
同物理邊界一起收窄的,還有大學生們對外部世界的探索欲。
姚創在朋友圈裡寫道,「在一個封閉的空間,獲得自我療愈的能力和個人內心豐盈,自我營造生活樂趣和意義感,並把這種自洽能力變成一種『本能』是多麼重要」。
春天一份名為「精神互助避難所」的文檔在隔離期間瘋轉,在頁首,創建者寫下建立它的初衷「減輕焦慮,記錄舒適浪漫的溫柔時刻」,裡面有貓貓狗狗、花花草草,大家尋找內心的安定,而不是關注世界的動盪,「時間在繼續,生命在流逝,我們在活著」。
校園與社會曾有分明的界限,但病毒所引起的劇烈動盪,讓邊界逐漸消融,可以說,疫情成了一場來自於理想主義教材之外的被動教育。
讀書期間一直順風順水的王碩,直到最近,才開始真正理解環境與個人的關係,「瘋狂裁員這種事兒,並不是因為個人能力的問題,它更多地與外部環境有關。裁員潮里,倒掛的應屆生總是首當其衝,這些因素是個人無能為力的」。
「所謂世道艱難,對誰都是如此。除了少數的幸運兒,對普通人來說都是差不多的,能早日找到一個舒服的方式,可能至少會活得舒心一些」,一位高校教授評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