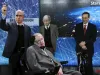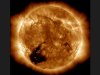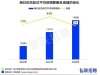作為我們系5年內招的唯一中國人,你可以想像剛進校時的我該有多麼意氣風發。不過生活捉弄起人來真的很簡單,只要把參照系換了,瞬間就能把大咖變成人渣。很快,耶魯就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剝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驕傲,也為我開啟了一段漫長的學術苦旅。
作者簡介
QQ,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博士。
今天終於交了博士論文,也算是給我的留學生涯畫上了大半個句號。2010年我被耶魯錄取的時候,拿著學校的最高獎學金。
作為我們系5年內招的唯一中國人,你可以想像剛進校時的我該有多麼意氣風發。不過生活捉弄起人來真的很簡單,只要把參照系換了,瞬間就能把大咖變成人渣。很快,耶魯就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剝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驕傲,也為我開啟了一段漫長的學術苦旅。
和優越感說再見
我所就讀的政治系是一個非常「白」的專業(就是教授和學生都以「白人」為主),這是因為專業對語言文字和表達能力的要求對國際學生來說實在是太高。以閱讀為例,僅僅是為了完成課業的最低要求,我們每周的平均閱讀量就達1000頁左右。我的美國同學每周花四五個小時就能看完並寫出精彩評論的書,我花兩整天時間啃下來,卻還是記不住書里到底寫了什麼。
低效閱讀的直接後果就是說不出話。政治系上課基本都是討論。我的美國同學都有本事把30秒的事情天花亂墜地說成5分鐘,而我的腦袋裡即使里有5分鐘的乾貨,用英語說出來也最多就30秒。這種強烈的反差導致了深深的自卑,讓我開始不願意在課上說話。而不說話是一個惡性循環,越是不說就越不敢說。有一門課我一學期就發了兩次言,每次上課都坐如針氈,像鴕鳥一樣低著頭不敢看老師,但回家後又總為自己今天怎麼又沒說話而難過不已。
至於寫作,就更是一道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有一次一個教授看完我寫的文章,專門給我發了一封郵件,列出了各種學校能提供給國際學生提高英語寫作水平的資源。我看了之後簡直覺得受了奇恥大辱。教授雖然沒有明說,但那意思就是,寫得太爛,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
面對殘酷的現實,自小順風順水的我也曾脆弱得不堪一擊。每次和遠在加州的男友打電話,一半時間是哭,還有一半時間討論什麼時候退學。最後商量的結果是,再堅持一年讀個經濟系碩士。當時很多不明真相的小夥伴都覺得我志存高遠,要上演一出屌絲逆襲的勵志劇。其實真相就是,我實在是受不了這種摧殘心智的日子,準備讀完這個碩士就退學,而有個經濟系的文憑找工作可以方便點。
於是抱著再讀一年就滾的心態,我這個只知道怎麼求導的文科生,開始和那些把數學專業課都上過一遍的經濟系博士們一起上課。閱讀寫作的要求是沒那麼高了,可也終於領教了什麼叫作碾壓智商。當我每周花10個小時才能寫完一半作業時,經濟系的大神們早已經結伴去酒吧撒野了。但此時我的心態卻好了許多,因為知道自己底子差,便覺得不會做題也並不丟人。
有一次微經考試三道題我只做了半題。一個同學跑來安慰我說沒關係,有曲線在(意思是大家都考的很差,最後成績不一定差)。我苦笑著回答道:「我都不在曲線上,我只能遠遠地遙望她」。說完這句話,我突然發現,曾經玻璃心的自己不知從何時起居然學會了自黑!以培養精英為己任的藤校,教給我的第一課是如此地接地氣,想想也頗為奇妙。當然這事最後的結局很俗套,碩士拿到了,我也決定不退學了。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當時腦子裡想的應該是,連經濟系碩士都拿到了,還有什麼困難過不去呢?
走出舒適區
從那以後,我就有一種「既然已經被剝奪得一無所有,便也不再害怕失去了」的感覺。為了在政治系繼續生存下去,我開始強迫自己在課堂上發言。而為了讓這個過程變得容易一些,我每次都儘量讓自己第一個發言。因為這樣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討論,又可以提前完成自己制定的發言任務,讓我不會在上課過程中被內疚感和挫敗感包圍。至於說什麼,我也儘量把討論的問題和中國聯繫起來。畢竟幾乎所有學政治的博士都對中國感興趣,而大家又都默認我是「專家」,萬一說得不對也沒人知道。就這樣開始,我給自己不斷加碼,從一節課必須說一次話,到兩次,三次,後來不用規定次數,說話也成了習慣。不久以後,我也從一個不敢說話的「啞巴」變成了能對學術著作評頭論足的人了。
但剛立住腳,新的考驗便又悄然而至。當時和我關係比較親近的三個教授在兩年中相繼離開了耶魯。面臨開題的我,居然一時找不到能指導論文的老師!前兩年苦心經營的關系統統作廢,而我卻必須在兩個月內說服三個對我毫不了解的教授組成論文委員會。在社會科學學科,學生的論文都是獨立作品,因此學生對教授來說更多是種負擔而非財富。於是我又一次被面子這貨擾得心緒不寧——教授對我這個不速之客會怎麼想?他們不願意指導我怎麼辦?轉念一想,找不到教授自己都要滾了,還來得及在乎這些?於是開始一邊向教授們刷存在感一邊展示自己的價值。去辦公室侃大山,出現在教授組織的討論會上,幫他們做研究。以前我特別看不起那種為達到目標不擇手段的人,覺得他們太功利。經過這一段才明白,那只是我為自己不願意走出舒適區而找的藉口。
我們系那年招中國方向的教授,來了三個候選人面試,由於相關教授因為利益衝突必須迴避,整個系竟沒有教授能從中國這個角度對候選人進行客觀評價。於是我熬了一夜洋洋灑灑寫了五頁看法交給錄取委員會,第二天被教授告知他們受益匪淺。以至於後來我趁熱打鐵,問教授能不能指導我的論文,他就欣然同意了。
少糾結,多幹事
我記得自己剛開始給教授發郵件,會呆坐在電腦前一遍遍刷郵箱。每天等不來教授的郵件就心煩意亂並開始胡思亂想,老闆為什麼回復了別人卻沒給我答覆?他是不喜歡我嗎?是我寫的太差嗎?我該不該發個郵件去提醒呢?過幾天發比較好……在這樣的無比糾結中度過了兩周後,我覺得自己要徹底瘋了,於是鼓起勇氣,把要說的話在心裡排練了好幾遍,設想好多種老闆回答的情景及對策,並裝作偶遇的樣子問教授,您收到我郵件了嗎?教授頗為輕描淡寫地答道:「哦?我好像不記得了我回去查查。」我當時簡直想把自己千刀萬剮——為了那些因毫無意義的糾結而流逝的時光。
還有一次,一個教授對我的論文提了個意見,我左思右想覺得他說的不對,可人家畢竟是專業大牛,於是我又為此事耿耿於懷了兩周。後來在一次會面中,我小心翼翼地闡述了自己的理由,沒想到教授一改往日態度說:「你做的對啊!我上次是這麼說的嗎?可能我那個地方疏忽了!」於是我又恨不得把自己暴打一頓……由此我學到了一個頗為殘酷的事實——別人沒那麼在乎我。
雖然教授很牛,但他要操心的事太多,哪裡會牽掛著我的每封郵件,又怎麼會記得我文章里的每個細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教授之於我只是經驗豐富一些的同事。尊重他們是應該的,但用不著為他們不回郵件而自作多情,也不必對他們的每一句話唯命是從。畢竟,只有我才是最需要為自己負責的那個人。有了這兩段經歷後,我就不再為盼著教授的郵件而輾轉反側,也不再為不同意教授的評論而寢食難安了。
看看外面的世界
當然,對於視學術為真愛的大神們,這句話可能不對。
文章能不能發表,教授喜不喜歡你,甚至最後能不能畢業,都不是努力就能夠搞定的事。如果把生命的全部喜怒哀樂都寄托在這些事上,不但荷爾蒙分泌會嚴重失調,結局也往往相當悲催(我第一年整天為課業憂心忡忡,結果長了一臉痘,回國時我爸在機場差點沒把我認出來)。
道理很簡單,但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呢?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找些別的事做。那個時候我除了寫論文,還一邊幫媒體寫稿一邊幫前世行行長打工,同時經營著自己的博客。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防止太專注於論文而走火入魔。對我這種神經還不夠強大的人來說,只有把論文當成是生活的一部分,才能不為了令人失望的回歸結果而垂頭喪氣,才能不為了教授的批評而鬱鬱寡歡,才明白即使最終拿不到學位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說來也奇怪,這最分心的一年也是我學術上收穫最大的一年。除了狗屎運外,平和的心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分心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可以環顧四周,開闊眼界。特別是對於像我一樣既沒有成為學術大牛的智商,又不是那麼熱愛學術的博士們來說,讓自己認識到世界之大和生命的可能性很可能是拯救我們未來的一根稻草。讀了博士的都知道,我們每天做的就是去思考「怎樣在已經被過度開發的學術山頭上,插上自己的一面小紅旗」。我們無數遍地被教授洗腦只有走學術道路才不枉博士一場,我們在一個狹小的領域裡竭盡全力走到前沿,卻無暇在意外面飛速變化的世界,最終讓自己成了象牙塔里的囚徒。
曾經有一個在系裡念了八年的同學跟我說,他之所以接受了那所美國中西部三流學校的教職,並不是因為自己想做學術,而是因為他不知道除了做學術外自己還能做什麼。已經陪上了八年青春,卻由於「不聞不問」而不得不繼續做自己不喜歡的事,豈不十分可悲?
動筆之前我一直期待自己能整出點金玉良言,但回頭看看這幾條,卻發現它們都是老生常談。曾經頗為失望——原來我讀了個博士才明白了這些道理!但轉念一想:讀博士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於學到了多少新知識,而在於經歷一場自我摧毀與重建的修行並由此獲得心智的成長。也許只有這樣,才有資格在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釋然地說一句:「Finally,I Ya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