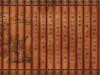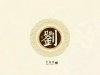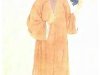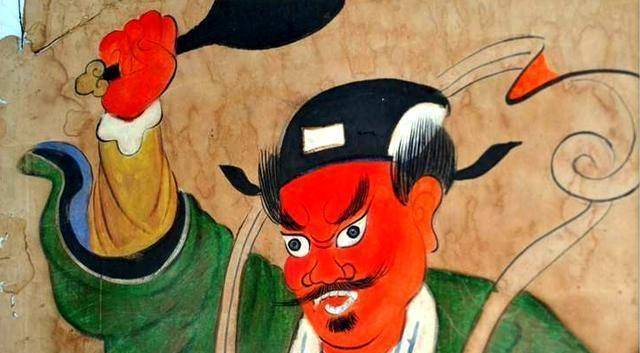
《山海經·海內東經》中載: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
坊間亦有諺:
心藏不義事,下雨莫出門。
01
一日午後,好端端的突然下起了雨。
天空看似雲薄,雨卻越下越急,澆得路人紛紛往家跑,或就近找地兒躲避。
驀地,隨著一道閃電閃過,一個霹靂當街炸響,直震得人頭暈腦脹,耳鼓嗡嗡作響。
緊接著,便聽驚叫聲起:「老天劈死人了——」
循聲望去,街面上果真有個男子遭了雷擊,被劈得外焦里嫩,猶如過火焦木般仆倒在地,一動不動。
顯然,早已氣絕身亡。
眾人戰戰兢兢靠前,搭眼一瞅,很快認出了遭雷劈者。
是個綠營兵。
大夥都認得他。平素性情溫良,待人和善,遇著貧弱之人還經常送些吃用,從不似那些兵痞般耀武揚威欺負人。
如此熱心腸的一個人,咋就遭了雷劈,死得這般慘烈?
一時間,眾人議論紛紛:
莫非,老天也犯糊塗,看走眼認錯了人?
02
天雷劈人,本是一種自然現象。
比如,綠營兵是扛著槍走的,槍尖引下雷電致使身亡。
但在古時,坊間百姓都堅信「人在做天在看,舉頭三尺有神明」,誰敢打爹罵娘,誨淫誨盜,必然會遭天譴。
這天譴的基本路數之一,即是雷劈。所以,人們在發誓時,特別愛拿雷公說事兒:
「我要撒謊,五雷轟頂!」
「我要在外包養小妾,天打雷劈!」
由此,龍身人頭、尖喙猴腮的雷公(《封神榜》中雷震子的形象)便成了懲罪罰惡、祛邪避災的總裁判。而被他咵嚓掉的,自然也都是些為非作歹的奸惡之徒。
扯遠了,趕緊回到雷劈現場。
這位慘遭五雷轟頂橫死當街的綠營兵,可是個好人呢,素無劣跡,不應該啊。
短短片刻,此事便報進了官府。
綠營,是清朝的常備兵種之一,參照明軍舊制,以營為單位,以綠旗為標誌,故稱綠營,也叫綠旗兵。
在清朝之初,尤其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中,綠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後,隨著八旗兵日漸腐化,綠營的地位則愈來愈高。

綠營兵規模大、工作累、待遇低,有滿清農民工軍隊之稱。
如今死了個好兵,須得徹查,給百姓以交代。看看到底是兵藏隱惡,還是雷公劈錯了人?
可不等派出人手,一個老兵便走進官府,長聲一嘆後道出了一樁發生於多年前的舊事。
03
當時,老兵和遭雷劈的綠營兵同在一個營,又是同鄉,關係相處得格外熟稔。
有一年,頂頭上司帶隊前往皋亭山(位於杭州城東北部)圍獵。暮色降臨,各自於山野中紮營歇息。
說來也巧,恰恰有個年輕小尼姑從綠營兵的帳篷旁經過。
見其素麵清秀,細眉細眼,身段也苗條,綠營兵禁不住心生歪念。
看周遭無人,便笑嘻嘻攔住了去路。
「你、你想幹什麼?」小尼姑慌問。
「別怕,陪哥耍耍。」
綠營兵一把扯住小尼姑,強拉硬拽拖進帳篷,並撕脫她的褲子欲行不軌。
眼瞅就要受辱,小尼姑又驚又怕,拼命掙扎中猛地一抬膝蓋,頂中了綠營兵的下三路。
這一下,可謂穩准狠,差點讓其雞飛蛋打。
趁其捂腹痛嚎之際,小尼姑奪路而逃,連褲子都沒顧上拿。
好事沒辦成,還連累小弟幾乎爆頭,綠營兵惱羞成怒,呲牙咧嘴開追。一直追出半里地,見小尼姑逃進一個小村落,方才悻悻而返。
而讓他怎麼也沒想到,一時獸性起,竟引發了一連串命案。
04
且說那小尼姑赤裸半身,慌不擇路跑進了一戶農家。
家裡,只有一個年輕少婦帶著個年約三歲的男娃,男人外出做傭工去了。
「姐姐,求你救救我。」小尼姑嗚嗚哭著央求,「讓我躲一躲,住一宿,行嗎?」
「出了什麼事?」少婦問。
「有個兵,想非禮我…」
聽罷小尼姑的哭訴,天性善良的少婦急忙關門上閂,將其藏於屋內,並借給她一套衣褲穿。
次日一早,天色未亮,擔驚受怕了一夜的小尼姑便倉皇離開,急匆匆回返尼庵。
臨近中午,少婦的男人回了家。
因做的是力氣活,弄得滿身髒兮兮的,男人便脫下衣服換一套穿。少婦打開衣箱,沒找到,這才想起昨晚錯把男人的衣裳拿給了小尼姑,而自己的還在。
正自責粗心呢,兒子稚聲稚氣地開了口:「爹,你的衣裳叫一個和尚穿走了。」
和尚?男人聽得心頭一咯噔:「哪來的和尚?」
「別聽他亂說,是尼姑。」少婦解釋道。
「是和尚,就是和尚嘛。」
小兒子比比劃劃,說昨晚來了個和尚,娘留他住了一晚,睡在了一張床上。聽說你今天要回,天不亮就走了。
「你閉嘴,越說越沒譜。是尼姑,」
「是個和尚,光頭的。」
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哪裡能分得清和尚尼姑?可少婦漲紅著臉越辯白,男人越懷疑:若是尼姑,幹嗎穿他的男人衣褲?為啥摸黑來,又摸黑走?
該不是怕街鄰瞧見吧?
好事不背人,背人准沒好事。男人越想越覺妻子與和尚做了羞恥之事,害他腦門泛綠,遂氣鼓鼓開罵。罵著罵著又動了粗,幾次將少婦搡倒在地。
不信我是吧?那我證明給你看!
少婦滿心羞憤,欲哭無淚,一掉身回了屋,懸了梁。
05
次日,男人正對著妻子的屍身發呆呢,院門口傳來了詢問聲。
「姐姐在家麼?我來還衣服了。」
男人抬眼看去,只見一個光頭小尼姑站於院門口,一手托著他的衣褲,一手提著糕餅。
這時,小兒子也看到了尼姑:「爹,那天晚上,和娘住一起的就是這個和尚。」
男人一聽,頓覺腦瓜子嗡的一下,後悔得要死。
「小混帳,這是和尚嗎?這是尼姑!」
趕走小尼姑,關上院門,念及是自己冤枉死了妻子,男人扯過小兒子,劈頭蓋臉沒輕沒重就是一通打。
結果,一時失手,把兒子給打沒了氣。
妻子上了吊,兒子也沒了,家破人亡,獨活還有啥意思?男人遂取來一根麻繩,自縊於妻子棺旁。
一場欺凌,一條褲子;稚子一言,三條人命。
彼時,街坊鄰居還納悶呢,女人賢惠兒子乖巧,男人能吃苦,好端端的一家人為啥就全尋了短?
而這樁絕門案,遭雷劈的綠營兵是在次年再度隨將軍去圍獵時才聽說的。
一念之惡,絕滅一家。
綠營兵深為自己的不軌之舉懊悔不迭,從此改惡從善,處處積德以贖補罪過。
哪成想,最終還是罪業太深遭了天打雷劈。
06
這樁雷斃營卒公案,出自清人袁枚所著《子不語》。

文末,袁枚如是結語:
「自是改行為善,冀以蓋愆,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逭也。」
《子不語》取自《論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此書仿照六朝志怪小說及《聊齋志異》,所載所錄多為鬼神怪異、因果報應之事。
雷劈營卒,講的也是善惡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