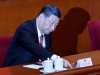2018年12月23日,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冬季那達慕大會開幕式上,當地民眾身著蒙古族盛裝參加騎馬比賽。
1991年有朋友安排我去西藏躲風,避免我剛在境外出版的小說《黃禍》惹來麻煩。那段西藏生活和旅行讓我開始認真思考中國民族問題。因為要避免《黃禍》發生,中國必須政治轉型,而那時正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民族衝突在轉型過程首當其衝,揭示中國的政治轉型會面臨同樣難題。本來我是當作中國政治轉型研究的分支,計劃用幾個月時間,結果持續了二十年,寫了《天葬——西藏的命運》、《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兩本書和一系列文章,以致在我被介紹身份時總是先被划進民族學領域,其次才說我是作家,而沒人注意我的主業是政治轉型。
有讀者問我為什麼沒有關注內蒙古,即使無力關注中國所有民族,內蒙古有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與西藏新疆是同級別的民族問題,我卻幾乎沒寫過什麼。
我多次去過內蒙古,二〇一四年還驅車上萬公里,走遍了內蒙古所有盟市,想看看有沒有寫的可能。但最終沒進行下去。因為如果動筆,我要寫的不是遊記,是民族問題,是蒙古的人。寫《天葬》時,我還能在西藏收集各種文件,與不同的人交談採訪。寫《我的西域,你的東土》時,收集文件成了罪,我坐了牢,但還有機會和當地的人交流。而現在的內蒙古,卻既無處收集文件,也無處跟人交流,甚至連蒙古人都難看到,滿目皆漢,無論是人是物還是地方,遇到的蒙古人要麼漢化,要麼不敢講話,要麼無話可講。
蒙古族的失聲,與文革期間的肅清「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直接關聯。當時在中國軍隊主導下,主要由漢人執行刑訊逼供,中國境內整個蒙古族當時為二百萬人,定為「內人黨」或被株聯的近百萬,幾乎席捲了所有蒙古人。數以萬計的蒙古人被屠殺或迫害致死。蒙古人的政治、文化、知識精英在那個過程基本被消滅殆盡。當一個民族經歷過那種摧毀,即使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下也得幾代人才能恢復,而在不自由的環境下持續中斷,一兩代人後便會永遠失去恢復的可能。
在我看,中國境內的蒙古族已經快像滿族那樣消失了。滿曾是和蒙古一樣強大的民族,蒙古人創立元朝,滿人創立了更長久的清朝。我出生長大的中國東北是滿人故土,我身邊應該有不少滿人後裔,但是連他們自己都失去了滿的意識(更別說語言、歷史和文化傳統)。在現實中,滿民族已經完全不存在,只留存在歷史的故紙堆,假冒的景點和清廷宮鬥劇中。內蒙古的蒙人除了馬頭琴和長調,民族意識的表達只剩在酒後感懷成吉思汗的榮光,再為蒙古人的已逝輝煌哭上一場。
不過,內蒙古的北邊有蒙古國,更北還有俄羅斯的四個蒙古共和國。我曾想過那裡也許可以作為了解蒙古問題的入口。當我的西藏問題文集俄譯版在布里亞特共和國出版後,布里亞特大學邀我去訪問。就在我將去機場飛布里亞特首府烏蘭烏德時,北京警察將我攔截在家,禁止前往。後來知道是俄國警察先去了布里亞特大學,禁止為我安排的所有活動。我只能猜想是因為布里亞特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俄方擔心研討中國民族問題的活動會產生官方不喜歡的影響。我懷疑攔截我出境是俄羅斯警方要求的,中國警方是配合,雖然沒有證據,但是各種拼圖之間的關聯明顯。從那時至今,我的出境禁令一直沒有解除。
此時,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中,可以看到俄羅斯的蒙古人被驅使充當前鋒,他們的傷亡率遠超俄羅斯人。這情景很像一九五九年中國軍隊對西藏的所謂「平叛」,派去衝鋒陷陣的是蒙古騎兵(見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還有這樣的報導更令人傷感——在布里亞特的首府烏蘭烏德,幾乎每天都舉行葬禮。首府大會堂本是孩子們玩耍的地方,現在放滿了陣亡士兵的棺材……
不知曾來我家做客的布里亞特青年攝影師格桑現在的狀況怎樣。二〇一五年那次我如果去成了布里亞特,學術活動結束後會去格桑在貝加爾湖畔的老家,與他家人共住幾天——那是當時最吸引我的安排。而今他的家人又是什麼命運?他的兄弟是否被送上了戰場?是否還活著?雖然經常牽掛,我卻沒聯繫他們,一是怕俄方監控通訊對他們不利,二是不知該怎樣表態。我反對戰爭,譴責普京,可那畢竟是他們的國家和總統。在涉及到民族問題時,分屬不同民族的友人之間就會陷入這種左右為難。我能做的,只是為他們的平安祈禱。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