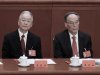去年臘月二十日我母親因病逝世,做兒女的頓感天塌地陷茫然無措。
親朋好友聞訊後第一時間趕過來跟我們一起分擔悲傷痛苦,克服天寒地凍的困難,不顧年底事情特別多,幫我們把母親喪事辦得簡樸而隆重。
辦理喪事期間,瀏陽電視台和瀏陽日報社幾位朋友的傾心相助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犧牲休息時間連夜通宵幫把我一篇早些時候寫母親並念給母親聽過的隨筆(實際上是我們母子最後的心靈對話)從我的微信公眾號里下載整理,精心設計式樣,反覆推敲排版,然後制印成十分别致暖心的紀念冊。
我之所以特別感動,是因為,我不只是離開宣傳線的工作崗位十七八年了,而且離開瀏陽住長沙賦閒休息都快三年了。
我當宣傳部長時,他們是報台一線的編輯、記者,彼此直接的工作交集並不多。有兩位我僅僅聽說過名字,人和名字至今都無法在腦海里掛起鉤來。

《暖暖春暉漫心田》紀念冊
事後讓人轉達我對這幾位過去老同事的感激之情時,他們竟說我太客氣了,都一致表示那個時候特別想為我分擔一點。有一位還說,回想我當部長時對媒體的真心理解、得體指導和全力支持,至今還會在他們遇到困難需要堅持時成為一種給自己鼓勁打氣的力量。
慚愧得很,我何德何能?說起過去我跟報台朋友們在工作中建立起來的這種超越時空的友誼,我覺得似乎不只是因為彼此工作有著高度關聯性,更多應該是緣於我們對新聞的理解與認知大體上是合拍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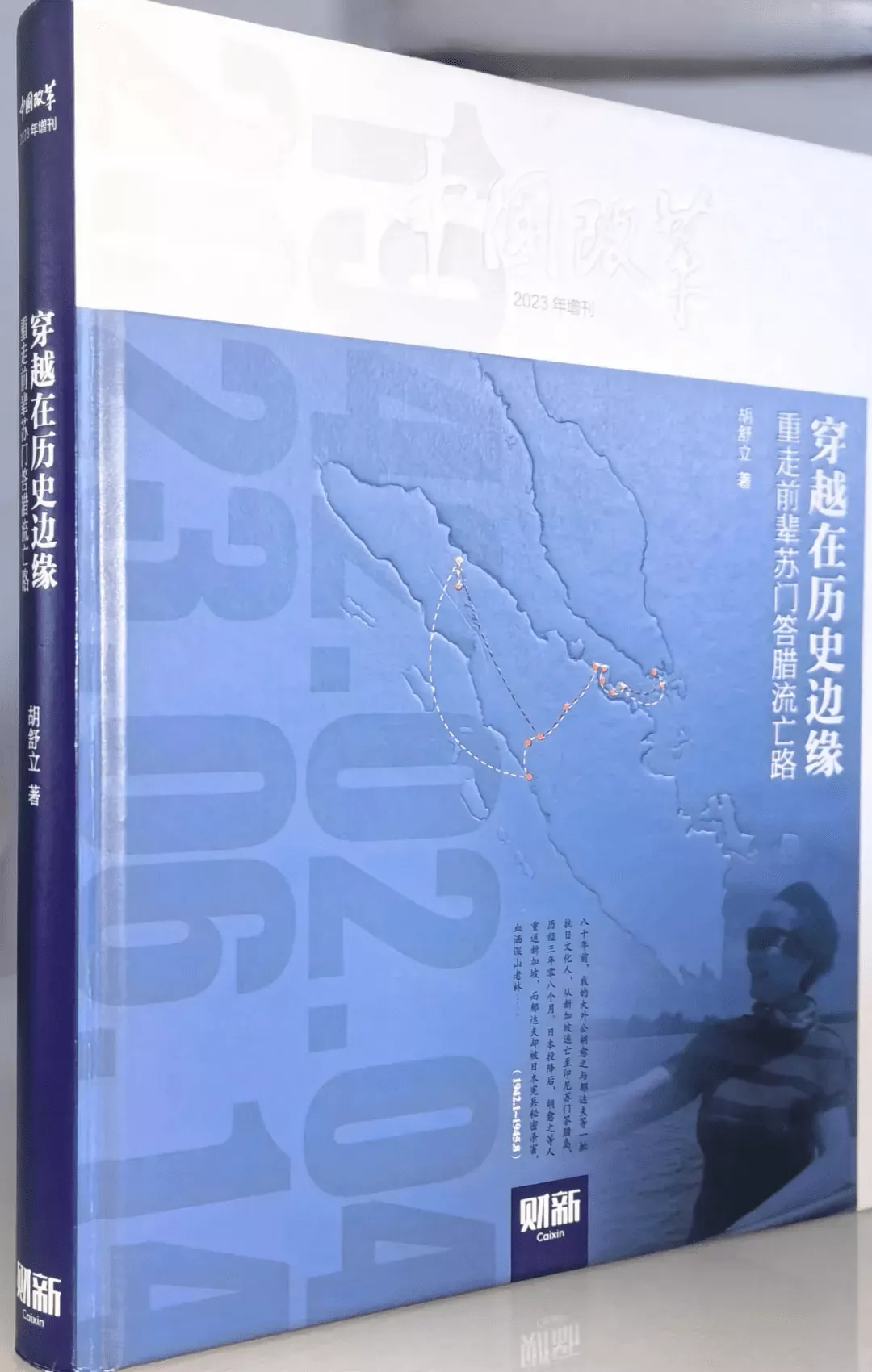
胡舒立女士新書《穿越在歷史邊緣》
就在上周末,接到瀏陽日報社的一位朋友發來一條信息,問我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女士的新書《穿越在歷史邊緣》是否有了,如果沒有,建議趕快下單,估計以後很難買到。我心裡「咯噔了兩下」。這位朋友怎麼知道我會對胡舒立的書感興趣呢,我對瀏陽媒體的同志從沒有說過我對胡舒立其人其書的看法啊。胡舒立的書真的會很難買到嗎?不至於吧,胡是一位專心致志做新聞做媒體得到社會廣泛認可的專家型媒體掌門人,說她的書會絕版應該是書商們的營銷策略?
過了兩天,我是這樣回復朋友的:
《穿越在歷史邊緣》到手了。謝謝您及時提醒我以後這書可能絕版,不然我還不會這麼上心。您可能不知道,胡舒立的新聞專業主義思想對我當年做宣傳部長有過很是深刻的積極影響呢。
記得是1999年年底,我們在長沙請上級媒體開一個座談會。在等待開會的時候,我聽一位央媒記者跟人在聊胡舒立有一本《美國報海見聞錄》很是有趣。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自己尋找無果後,就讓北京一位我過去的學生給我弄來一冊。記得隨同《美國報海家見聞錄》一起寄來的還有胡舒立的《微觀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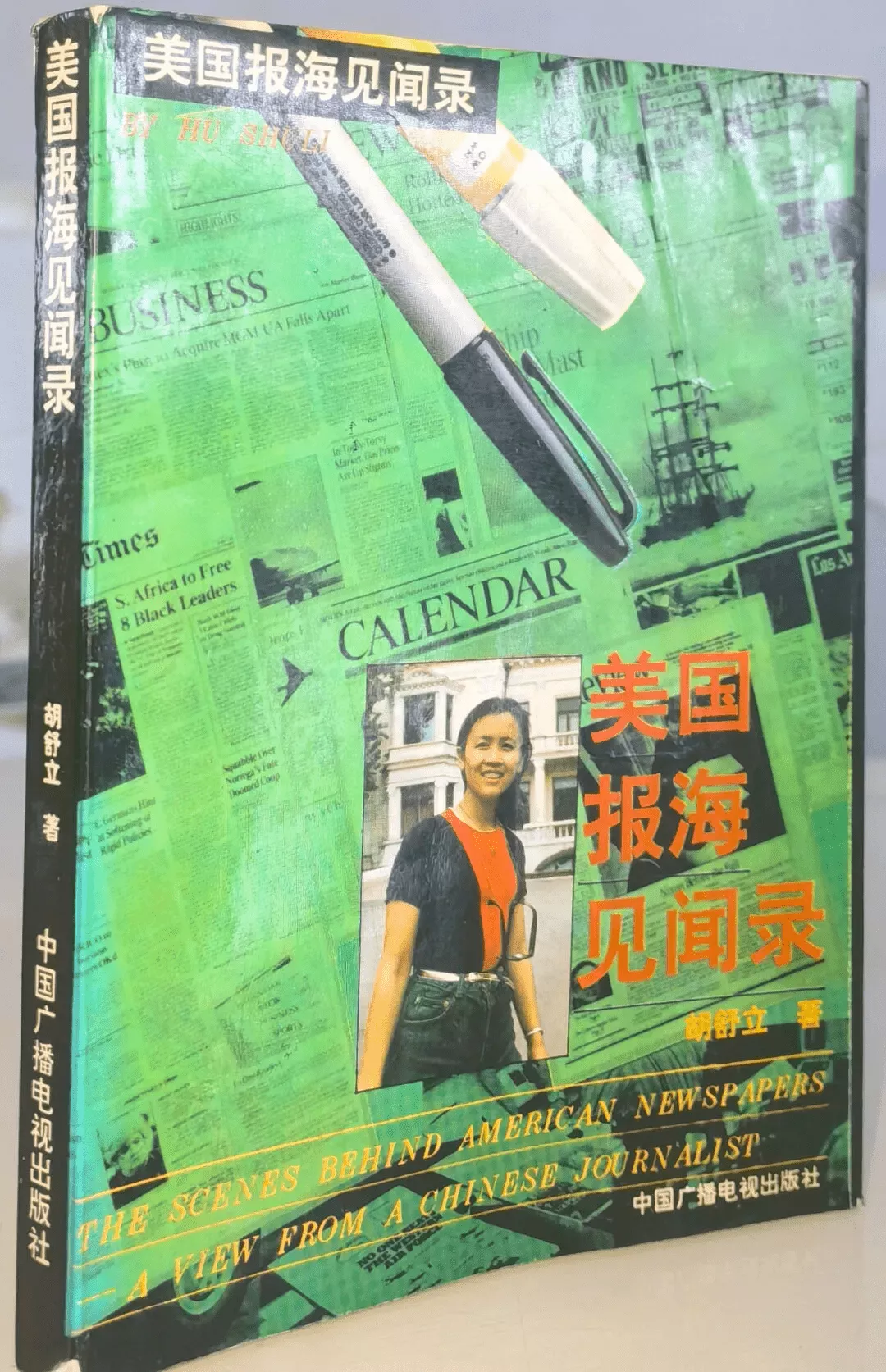
胡舒立《美國報海見聞錄》
《美國報海見聞錄》是1991年出版的,並不是很厚,封面略顯花哨,頗具那個時代的特色。內容甚是豐富,都是胡舒立花了將近半年時間深度走訪美國媒體的親身經歷,故事性極強,寫得輕鬆活潑,全都是關於美國報刊的人和事,琳琅滿目,活色生香,引人入勝。美國有影響的大小報紙的各自特色以至各類報紙從採編到發行的全過程都在胡舒立的見聞錄中得到生動細緻多層次立體式的呈現。胡舒立是新三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高材生,其時已在工人日報工作八年,是工人日報國際新聞部的副主任。她對國內媒體與美國媒體自然會有比較分析,但她的比較分析都是很得體地幾乎是不露痕跡地蘊含在客觀敘述的溫婉文字中。
那時,我剛到宣傳部履新不久。我原來對新聞對媒體了解很是有限。就這樣,胡舒立的《美國報海見聞錄》成了我在宣傳部長任上做新聞宣傳工作、跟媒體人打交道的啟蒙書。
胡舒立筆下的美國媒體都是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沒有各個層級的好心「婆婆」領導管理他們,但媒體活力十足。我在我們最基層的黨委宣傳部負責,就應該儘可能放手儘可能少做居高臨下的干預式「指示」,管理的核心定位在於為媒體服務,為他們撐腰,支持他們把新聞做好,讓媒體真正成為瀏陽人都喜歡的報紙、電視。後來有一次,新華社湖南分社分管編採業務的領導在一個公開場合稱讚瀏陽日報是一份值得尊敬的報紙。聞罷此言,我心裡感到特別開心。
我經常跟媒體負責人商量著如何做好監督批評報導。我跟他們說,沒有高質量的監督批評報導,媒體就不可能樹立自己的權威。我還說過,監督與被監督者不能共享利害,如果利害關係結為一體就不行;兩者必須要有一定的距離,有距離有空間才好做文章,如果距離太近,空間太小,就無法騰挪,監督報導就做不好。胡舒立在介紹自己走訪《華盛頓郵報》的具體情形前,先對當年這家報紙十幾年前「一意孤行」頑強作戰硬是一步步把水門事件弄個水落石出逼著尼克森總統黯然下台的過程做了一番梳理,然後指出《郵報》成功撬開「水門」的兩個關鍵:一是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新聞界的那種敏感、勇氣和韌性,二是有關政府公務人員對法律和正義具有比對白宮現任主人更高的忠誠。胡舒立借美國友人說出的這段話給我留下極深印象,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在宣傳部我工作了七八年時間,遇到媒體因輿論監督招致有關方面壓力時,我總是選擇站在記者一邊。
宣傳部的外宣工作除了對外推介本地的政績及經驗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協調踩壓上級媒體對本地的批評報導——大家喜歡叫負面新聞。與支持本土媒體做好監督批評報導一致,我對協調踩壓上級媒體的負面新聞缺乏應有的熱情,以致總是顯得力絀技窮,按現在的說法便是自甘「躺平」。2001年下半年瀏陽辦花炮節,組委會為了籌錢,讓計程車主花不少的錢買一份特製的宣傳招貼畫貼在各自車上。這一做法招致社會不滿,省里的媒體做了報導。那天晚上全體市領導坐著一張大車檢查節前市容市貌。行至半路,市委書記忽然從座位前站起來當著大家的面以甚是嚴厲的口氣斥問我知不知道媒體報導瀏陽攤派招貼畫這個事。我說知道啊。書記怒不可遏,「你要對這個事情負責!」我一聽,立馬也從座位上站起來,指著書記,一大串連珠炮隨即轟將出去:這次辦節賣招貼畫有沒有這個事呢?社會有不有意見?這個事是我乾的嗎?我負什麼責?這個事只有你書記才負得責起啊,攤不攤派招貼畫組委會會聽我的?市民舉報後要阻止省里媒體的深入細緻的客觀報導,人家能聽我的?直到我被同座拖住才結束對書記的頂撞。我心裡對踩壓這種客觀的「負面新聞」真的一點都不感冒。一個地方的美譽度是靠實幹干出來的。靠吹是吹不出來的,總是吹,牛皮都會破的;靠捂靠壓更靠不住,捂久了壓多了,會生瘡灌膿。今天回想起這件事,我都不知道當年那樣頂撞一把手是全因年輕氣盛初生牛犢不怕虎呢,還是受了胡舒立那本書的「蠱惑」。我是瀏陽的公務人員,我對法律對正義對事實應該具有比對現任市委書記更高的忠誠啊。
有一位周先生,「業餘記者」,以網絡發帖監督為業,監督瀏陽的方方面面,一度人氣挺高。我剛到宣傳部工作不久就跟他打過交道,成了「熟人」。從那時開始,他就一直把我的工作單位把我本人連同我的家屬親友都作為重點監督批評對象。前年10月在換屆交棒時我代表人大常委會做了工作報告,這位先生還撰文發帖提出冷嘲熱諷式的尖銳批評。其實,這二十幾年,對他和其他社會批評者我都是持很真誠的包容態度。我當宣傳部長也好,當副書記分管意識形態和政法穩定也好,包括當人大常委會主任,我既反對用錢用好處去爭取他和他的戰友,也反對用管理權力去打壓他和他的戰友。拿錢堵嘴,讓他們站在進一條戰壕,他們的聲音就跟我們的聲音成了一個調調。以力相壓,他們心底的怨聲更大,但再大的聲音被權力壓下了,我們便再難聽得到不同的聲音。

1986年1月29日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次日的《今日美國》頭版版面
當年讀胡舒立的《美國報海見聞錄》,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就是美國媒體特別注重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表達。胡舒立在闡述美國新聞教科書上的一個觀點時舉了這樣一個例子,《聖保羅報》在刊出社論《延長大赦期限》的次日,在社論版對頁登了一篇意見針鋒相對的文章《非法移民大赦該適可而止了》。美國新聞教科書的那個觀點是這樣的:社論、言論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其篇幅,它是有機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平衡的,表情豐富的。美國媒體一般都是通過版面平衡來實現表情的豐富,他們十分尊重批評家的獨立意志——哪怕會傷害自己報紙。批評家觀點對錯不是最重要的,「沒有一個讀者要求社論作者是先知,但每個讀者都要求社論作者絕對正直。否則,他的作品就成了推測和宣傳!」
我曾經為瀏陽日報社同志寫過兩篇書序。一篇就是為報社副社長彭劍澄先生的言論集《劍與盾》寫的。我自己曾經出版過一個雜文集子《琢磨事與琢磨人》,裡面也收了好些我為各級報刊寫的言論文章。我跟報社、電視台各個時期的評論員都保持著很不錯的公情私誼。
另一篇序言是為瀏陽日報社總編輯戴建文女士的社會新聞作品集《小人物大社會》寫的。言論之外,我特別看重社會新聞。《小人物大社會》這個集子,原來不叫這個名字,我看過書稿後建議她改用了這個名字。我覺得社會新聞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被時政新聞、財經新聞、文娛體育報導……切割得幾近於無的邊角余料蛋糕碎屑。即算從社會新聞的角度看,政治、經濟、文化依然是構築社會的三維。只是,在這裡生活的主角不再是政界要人、經濟巨擘、文藝明星,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也即平常我們所說的小人物。在我們的新聞世界裡,那些「大人物」你還能怎麼寫呢?他們自己講話多是照字念經乾枯乏味面目可憎,你再去按我們統一的宣傳口徑濃縮他們在各種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還能寫出有味道的新聞來?沒味道,誰看啊。那些「高大上」的時政新聞是給少數領導自己看的,社會關注度有限得很。